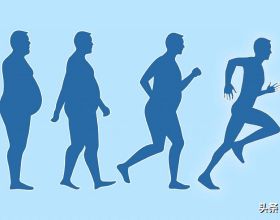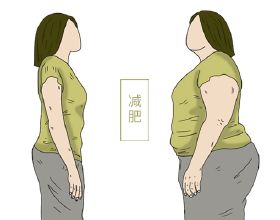“屈平辭賦懸日月”——李白的讚頌其實出自漢初淮南王劉安對屈原的評價。這是漢武帝即位第二年,劉安奉詔作《離騷傳》,稱《離騷》所述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楚辭”出現的第一個歷史記錄,也是因為漢武帝的賞識:“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史記》這段記載不如《漢書·朱買臣傳》交代得清楚:“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朱買臣言說了《春秋》《楚辭》,漢武帝就拜他作了中大夫。正是漢王朝帝王的推崇,開啟了楚辭經典化的歷史程序,而楚辭的成書就是它最重要的一個歷史標誌。
淮南定本的楚人之辭
同歷史上早期的典籍一樣,楚辭也有一個成書前的單篇別行民間口頭流傳階段,看《懷沙》一篇,《史記》所載與《楚辭章句》異文多達40餘處可知。美國學者宇文所安就對其流傳生成方式提出了思考:“到底有沒有證據向我們證明《懷沙》最初是‘書面’創作的?有一個可能是《懷沙》最初只是口頭創作,在口頭流傳。”(《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所以王逸說屈原所作“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王逸《楚辭章句》敘)。這在1977年出土的安徽阜陽漢簡中有了實證。戰國末年楚考烈王曾遷都於鉅陽(《史記·六國年表》),就在今阜陽太和縣附近。阜陽漢簡1號墓主為西漢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卒於漢文帝二年(前165年)。阜簡出土了兩片楚辭殘句:“寅吾以降”,乃《離騷》“惟庚寅吾以降”中四字,一片“不進旑奄回水”,乃《涉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中六字(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楚辭〉》,《中國韻文學刊》,總第一期)。因為考烈王的遷徙,楚人以相教傳的屈原的詩篇自然也隨之流傳,汝陰侯墓中所藏楚辭竹簡,可以證明它是戰國時代流傳下來的作品。《楚辭》今本《懷沙》“船容與而不進兮”中的“兮”字,在阜簡中作“旑”,與今出土的楚簡“兮”多寫作“旖”字為同一字,應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楚辭》的最早成書,《漢書·地理志》記載很明白:“昔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併發,故世傳《楚辭》。”壽春也是楚考烈王二十二年遷都的地方,也一定會有屈原的詩歌流傳。今又得阜陽漢簡《楚辭》,則劉安招賓客著書,“世傳《楚辭》”,可確證章太炎先生所言:“《楚辭》傳本非一,然淮南王為《離騷傳》,則知定本出於淮南。”(《訄書·官統中》)就是因為了漢武帝的詔令,劉安才有了蒐集、整理、纂輯楚辭的行動。從今本《淮南子》中,我們看到《謬稱》等14篇中就有與《離騷》《天問》《九章》《招隱士》等10餘篇中相同或相似的詩句,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劉安“招賓客著書”《楚辭》的內容。根據湯炳正先生《楚辭成書之探索》研究,宋代洪興祖《楚辭補註》目錄所載《釋文》保留了《楚辭》舊本的篇目次序,劉安所編《楚辭》,包括《釋文》編次第一到第十的篇目,皆為楚人之辭,由屈原、宋玉的作品組成。其中第九《招隱士》,作者為淮南小山,但蕭統《昭明文選》題為劉安。如是,則為古書舊例,書末附上編纂者自己的作品。而《招魂》一篇,不知作者,則為附錄,這也成了後來劉向、王逸《楚辭》的編纂體例。
騷體詩歌正規化的接受與生成
劉向編纂的《楚辭》見於王逸《楚辭章句》敘:“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不僅包括了劉安纂集《楚辭》全部作品,還增添了漢代作家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東方朔《七諫》、劉向本人的《九嘆》,另外,《惜誓》《大招》作者,王逸序有異說,《釋文》列在第十四、十五,屬於附錄。這使得《楚辭》內涵、外延都發生了變化,不再僅僅是楚人之辭,而是以楚辭的體式寫作的詩集。漢代作家創作的騷體作品,都以屈原為中心人物,採用了第一人稱敘述視角、“重著”的言說方式。我們看或題為賈誼之《惜誓》:“惜餘年老而日衰”,賈誼死時僅三十,何得言己“年老”?嚴忌《哀時命》:“靈皇其不寤知兮”,“孰知餘之從容”?東方朔《七諫》“赴沅湘之澌”“懷沙礫以自沉”,劉向《九嘆》:“雲餘肇祖於高陽兮”,“九年之中不吾反”。這些都可以看出敘寫的是屈原,不是漢代作家自己的人生遭遇。他們的詩不僅用了第一人稱,有的還用屈原的詩句或相似的詩句。宋玉《九辨》“去鄉離家兮徠遠客”,“願一見兮道餘意”。清人張雲璈就說“篇中自屬代屈之辭,文為宋文,語為屈語”(《選學膠言》)。這種第一人稱的代言體,本就是屈原詩歌的表達方式。如果說《離騷》《九章》第一人稱敘寫屈原人生行事,但《九歌》:“邅吾道兮洞庭”,“君思我兮不得閒”,“凌餘陣兮躐餘行”,《天問》:“吳光爭國,久餘是勝”,“吾告堵敖以不長”,皆非詩人行事(參拙文《口頭傳統與文人創作——以楚辭的詩歌生成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因而嚴忌等漢代作家作品收入《楚辭》之中,就在於他們在閱讀屈原、宋玉的作品中,同愁共感,接受認同騷體詩歌的書寫方式。在王逸建構的歷史上第一個“楚辭”正規化中,就包括了他們的創作:屈原詩歌“諷諫懷王”,宋玉“閔惜其師”“作《九辨》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鹹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辭’。”明於此,就懂得了唐人皮日休《九諷》序不解王逸不錄揚雄《廣騷》、梁竦《悼騷》的原因了,因為它們並非屬於屈原為中心人物,運用第一人敘述的代言方式的騷體。後來宋人重編楚辭不成,也因為他們試圖納入許多不合騷體範式的作品。所以,從書寫體式上,可以更好理解王國維“楚之騷”為“一代之文學”的意義,《四庫提要》則從圖書分類的學術性質上說:“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他集類。體例既異,理不得不分著也。”
其實漢代作家的騷體作品又何嘗沒有書寫自己的時代遭遇與人生情懷呢?他們的“鹹悲其文”,就是在屈原作品裡,強烈地感受到了其中的現實人生的價值關聯,而漢成帝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不過是為十六卷《楚辭》的生成創造了歷史條件。
楚辭詩歌與楚辭之學
在劉向《楚辭》基礎上,王逸撰成《楚辭章句》十六卷,雖然只增添了王逸《九思》一組作品,卻代表了一個楚辭經典篇目的文字最終建構完成,共計十七卷。從前的相關著作,多集中解說《離騷》一篇,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楚辭章句》則對《楚辭》全部作品分篇作序,逐句訓釋、解說,考訂作者及其創作背景,闡明主旨。其中“或曰”“或雲”保留的前人舊注40餘條,又告訴我們,它們可能是來自楚辭作品的“以相教傳”“史官錄第”“列於譜錄”多樣化的傳播渠道。
因此楚辭的經典化就在《楚辭章句》這樣文字的生成中展現出來。它收錄了全部楚辭作品、作者的資訊,在對騷體的詩歌正規化的歷史認同與接受中,構成了楚辭的經典文字,成為後世所有楚辭研究的作品文字依據。在全面系統的訓釋、解說、闡釋、評論中,開掘作品的闡釋空間和價值潛能,召喚了無限的屈原、楚辭詩學的論題與思索,展現出了楚辭一家之學的廣闊空間(章學誠《文史通義·文集》)。不過,王逸作《楚辭章句》是上奏朝廷,章句之體採用的就是漢代經學的思想方法。他推崇屈原是“忠正為高”“伏節為賢”的人臣典範,屈原詩歌的定位是“依《詩》取興”“以諷諫君”。這與漢武時代劉安《離騷傳》的比附經義,劉向《楚辭》典校經書的傳統一脈相承。可以看出,楚辭的經典化就是在漢王朝的政治文化建設的歷史程序中完成的,而作品得到了系統的評論、闡釋,楚辭的經典化才有了實現的可能,因為它代表了歷史的檢驗與認同。
(作者:熊良智,系四川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