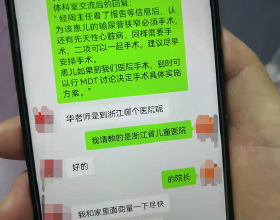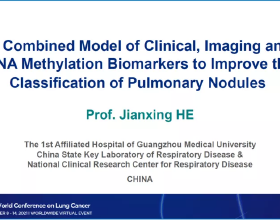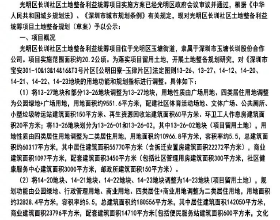回家探親,老遠就看見啞巴哥給我打招呼,“來了”(他衝我點點頭),“來了”(我也衝他點點頭),我們倆都不約而同地笑了。
我們找了個乾淨的地兒坐下,他抽出一支菸遞給我,我說:“我還是不抽菸的。”(我笑笑搖搖頭),他說:“這樣好,抽菸沒有好處的。”(他衝我豎起大拇指,然後用手捂著胸口做咳嗽狀)。我們倆又都不約而同地笑了。我捏了捏他的腿問道:“如今腿還疼嗎?”他說:“越來越嚴重了!”(他做了個痛苦的表情,然後從腿一直摸到腰間),我知道他的老寒腿病如今已經影響到腰椎了!我真的後悔這次沒來得及給他捎些“虎骨傷溼解痛膏”來。
說起啞巴哥的老寒腿,那話就長了。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莊上的人吃水很困難,幾十戶人家都吃一個土井裡的水,很不衛生,而且遇到乾旱年頭,連渾水也吃不上。於是幾個年青人就自發地鼓動起來打井,這是件好事呀,全莊人都很支援。可這裡是山區,真的要打一眼水井是相當困難的。真是工夫不負有心人,從開春一直幹到挨麥口,終於打出了一眼二十多米深的水井來。
可是就在修井沿的時候,石匠不小心將錘子掉進了井裡,當石匠想下去撈錘子時,被老人們攔住了。老人們說別看現在是夏天,可井水涼的很。夏天人的汗毛孔是張開的,下去會激成病的,弄不好還會落下關節炎病根呢。大家都說算了,不就是一把錘子嗎,弄成病就不值得了。
就在大家決定放棄撈錘子的時候,只見啞巴哥已經順著井沿的石級下去了。大家都很著急,示意他趕快上來,可啞巴哥還是把錘子撈了上來。然而,不好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啞巴哥的腿從此就真的落下了關節炎,成了老寒腿。晴天還好點,一到陰天啞巴哥的腿就疼得不能邁開步子,夏天還好點,一過立秋,啞巴哥就得早早地穿上了棉褲。冬天那就更慘了,腿上裹了好幾層老羊皮,還是冷得哆嗦,疼得要命。如今啞巴哥老了,連腰椎都疼了。唉,這該死的錘子,我想。
其實啞巴哥不光腿疼,他的心臟也不好,那是被氣得。
這事還得從頭說起。有一年,啞巴哥逃荒要飯到了東海,那可是個出名的瓜鄉!東海的土壤是沙淤,特別適合種西瓜,那裡的西瓜真的能與新疆的哈密瓜媲美。一天,啞巴哥要飯來到一個瓜棚裡,善良的老人看是一個聾啞孩子,就收留了他,並手把手地教啞巴哥學種西瓜的本領。啞巴哥雖然不會說話,可也是個心靈手巧的人,一年下來,就學會了整套種西瓜的技能。
不久啞巴哥的家鄉也分田到戶了,啞巴哥也有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於是他學到的手藝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了地裡。他要種出和東海一樣的甜瓜來,也好改善一下自己窘迫的生活。
他不用拖拉機耕地,而是用鐵鍁一鍁一鍁地挖,一鍁一鍁地翻,把個山地整得跟菜畦似的。再說那老天爺也架勢,那年冬天的雪雨特別多,天氣也特別冷,把個土地凍得結結實實的。過了年,一開春,一解凍,那土酥得像砂糖,那地軟得像棉絮。啞巴哥又把一冬天起五更睡半夜拾來的雞屎糞,摻豆餅和麻汁,捂好曬乾碾細,撒在地裡,接著又把那一畝三分地整整翻了三四遍。啞巴哥又跑了一趟東海,向師傅要了最好的西瓜子——豐蜜一號,精心地挑選,浸種催芽打缽,便在清明的當天下種,穀雨的當天移缽於地膜之中。哪天破膜,哪天間苗,哪天壓壟,哪天理花,哪天梳果,哪天掐頭,啞巴哥都是做的井井有條,頭頭是道,真是個行家裡手了。
一百天的時候,啞巴哥的西瓜地裡已經是滿地滾繡球了。那些綠皮黑槓圓圓的傢伙靜靜地躺著,散發出誘人的清香,惹來了多少“讒嘴貓”駐足而觀,啞巴哥哪裡能放心得下。他白天在地裡侍弄著瓜田,晚上就住在瓜棚裡。因為他有腿疼的毛病,喜歡喝點小酒,一來暖暖身子,再者也能和和血,減少點疼痛。
一天晚上,看著自己用汗水澆灌的滿地的西瓜,也許是心中高興吧,不知不覺竟把大半瓶蘭陵二曲喝得精光,呼呼倒頭便睡。哪知莊裡那幾個遊手好閒的“饞貓”早就打起了偷西瓜的主意,今晚見有機可乘,便悄悄來到瓜棚,連人帶床抬出去老遠放了,就把那滿地的西瓜一掃而空,揚長而去。
啞巴哥醒來後,看著那光禿禿的瓜田,竟雙膝跪地,手抓黃土,仰天長嚎。這真是應了那句老話,“啞巴吃黃連——有苦沒法說”呀!突然,啞巴哥猛吐一口鮮血,栽倒在地,昏了過去。
啞巴哥甦醒後,他一口氣拔光了所有的西瓜秧,一棵沒剩。又一把火燒了瓜棚,便離家出走了。
看我坐著出神,啞巴哥輕輕的推推我,朝著他家的方向指了指,意思是讓我到他家裡去坐坐。我點點頭,起身朝他的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