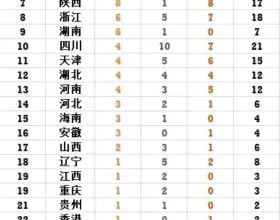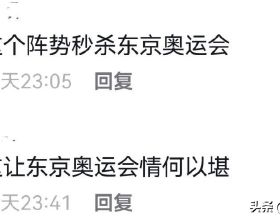吱呀吱呀的開門聲,隨著一陣微風飄向村外……
村中央老宅院的門口坐著一個老頭兒。老頭兒身邊臥著一條黝黑的狗,還有一群在樹下刨土啄食的雞。老頭兒對樹下的雞說:“叫幾聲,咯咯地叫幾聲。”雞隻顧啄食,沒叫。
老頭兒站起來,離開老宅門,手背在身後,向村邊走去。
狗起身跟著老頭兒,來到村外的小河邊。老頭兒長嘆一口氣,望望遠方,低頭看看狗說:“老夥計,你朝著村外叫喚幾聲。”狗抬頭望望老頭兒,不叫喚。老頭兒和狗繞村一圈,又回到老宅門。他對狗說:“不叫喚算了。”他兩手開始推動老宅門,老宅門吱呀吱呀地響了……
老伴兒從屋裡走出來說:“老頭子,你是咋了,和門有仇?”老頭兒拍拍門說:“老伴兒啊,我不傻,門比我的命還值錢。我就是怕它生鏽,才讓它和你我一樣喘喘氣,動彈動彈。”
老伴兒似乎懂了。她走近老宅門,細細打量著,兩手摩挲著,也慢慢地一開一合地推著……
老兩口兒一人一個門墩坐下來,眯縫著眼睛說話。
老頭兒說:“老伴兒,你還記得咱倆成親那時候嗎?”老伴兒說:“記得,當年咱倆騎著高頭大馬繞村一圈,最後你揹著我跨過這個老宅門,一直背進南屋房的。”老頭兒說:“你是大家閨秀,村裡人看稀罕,老宅門,門裡門外都是人,鞭炮聲、嬉笑聲,還有八音會的鑼鼓聲,可把個小村莊鬧騰夠了。”老伴兒說:“我蓋著蓋頭,戴著銀帽,沒敢掀開,只從蓋頭下面看著滿地的腳挪來挪去。”
“是呀,深夜十一二點了,那幫渾蛋們還在鬧洞房。他們走了,我才吱呀一聲關上了老宅門。”老頭兒笑著說。老伴兒說:“那天你迎來送往累了,躺倒就鼾聲四起,都沒顧上看看我……”兩位老人在緩緩地說著話。大黃狗許是臥得時間長了,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在院邊轉悠。突然,狗跑了起來,汪汪地叫了幾聲。老兩口兒趕緊睜開眼,還以為有人來了,一看,是大黑狗在追耗子呢。
老頭兒望著村口繼續說:“老伴兒啊,還記得咱兒子結婚嗎?”
“記得,村裡人第一次見城裡姑娘,滿村的人又把個老宅門門裡門外圍個水洩不通。小汽車在大門外排成一長排。”老伴兒說。老頭兒說:“那個氣派呀,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進城了呢。”
老伴兒說:“那時夏天吃飯,村裡人最愛端著碗來咱們老宅門坐著,一邊嘮嗑兒一邊吃,吃個飯就像開會似的。”
老頭兒患上了半身不遂,老伴兒也老得沒力氣再去推那沉重的老宅門了。螞蟻在老屋的地上拖著東西發出吱吱的聲音。
老頭兒好久沒聽到老宅門的吱呀聲了,他躺在炕上白天黑夜地睡不著。老頭兒伸手拽拽老伴兒,讓她想辦法。老伴兒尋思著,去箱裡翻翻吧。她找出了當年他倆結婚時戴的銀帽子,上面有許多亮閃閃的銀鈴。
看到帽子,老頭兒彷彿看到了年輕的自己……
她不忍心地把帽子上的銀鈴卸下來一個,舉在手中搖晃著。聲音有點兒小。老頭兒說:“有聲音總比沒有強。每天,你搖幾下,我搖幾下。”老伴兒知道是自己自私,不想失去年輕時的風光。老頭兒也看出老伴兒的心事。老伴兒把銀光閃閃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左右搖晃幾下,滿屋子銀鈴聲聲。老兩口兒都笑出了眼淚。
老伴兒從頭上摘下帽子,放在炕上細細地端詳著說:“我已經風光過了,還是把銀鈴全摘下來吧,把它們拴在一起,聲音會更響亮的。”老頭兒老淚縱橫地說:“這銀帽可是你孃家最貴的陪嫁,你還是留著吧!”老伴兒說:“放箱底也是閒著,拿出來讓它響著,咱倆能天天樂和。”老兩口兒用他們那佈滿老年斑的手慢慢地把亮閃閃的銀鈴一個一個地都摘了下來,用一根細鐵絲把銀鈴全系在了一起。老伴兒託著沉甸甸的銀鈴走出老屋,來到院子裡,把銀鈴掛到了老宅門的門閂上,又用一根長繩子繫著銀鈴,一直拉到屋裡的炕頭。老伴兒把繩子放到了躺在炕上的老頭兒手裡,老頭兒輕輕一拉,銀鈴就丁零當啷地響起……
老兩口兒每天有事做了。你拉一下,我拉一下。銀鈴在老宅門的門閂上發出陣陣清脆的聲響,聲音驚動了院子裡的雞狗。
瞬間,村莊一片雞鳴狗叫聲……
老頭兒說:“好啊!好啊!村莊有魂了。”(作者 張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