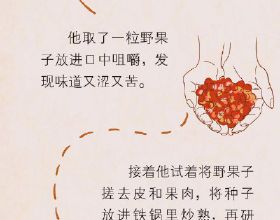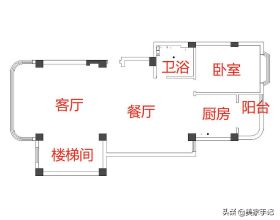落日慢慢的垂下,暮色中人們忙亂地搭起了帳篷,然後都陸續地進入帳篷內,老門頭和幾個士兵把駱駝和馬匹都安頓好了,也鑽進了帳篷。
一支燭光下,常貴照常挨個給每個人發一點水,大家邊喝水邊啃著乾糧,老門頭繼續講著古老而又古怪的故事,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力。“在很多年以前……”他說。
曹果子突然打斷他的話:“你總是說很多年前,到底是哪一年啊?”老門頭嘿嘿一樂:“這我哪裡曉得,還是我爺爺的爺爺講給我爺爺聽的。”眾人大笑。
入夜,人們和衣而睡。另外一頂帳篷內還亮著燈,人影晃動。洪福生心事重重:“司徒大人,阿布列和莫依他們能找到水嗎?”
“會的,會找到水的。”司徒旺堆說。
望著司徒大人非常自信的樣子,洪福生先前懸著的心才慢慢的放下。
帳篷外面一片漆黑,風小了許多,夜幕上的星星東一簇西一簇發出珠寶一樣的光澤,怎麼也照不亮這一片廣袤的天地。和白天酷熱相比,晚上的氣溫跌到了極點,感覺整個人就像掉進了冰窖裡,好在駝隊早就備足禦寒的棉衣、被褥和睡袋,大家又都擠在一起睡,帳篷內溫暖得像火炕。
三天後,出去找水的三個人一直沒有回來,此時駝隊已經陷入極度困境之中,吃的乾糧還能維持一段時間,只是喝的水就剩下一點點了,原來每人每天還能喝上一小壺水,現在一壺水每人每天輪流喝上一口。絕望和恐怖烏雲籠罩他們,幾乎所有的人都動搖了,而司徒旺堆卻異常的鎮定,當有人問起水和阿布列他們的時候,他總是信誓旦旦地說:“快了,阿布列他們很快就會回來了,水也會有的。大家再堅持一兩天時間!”
很快一天又過去了,夜幕再次降臨。
洪福生在帳篷內焦躁地走來走去,嘴裡喃喃著:“司徒大人,都這麼多天過去了,阿布列他們會不會出事了?”
司徒旺堆連連搖頭:“不會的,別看阿布列這麼年輕,卻是個經驗非常豐富的老向導了,他十幾歲的時候就跟著東西南北的馬幫和駝隊一道徒步過大漠,朝廷是不會看錯他的。”
“可是,可是司徒大人你有沒有發現這些天有好多人開始動搖了,他們都在私下裡議論,說阿布列他們已經逃走了,現在我們喝的水就要完了,都要死在這裡了。”洪福生還想繼續往下說,司徒旺堆猛地打斷了他的話:“胡說,誰再敢胡言亂語,定斬不饒!”
見何若秋和洪福生都耷拉著腦袋,司徒旺堆話鋒一轉,語氣緩和了一些:“臨出發前,朝廷的雷大人曾經親口告訴我,他說大漠深處確實有一條嘎拉木河,水源很豐富,人稱‘不死的河’,因為它的大部分河床都已經陷進大漠下面,只有極少部分的河床露出來,一般人是很難發現它的,不過對於像阿布列這樣有著極其豐富經驗的老向導來說,還是能夠找到它的。”
司徒旺堆稍微停頓了一下,艱難地嚥了一口吐沫,接著說:“雷大人還特別面授我機宜,他說阿布列是大漠裡的一支神狗,朝廷曾經花重金僱傭用過他好多回都能化險為夷,而這一次更不例外!洪都頭,你和何若秋都是朝廷的重臣,此次出征乃事關重大,關鍵時候你們一定要守得住哇,要告誡和曉諭那些鼓惑人心者,經常安撫他們那顆騷動的心哦!”洪福生和何若秋聽了不住點頭。
夜色闌珊,一輪彎月高高懸掛在天空,皎潔的月光下,大漠像是被抹上了一層奶油,夜風徐徐吹來捲起細小的砂石吹打著牛皮帳篷,發出咕咚咕咚的聲響,像部落族人在篝火堆裡歡快地敲打著羊皮鼓。陣陣寒意襲來,刺骨般的陰冷,似乎有人拿著牛耳尖刀往你的骨頭扎,疼痛難忍。好在大家都躲進了帳篷內,又相互依靠在一起,用彼此的體溫取暖。
幽暗中車布提和都爾輥鬼鬼祟祟從一頂帳篷內鑽出來,當他們看見站崗計程車兵走來走去,忙又像烏龜一樣縮回了腦袋。車布提小聲罵道:“鬼妞兒,現在咱們動手怕是晚了吧,那個該死的阿布列又不見了。”
“那現在怎麼辦,我們不能眼睜睜地等死呀?”都爾輥急得抓耳撓腮。
車布提看了他一眼,咬著牙說:“現在就是殺了他們,我們也逃不出大漠的魔掌呀,要不是司徒旺堆放跑了阿布列,我們早該動手了。”
沉默了一會兒,都爾輥眨著小眼睛,低低地說:“不晚,我們現在就動手,把那個看管黃金和珠寶的何若秋和常貴幹掉,然後挑兩匹好馬逃走。”
車布提翻了翻白眼:“往哪兒逃?”
都爾輥嘿嘿笑道:“老提子,你咋不開竅呢?我們去找嚮導阿布列啊!”聽他這麼一說,車布提眼睛一亮,他把牛耳尖刀在靴子上蹭了蹭,說:“行,就依你說的,今晚就動手!”
所有帳篷內的人都已睡下了,司徒旺堆微合著眼睛卻怎麼也睡不著,心裡總想著阿布列和莫依,猜想著他們是不是找著水了?先前洪福生和何若秋的一番話以及眾人內心發生的跌宕,讓他無不擔憂,朝廷委他以重任,像一座大山壓得他喘不過氣來。此次他也是頭一回出征西域,雖說出發前信心十足,可如今卻前途未卜,他感覺好像一下子陷進了無底深淵,而難以自拔。
夜深了,另一頂帳篷內,洪福生同樣也是憂心忡忡,朝廷派他和何若秋來主要任務是全力協助司徒大人出訪西域諸國。現在大家都走到了生死攸關的盡頭,是生是死誰都難料?他的內心充滿了焦慮和不安。好不容易有了一些睡意,誰知剛合上眼睛,耳畔忽然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響,他猛地一睜眼,把頭伸到帳篷外,就見不遠處的月光下有三個鬼影在蠕動。他的心頭升起了一團疑雲,嗯?這個時候還有人沒有睡覺,他們想在幹什麼?他滿腹狐疑提劍在手悄不聲地探出帳篷朝黑影快步走去。
都爾輥和馬祖強各提刀槍跟著車布提向存放馬匹和珠寶的帳篷靠近。“快,動作要快,趁著那幫傢伙睡死了,幹掉他們!”車布提催促著。三個鬼影快要接近帳篷了,馬強突然小聲叫道:“不好,後面有人追來了。”
都爾輥和車布提回過頭來看,頓時慌了手腳。那個追過來高高大大的影子,分明就是副統管洪福生,這個人不僅精明能幹而且武功非常了得,如果一對一的單挑,三個人肯定不是他的對手,不過如果三個人加在一起要夠他都統喝上一壺的了。雖說洪福生武功超群,但是這三位也不白給,他們可都是朝廷千里挑一給挑出來的,那都武林界的精英,只不過眼下他們真不想跟他糾纏在一起。還是車布提反應快,他喊道:“快搶馬跟我走!”說著他搶步上前手起刀落砍倒了兩個正在打盹的哨兵,抓起韁繩飛身上了一匹馬就逃,都爾輥和馬祖強也不含糊,各搶得一匹馬跟著車布提向北逃去。與此同時,洪福生也已趕到了,他看到躺在地上的兩個哨兵,再看前面三個騎馬的人影,頓覺事情不妙打馬緊追過去。
涼涼的月下,四條黑影一前一後展開了一場拉鋸戰,最終都爾輥被洪福生給追上了,只幾個回合就被洪都統給生擒活捉了。為了搭救同夥,車布提和馬祖強掉轉馬頭,向洪福生展開了圍攻。一時間刀光劍影,喊殺聲震耳欲聾,都爾輥趁機逃脫,操起手裡的一杆長槍刺向洪福生。三個人與洪福生又是一場生死對決,勢均力敵一行人只殺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車布提喘著粗氣喊道:“洪都統,你就放了我們一馬,咱們井水不犯河水。”
洪福生破口大罵:“啊呸,你們這幫逆賊,朝廷對爾等不薄,爾等竟恩將仇報,我豈能放過爾等,快跟我回去,還有生路,否則死路一條!”
“啊呸,姓洪的,你算個什麼東西,大爺給你退路好讓你借坡下驢,你卻不認好歹,今天不是魚死就是網破,來吧!”四人追追打打,打打追追越行越遠了。
下半夜,司徒旺堆剛睡了一會兒。突然帳篷外查崗的葛木雷匆匆闖進來,慌慌張張地喊道:“啟稟司徒大人,大事不好了,洪都統和車布提等眾人不見了,他們可能是逃跑了。”
“怎麼可能?”司徒旺堆笑道。
葛木雷一本正經地說:“千真萬確,司徒大人,都已經過去快兩個時辰了,也不見他們的蹤影?而且看管馬匹的兩名衛兵也被殺了!”
司徒旺堆一驚:“走,快引我看看去!”
他們剛走出帳篷,迎面就見曹果子怪叫著跑來:“啟稟司徒大人,了不得啦!”那叫喊聲比夜貓子哭還難聽,讓人毛骨悚然渾身起了雞皮疙瘩,他的身子和聲音都在顫抖著。
司徒旺堆不免又是一驚,問:“怎麼啦,曹果子?’
這時帳篷裡所有的人都被他的怪叫聲給驚醒了,人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紛紛鑽了出帳篷,驚慌使他們忘卻了外面的寒冷。
曹果子驚恐萬分,嘴裡繼續結結巴巴:“司,司,司徒大人,你,你,你看前面是個什麼玩意兒,黑咕隆咚的?”眾人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就見不遠處的天邊烏雲翻滾,那好端端的一輪月亮眨眼就不見了蹤跡,再看一團嘿呼呼的霧球正迅速的向四周擴散和瀰漫,眾人看那霧霾越看越像個巨大的惡魔,就見它張開黑咕隆咚的大嘴巴,彷彿要把這世間萬物一口吞吃掉......
“不好,快逃命吧!這就是傳說裡的大漠魔障!”老門頭最先做出判斷,他驚叫著拉起一匹駱駝就逃,眾人隨後跟著他一起望風而逃。
司徒旺堆氣急敗壞揮舞著長劍就追:“好呀,老門頭你竟敢妖言惑眾,我定斬了你!”話音未落,就和眾人被那個龐然大物給吞噬了。
中國淮安姚莊村 姚荔春
選自姚荔春編著的長篇小說《西風吹雪》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