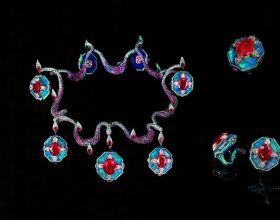宋雲奇
午夜難眠。一群雞婆撲稜進腦仁,咯咯嘎嘎叫得歡暢。霎時回到兒時老家,看見每日清晨雞叫三遍,天麻麻亮,母親走出屋門,開啟窗外的雞舍。那些蜷臥一夜的雞們,便嘰嘰嘎嘎躥蹦而出,然後四散開來,開始在院子裡刨土覓食。
那隻赤冠金羽的公雞,最是興奮,出窩就追著雞婆中一個靚妹談情作愛。然後無比愜意地扇動翅膀,哏哏哏地引頸高歌,好像享受愛情的歡愉。雞婆們聚攏來,圍著那隻剛才享受愛情,還有點嬌嬌欲羞的雞妹,交頸私語,似乎在交流愛情的感受?
我雖然羨慕那隻靚麗威武、妻妾成群的公雞,然而心裡最喜歡、最感恩戴德的,卻是那群貌不驚人的雞婆。因為,她們是我家零星花銷的小銀行,是我上學讀書的保護神呢!
20世紀60年代初,農村還是生產隊。除了集體,農戶不能養牛羊,只能養少量雞鴨鵝等。一家的大開銷,靠父母掙工分,年終分紅,平時零花錢,就靠“雞銀行”。
鄉下養雞,開始是賒。每年春天,賒小雞的賒雞販兒,一條扁擔兩隻籠,無數的小雞,嘰嘰啾啾,扎堆擁簇,任人挑選。當時賒賣,秋天按成活率收錢。母親挑了二十隻小雞,秋天存活十隻,四公六婆。後來雞婆長大,就讓雞婆自己孵蛋,繁養小雞了。
孵雞的雞婆是特定,發現哪隻繁蛋雞婆繁,忽然不思飲食,蓬鬆羽毛,精神萎靡,懶散嗜睡,就是想“坐月子”了。這時先要挑選雞蛋。母親選蛋時,用手罩著雞蛋,對著光線,挨個B超透視,確定哪個是受精欒。挑好後,將其擺好在雞窩裡,“坐月子”的雞婆就會輕臥上去,蓬鬆翅膀,將雞蛋全部覆蓋,用體溫進行孵化。大約二十來天,稍長或稍短。雞婆就那樣臥在蛋上,一動不動,直到一隻只小雞啄破蛋殼,來到世間。
看著新孵化的小雞,五顏六色,毛茸茸的樣子,忍不住想去捧玩撫摸。母親卻只讓看,不讓摸,說摸了會長不大。而且還有“雞媽媽”看著呢,你一過去,她就炸了翅膀,昂頭瞪眼咯咯咯地叫,讓人發憷,不敢近前。
小雞長大後,要先將公雞賣掉或殺了,就留一隻護群。那時鄉村養雞,不像現在只為吃用,而是為了“攢蛋換錢”。雞婆下蛋,要攢起來,換醬醋油鹽,跟“撥浪鼓兒”換布頭線腦兒。當然最重要的,是攢了給我交學費啊!
因此,我最愛聽繁蛋雞婆“咯嗒咯嗒”的歡叫。那是生育的快感,那是勝利的歡歌!一聽到她們“咯嗒咯嗒”,我就格外興奮,放下書包,跑到雞窩,將帶著雞婆體溫的新蛋輕輕收起,小心翼翼存到抽屜裡。
記得有次交學費,也不多,三塊錢。全班幾十人,就剩我跟幾個同學了。老師催我,我回家催母親。母親說,雞蛋還不夠,叫老師緩幾天。如是幾回,老師惱了,你們幾個,再交不上,別上學了。我當時就嚇哭了:老師,俺想上學,想當幹部。俺家派飯的幹部,都是四個兜,上衣兜還插著鋼筆哩!聽母親誇我學習好,我在心裡哭喊,卻不敢對老師說。放學路上,才扯開喉嚨哭起來,一路直哭進家門。
母親問明原委,笑了:老師嚇你哩!咋能不讓你上學哩!別掉金豆兒啦!快去抽屜數數,多少雞蛋了。給你借了十來個,估計差不多了。我破涕為笑,忙去數蛋。一數,五十九個,一個雞蛋五分,兩塊九毛五,還差一個雞蛋啊!我又撇嘴想哭了。母親說,就知道哭!快去摸摸“雪裡白”的屁眼兒,看她今兒有蛋沒?
“雪裡白”是隻最幹活的雞,每天繁蛋不落空。昨天繁過蛋,今天還沒呢!一聽母親的話,趕忙跑到院子裡。“雪裡白”正在院裡悠閒覓食哩!我躡手躡腳走近,伸手抓住她。學母親的樣兒,一手抓住翅膀根兒,一手食指進屁門兒,果然有個硬硬的“圓”。
心裡有了底,就等她下蛋。當天傍晚,都沒吃出夜飯啥滋味,匆匆放下碗,就靠著堂屋門,痴等著“雪裡白”繁雞蛋。直到太陽落,雞們都跳上雞舍歇息了,“雪裡白”才好像憋不住,惶然跳進堂屋門,走到門後的雞窩裡。
一陣難熬的等待。終於聽到咯嗒咯嗒的歡叫,我忍不住喜出望外,蹦跳入屋,將“雪裡白”一把抱起,在她臉上親了一口,然後捧起那枚白白亮亮、依然帶著熾熱的新蛋,放進已裝有五十九個雞蛋的竹籃,飛也似地去了村裡的代銷點。
次日清晨,我去上學走時,先替母親開啟雞舍,給“雪裡白”餵了一把糧缸裡的麥粒兒。母親看見,揚手就打:你鱉娃子!那是秋後的麥種吶!叫你爹瞅見,看不慣你。我嬉笑著起身,揣著湊夠的三塊錢飛奔而去,終於去學校把學費交上了。
如是幾年,年年如此。是“雪裡白”和她的同伴下的蛋,幫我完成了小學學業。
時光荏苒,歲月更迭,“雪裡白”和她的同伴逐漸變老了。雞婆變老就下蛋稀少了。母親又買了十幾只小雞。那些逐漸不下蛋的老雞婆,就被母親剪了翅膀,綁了腿腳,分別拿到集上去賣。也有節日或者來客,被父親殺了炒吃的。
看著這些曾為我和我家無私奉獻的雞婆,被繩捆索綁地賣掉;看到她們被父親的大手攥住翅膀和脖子,鋒利的菜刀割破喉管,血流噴射如泉,漸漸變成線流、點滴,直至流盡。然後扔在地上,居然還能掙扎著站起,撲扇著翅膀,在院子裡東倒西歪地奔跑,最後撲稜不動了,才頹然倒地。母親這時端來熱水,將雞們放入,浸泡,拔毛,開膛,然後刴碎、烹炒……我真是傷心氣憤之極!怎麼會這樣呢?怎麼能這麼待她們呢?傷心和氣憤,讓我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母親見我情緒低落,給我講了很多“家禽家畜就是給人吃的”大道理,但我就是聽不進去。
“雪裡白”雞婆中最後一個遭厄運。那天公社又來幹部,隊裡派到我家。晚飯沒葷菜咋整?只好把“雪裡白”殺了。我下午放學回家,正趕上父親磨刀殺雞。不由衝上去奪過“雪裡白”,緊緊抱在懷裡。母親勸說我不聽,父親搶奪我不給。一向性格犟硬、在家裡說一不二的父親惱了,劈手一個耳刮子,打得我一個趔趄,摔倒地上,懷裡的雞也被他拽走了。我從地上爬起來,突然淚流滿面,對父親罵了一句:劊子手!然後朝院子外跑去。
這是我第一次跟父親犟嘴,也是我第一次罵父親!我當時真的對父親惱怒之極,恨之入骨。恨他鐵血沒有人性,恨他沒有悲憫之心,恨他沒有半點親情溫情。
我從院子裡跑出去,一邊稀里呼啦地大哭,一邊在曠野裡沒命地奔跑。我也不知道跑向哪裡,更不知道我到底要幹什麼。我想跳山崖,我想跳水塘,但我最後都沒跳。而是跑到隊裡麥場後面的一個坡凹裡,坐在那裡哭了一陣,然後累了,就躺在那兒睡著了。
忽被一陣咚咚的腳步聲驚醒,懵懂中抬頭,父親正滿面怒容地站在面前。我預感這回又要捱揍了,而且比剛才那個耳刮子更狠,因為我罵了父親。然而,父親的怒容僵硬了一會兒,面部格蹦蹦跳動幾下,卻幻變為勉強的笑意。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明顯看出他的盛怒已達極點,為什麼突然向我讓步妥協了?是不是我的“離家出走”讓他害怕了?萬一出個意外怎麼辦?我想在父親的心裡,兒子的分量,肯定比一隻雞婆重得多啊!
心裡這麼想著,父親已輕輕把我拉起,拍打著我身上的灰土說:就知道你沒跑遠。走吧,咱回家。那隻“雪裡白”咱不殺了,啊!聽完父親的話,原有的怨憤仇恨煙消雲散。我忍不住嚎啕大哭,然後被父親拉回家了。此時開始,我原諒了父親。
回到家裡,我抱著“雪裡白”又哭了一場。她偎在我懷裡,眼圈紅紅地看著我,喉嚨不停咕咕咕地叫,嘬尖輕啄著我的手。她是在感激我的救命之恩嗎?
西方神話裡有天使,生有雙翅,能飛到你身邊和心裡,讓你實現美好的心願。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女媧與精衛,也是救人解難的天使。而在我的少年時期,與我親密相處,並助我上完小學的那些雞婆,西方神話裡有天使,生有雙翅,能飛到你身邊和心裡,讓你實現美好的心願。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女媧與精衛,也是另類救人解難的天使。而在我的少年時期,與我親密相處,並助我上完小學的那些雞婆,她們就是為我排憂、急我所難的天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