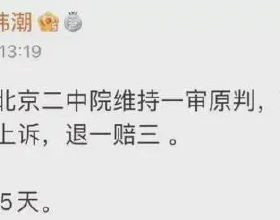“命”是什麼?
人,喜歡問“為什麼?”而在眾多“為什麼”中,又以個人在這個塵世的生死、禍福、貴賤、窮達等所衍生出來的“為什麼”最讓人縈繞於心。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行者常至,為者常成”、“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等古老的格言告訴我們,最大的決定因素在於“自己”。但人生的實際閱歷卻也一再提醒我們,它們往往和個人的才智、努力、德性、作為不成比例,而似乎有超乎這些的其他決定因素。
這些超乎個人的其他決定因素,即被我們的老祖宗籠統地稱之為“命”。所謂“君子不以在我者為命,而以不在我者為命”,“命”指的是並非自己能決定、但卻能決定自己生死禍福、貴賤窮達的各種因素。所謂“人受命乎天”,古人認為這個“命”是由“天”決定的(故亦稱為“天命”);而所謂“天”有兩個含義:一是人格化的“天”,它指的是“神的意旨”;一是非人格化的“天”,它指的是“自然奧律”。因此,在廣泛的定義裡,凡是超乎個人的決定因素,不管是出於“神的意旨”或來自“自然奧律”,都屬於“命”的範疇。
所有的天機或命運物語都是對“命”的揭露。而在這種揭露過程中,中國古典命定論的各種內涵——包括它的理論基礎、判讀方法、說服策略、文化特色、心理及社會功能等也都跟著一一顯現。本章想先從前面所舉的故事來探討一個基本問題——中國人的“命觀”,也就是我們的老祖宗認為“命”具有什麼本質,以及對“命”抱持什麼態度的問題。
天命不易與天命靡常
命的“本質”不會自行顯現,我們只能從被揭露的命裡來加以理解。
觀點一認為,命具有必然的、不變的本質,而這也正是《尚書》裡所說的“天命不易”——命之所以為“命”,正表示它是“半點不由人”的,不會因人力的介入而有任何的改變。就壞的一面來說,這種必然性雖然予人一種受擺佈的感覺;但就好的一面來說,因為命的“不易”,所以它也是“可信賴的”。
但另一觀點卻是另一番景象:命並非人所自以為是的那樣必然,它其實是無常的。而這也正是《詩經》裡所說的“天命靡常”——神的意旨或自然奧律不是一成不變的,它變化莫測。就壞的一面來說,這種變化莫測給人一種不可信賴、無所依循的感覺;但就好的一面來說,因為命的“靡常”,而騰出了不少轉圜的空間。
這兩種觀點看似矛盾,但卻同時存在。此一矛盾存在,在更深的意義上,正代表了中國人對命的“雙情態度”。因為有“天命不易”的觀念,使人興致勃勃地想要“窺天命”,而如果窺探到的玄機無法兌現,則可自我解嘲地將它們歸諸於“天命靡常”。反之,因為有“天命靡常”的觀念,使人覺得應該要多“盡人事”,而在徒勞無功、受到挫折後,又可自我安慰地將它們歸諸於“天命不易”。
具道家色彩的“安命觀”
不管命的本質是“不易”還是“靡常”,重要的是人要如何與命互動,而這就涉及“態度”的問題。
第三種觀點,則是有著濃厚的勸人“安命”的氣息。很多人無法體認那是自己“命中無份”的,竟然還刻意營求、強行索取,最後只能落得白忙一場、徒增煩惱,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相反,知足常樂,回絕了可能的榮華富貴,則會得到另外的豔羨。
一些修行者,“命理高手”,在知道自己大限已到時,並不像一般命理學家汲汲營營於為別人或替自己“改命”、“蓋運”,而是安然處之,臨死不懼,把握人生的最後時光,開懷暢飲。雖然安於無情而殘酷的命運,卻反而給人一種超然、灑脫的感覺。
這種“安命觀”,具有濃厚的道家色彩。道家承認命的存在,但就像老子所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在冥冥中決定萬事萬物的天地大力,是無親而又無情的,一個人面對它的良策是“無為”、“虛靜”、“棄智”這些反求諸已的心靈脩為。所謂“無欲則剛”,在殘酷的命運面前,人若無所營求,不為所動,即能獲得心靈的自由。他並不贊成人們去窺探命,因為他說:“先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想要預見事情的發展,所得到的只是華而不實的表象,但卻是愚蠢的開始。
莊子也有類似的觀點。他主張人“無以故(巧謀)滅命”、“去智與故”,又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德之勝”。這種“勝利”看似有點阿Q,但如果一個人能不在意命,不受它的干擾,則“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確實也是一種“精神上的勝利”。
終極而言,死亡是生命中最必然、也最難以超脫的“命”,你再如何費心營求、如何神機妙算,終歸是難逃一死。我們惟有“安然處之”,才能得到解脫。
具儒家色彩的“立命觀”
儒家的“立命觀”鼓吹的則是一種比較積極的態度。雖然一方面“信命”,但是透過各種積極的德行、學習可以改變“既定命運”。對此,提出了另一套說辭,所謂“理未易明”,不管你被告知的是什麼“命”,凡事“盡其在我”總是沒錯的。而所謂“盡其在我”,是“做應該做的事”。
這樣的態度,是比較傾向於儒家的,我們可以稱之為“立命觀”。孔子曾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說:“五十而知天命”,但這個“知命”並不是去“知曉神的意旨或自然奧律”。《朱子集註》曾引程子的話說:“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因此,孔子的“知命”只是“相信命存在”而已。孟子雖然曾說:“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但這也表示不要故意和可能的危險命運作對而已,他同樣未觸及命的內涵與運作法則。
讓儒家表現其特色的是“立命”,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在不是人力所能決定的命運之前,儒家強調“修身”、“盡其心”、“盡其道而死”、“知其不可而為之”,成就一種光輝的人格。我們可以說,將生死禍福、貴賤窮達委之於命,不患得患失、也不刻意營求,是儒家與道家相似的地方,但主張凡事盡其在我,讓個人的才智和仁義之道獲得最大的發揮,則是儒家有別於道家的“立命觀”。
陰陽五行家的“窺命觀”
“窺命觀”是一種更積極、也更為國人所熟悉的態度。想經由“窺探天機”以博取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的熱切之情:諸如按照某種預示取名博取富貴,進行某種禁忌。
“窺命觀”,讓人想起的是在春秋戰國時代與道家、儒家分庭抗禮的陰陽五行家。所謂“窺命”就是要像《易經》所說的“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找出神的意旨或自然奧律背後的運作法則以及判讀它們的方法,然後知所趨避,有所運用,以增進個人及集體的福祉。
很顯然的,它比道家的“安命觀”或儒家的“立命觀”都具有更大的實用性,而且也因為它把“命”當做一門知識來研究,所以也比前兩者具有更大的發展性,而在春秋戰國時代以後,陸續發展出各種體大用繁的理論和方法,積澱成一個非常龐雜的知識體系,成為筆者所說“中國古典命定論”的主要內涵。
三種命觀,三種自由
事實上,還有第四種態度,也就是以墨家為代表的“非命觀”,但為免治絲益棼,這種不承認命存在的態度,我們留待後面相關篇章再談。基本上,在承認命存在的前提下,中國人對命所抱持的就是“安命”、“立命”與“窺命”這三種態度,它們多少跟前述“不易”及“靡常”這兩種“天命”本質在個人心中所佔的比重及如何統合有關。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三種態度也可以說是在反映中國人於命運的陰影下,所渴望的三種“自由”。
人是相當矛盾的,一方面相信“命定”,一方面又渴望“自由”。其實,不管是道家的“安命觀”、儒家的“立命觀”或陰陽五行家的“窺命觀”,都是對“命定”與“自由”所做的不同形式的統合。哲學家斯賓諾莎曾說:“自由乃是對必然性的一種體認”,我們在體認了必然性(命定)後,要“選擇”和它維持一種什麼關係,才是“自由”的範疇。以此觀之,道家在體認人的生死、禍福等“必然”會受到某些因素的擺佈後,它選擇“安時處順”,以獲得個人心靈的“自由”。而儒家在體認同樣的“必然性”後,則選擇“盡其心”,以維護自己人格的“自由”。至於陰陽五行家則是在做了同樣的體認後,選擇“窺探”它、“運用”它,以期獲得追求個人福祉的“自由”。
這三種自由同樣為人所需要,所以事實上,前述的三種命觀也同樣為中國人所需要。當然,一個人要安命、立命或窺命,可能需視當時他渴望的是什麼自由而定。
民間百姓心中的最愛
通常,三種命觀的同臺演出。
由一個高明的窺命者來頌揚安命觀和立命觀,似乎表示“安時處順”與“盡其心”比“窺探天機”具有更崇高的價值。但在故事裡,最讓人“動心”的卻很可能是能讓人鑑往知來、趨吉避凶的窺探天機能力。
事實上,道家的安命觀和儒家的立命觀雖然“不錯”,但絕不是民間百姓心中的“最愛”。我們可以說,在這方面,儒家和道家都錯估了人性,因為一方面承認命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叫人不必理會它、不要窺探它,而只需在個人修為上下工夫,這不僅“低估”了人們的好奇心(求知慾),同時也“高估”了人們的德性,而這正是儒道兩家所共有的致命傷。在反映民間百姓心靈樣貌的明清筆記小說裡,勸人“安命”與“立命”的故事,寥寥可數。
多數民間百姓渴望的並不只是將生死禍福、貴賤窮達委諸於命而已,他們更希望知道(至少是有人能告訴他們)關於命運作的各種法則及判讀方法,以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和求知慾,並進而利用這些知識來追求幸福和財富,以滿足他們並不怎麼高尚的德性。在這方面,他們具有無比的決心和毅力。
中國人“窺命”窺了一兩千年,所窺出來的各種名堂,以後有機會給感興趣的介紹。
節選自:王溢嘉《中國人的命理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