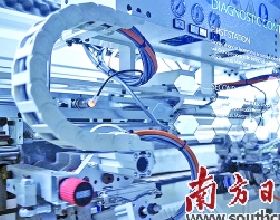我可以一直幻想,世事有常,歲月靜好
張山東的名字是來東北起的。小地方一有外來人,聽了口音,名字就有了。張山東也是小城最早收破爛的,所以,因職業又有了新名字:張破爛。這麼叫倒沒有貶意,主要是誰家有廢品,找張山東找不著,提張破爛就有了。山東還是小城裡為數不多的、還在使喚毛驢兒為運輸工具的老人家之一。
張山東原來用手推車,說自己推不動了,才買的毛驢兒。每天早晨,都能看到張山東跟著毛驢車走在大小街巷。問他怎麼不坐車,他說驢累。聽話,足見張山東有多心疼他的小毛驢兒。張山東走一段,便扯著嗓子喊幾聲,跟著打一聲歘。他手上的那個歘可是有年頭了,打我記事起,就聽著它響,別人換了喇叭,他還是打著他的歘。
每次見到張山東,總有時光停滯的感覺,尤其是他身上的那件復古的四個兜的幹部服,穿舊了,穿爛了,再換一件還是那式樣,再終日操著一副亙古不變的山東口音,沒有時空來去之感,彷彿前世今生都是可以自由穿越的。
張山東有句說辭常掛在嘴邊,收破爛不叫收破爛,叫換個饅頭吃吃。張山東這個饅頭一直在換,越換越大,兩個兒子娶了媳婦, 一個閨女嫁了人,現在,又在小街正中心,給小兒子換了個大飯店。日子過成這樣了,日日見了,嘴裡還是那句,嗯咽,換個饅頭吃吃。
張山東能掙錢,明擺的事,但是,他的老伴對他卻是一嘴的撅詞。張山東不給媳婦錢花,錢在家裡到處藏,不給錢的理由是媳婦有錢就買藥,並一再地申明,藥不是好東西,會吃壞人的。
張山東媳婦確實有亂吃藥的毛病,聽個偏方就去買,價錢還賊貴,而吃了又不見好。因此深知賺錢不易的張山東把錢看得死死的。張山東媳婦也有句口頭禪,張山東是換個饅頭,媳婦是渾身上下麻木疼。麻木疼是什麼疼,張山東媳婦也說不清楚。
老夥伴們一起鍛鍊,別人越走越熱乎,張山東媳婦越走越冰冷,走到最後連知覺都沒有了。天冷了這樣,天熱了也這樣,夏天時和張山東媳婦說話,感覺身邊站著個空調。張山東說,就這,藥都吃了一驢車了,能見好也值呀。
張山東媳婦生氣,氣老伴不疼她。但是,念在張山東一輩子沒讓她賺過錢,多大的抱怨也就是嘴上說說。老伴不給錢,不是還有孩子們給嘛。張山東媳婦做飯有一手,張山東也好伺候,尤其是,只要有饅頭吃,頓頓都是飽飽的。張山東是山東人,山東人習慣吃麵食,所以將“饅頭”兩字掛在嘴邊,可能不只是喜歡吃,興許是張山東內心的另一種懷鄉呢。
不管怎樣,張山東都算是小城裡的名人了。有次市裡電視臺有個節目,主題是尋找人生路上有特殊貢獻的人物。我把張山東推薦了上去。電視臺的領導當即拍板,採訪車跟著就來了。結果,事情卡在張山東的小兒子身上。
張山東那個當了飯店老闆的小兒子說死不同意老爸上電視。本來張山東都準備好換掉身上那件彷彿長在身上的工裝了,甚至連表情都在我的面前做了預演,但是,兒子從中做梗,張山東也沒擰著。一個本來可以在人前露臉、翻身的機會就這麼在兒子強硬的態度中像火花一樣熄滅了。
感覺,不管張山東多有錢,似乎都是以一種乞丐的心態活著。有一次有個挺牛的人,開個破車,因為張山東的驢車不是故意地擋了他的路,衝著張山東劈頭蓋臉就是一頓罵。張山東被罵得一臉懵。但他不爭辯,點頭哈腰,一路小跑,趕緊將自己的驢車牽走。嘴裡還一個勁地道歉,我就是個撿破爛的,我就是個撿破爛的。
大約在張山東小兒子的心裡,對父親的定位也是撿破爛的吧,所以禁止父親出鏡,以防在不知情人的眼裡丟了名聲。可是,小城能有多大啊,不偷不搶憑勞動賺的錢有貴賤之分嗎。想來,關於出身,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對的吧,世上最幸運的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人,而能輪到這樣機會的人太少了。
因為張山東沒有上上電視,我心裡還彆扭了一陣兒,出去吃飯都躲過張山東小兒子家。我對張山東上電視一直充滿期待。張山東除了有賺錢的本事,他還是個蠻有戲劇天分的人,自創的舞蹈能笑倒一街筒子的人。秧歌隊裡,只要有張山東在,誰的手腳也別想放在正確的地方。張山東在聽說自己可以上電視的時候,還弱弱地問了人家一句,可以上電視裡跳舞嗎。
現在,每天早晨還是見張山東跟著驢車出去換饅頭,一身破衣,兩隻舊鞋,一嗓子吆喝,一個歘,有張山東在,小街的時光彷彿就停在舊事裡,張山東不變,小街就沒有變,我就能看見自己的小時候,長大了以後,和變老之前。只希望張山東這個光陰的背景一直都在,我可以一直幻想,世事有常,歲月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