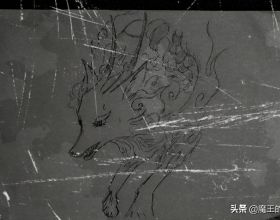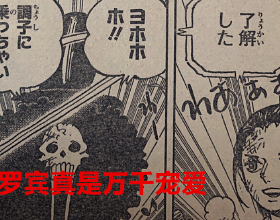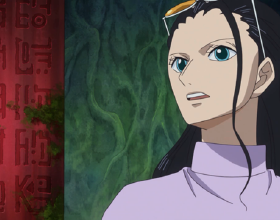古人講究道德與文章並稱,即做人要品德高尚,著文要文品至上。在社會生活中,雖說做人不一定要撰文著書,但做文卻一定要先學做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注重自身的人格修養,追求文品與人品的高尚統一,為歷代仁人志士所推崇。
偉大詩人屈原飽受凌辱,殘遭流放,乃賦《離騷》,始終不忘“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表現出了“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堅守正直,恪守高潔,一心向善,九死未悔的人格寫照和可貴品質。西漢司馬遷因替李陵辯護而獲罪入獄,身受腐刑,依然不改襟懷坦城、剛直不阿的為人精神,秉筆直書《史記》,被世人譽為“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成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實現了人文合一的高風亮節。另外,還有詩人杜甫憂國憂民的無限情懷;文天祥大義凜然、堅貞不二的報國之志;魯迅先生“橫眉冷對千夫指,腑首甘為孺子牛”的愛增分明等等。如果說是時代造就了他們正直坦言的品格,那麼嚴肅的社會責任感和自覺的歷史使命感則是成就他們文章不朽的根本。正如陸游在《上辛給事書》中說的:“君子之文也,如日明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文如其人,貴在為人。為文於世,止於文以載道,然人格不立,何能載道於文?但是話說回來,畢竟為文又不同於為人,為人是直截了當觀人品、看擔當;而為文則多是側重文章品德行、採優劣。難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古往今來文偽其人,人辱其文的例子早已屢見不鮮。那位曾為秦始皇統一六國效犬馬之勞的丞相李斯,文才不謂不好,他的《諫逐客書》鋪陳排比、音調鏗鏘和諧,下啟漢賦之漸。《論督責書》則文風峭刻,具有法家特點。可是論及人品卻是一個嫉賢妒能、貪戀富貴、品德卑劣、極端自私的陰險小人。恰恰是這些致命弱點,導致了他“持爵祿自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謫立庶”,最終落了個被腰斬咸陽,誅滅九族的可悲下場。也算是個大起、大落的悲劇式人物。據史料記載,明代嘉靖年間的大奸臣嚴嵩也很有幾分才華,從他作品中絕看不出其為人奸詐、貪贓枉法、作惡多端的蛛絲馬跡。他在一首《生日》詩中竟有“晚節冰霜恆自保”的佳句,足見大奸亦能為大忠之文。如今這樣的例子就更不新鮮了,“假作真時真亦隱,無為有處有還無。”把世人涮的辨不清真假是非皂白。
社會生活的複雜性和曲折性,自我表現方式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使為文的活動也變得光怪陸離、妙不可言。越發的文如其人與人如其文者少了,文偽其人與人辱其文者多了,若是一般的有失檢點,或口能言,身不能行,尚可稍恕,可卻是口言善、身行惡,南轅北轍,人前一幅衣冠楚楚、“豔若桃花”,背後一肚子男盜女娼、“潰爛化膿”,便大失了文人之德行,為世人所不齒。且時下,類似事情已經日趨成為某些職場小人欺世盜名的拿手把戲,他們作報告、寫文章、出集子,甚至組織御用文人、寫作班子,為自己樹碑立傳,巧取名利,或許塗抹出貌似華麗的篇章,卻只能譁眾取寵於一時,一旦人們曉其緣由,洞察其本來面目,報之的只能是無情的嘲諷。有的人是透過心靈描寫人生,有的人是包藏禍心偽裝人生。孰美孰醜?孰優孰劣,都將由歷史與實踐作出公正的評判。做為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文化活動,作為揭示心路歷程的一種精神產品,還是要大力提倡和遵從文如其人與人如其文的和諧與統一,那種人辱其文與文偽其人的事情最好少做或不做。背後讓人家指指點點畢竟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