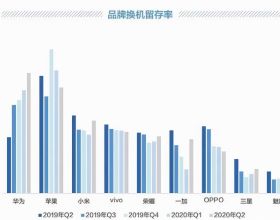師志輝
作者簡介;師志輝,陽峪鎮人。76年陽峪五中畢業後參軍,81年復員回家務農至今。閒暇無事,寫些小詩,苦練習書,他以顏真卿、柳公權、趙孟頫、褚遂良等名家楷書,又專修“二王”的行書、張旭懷的草書。他不僅學習楷書,在此基礎上又向行書、草書發展。他弄來《三十六法》《八訣》《用筆論》《傳授訣》等書論,勤苦學習,毫不鬆懈。他堅信蔡邕書論中“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利劍長戈,若強弓硬矢,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樂人樂己。
我於1959年出生。1967年還是1968年開始上學的,記不清了,反正就是八九歲的樣子。
小學一到四年級是在本村小學上的,因本村小學只有一至四年級。四個年級一個教室,一個老師。實行復式教學,即老師一堂課前半節教一年級,後半節教四年級。下節課再教二、三年級。
我們那時作業很少,基本上在課堂或自習課上就做完了。下課就去玩耍,回家從來沒有家庭作業。
學校只有一個老師,老師吃飯在學生家輪流吃管飯。那時候,經濟拮据,各家吃飽飯都成問題,輪到老師來家吃飯,家裡還千方百計給做著吃好的。但麥面很少,多半是玉米麵或高粱面。做時用麥面裹著玉米麵,還稱之為“銀裹金”。要麼就是玉米麵或高粱面攪團。
我家姐弟六個。前面兩個姐姐,大哥,二哥,三哥過繼給別人了。我就是最小的。
父母不識字,但自己再苦再累也千方百計讓孩子們都上了學。兩個姐姐小學沒念完就回家幫父母幹活養家了。大哥是老三屆初中生。初三遇上了“文革”就再沒上學。二哥和我“文革”後都讀完了高中。
我一到四年級是在本村小學讀完的,後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五年級。五年級在陽峪學校。那時學制是小學五年,六年級和七年級就是初中。就是陽峪初中了。
上了五年級,就要到陽峪學校去唸初中,在新的學校,也結識了新的同學。
記得五年級第一次數學考試,我糊里糊塗就考了個全班第一名。這下,原陽峪村的同學心裡有點不服氣。
究其原因,考試期間學校要開運動會,一些同學因參加訓練沒有參加數學考試,就和賽跑一樣,前邊沒有參賽運動員,慢著走也是第一名。
這虛榮的第一名成為我好好學習的動力。從此以後,我上課認真聽講,作業積極完成,在以後幾次考試中,數學每每取得第一。還參加了學校舉辦地五、六、七年級的數學競賽,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1972年底,五年級升初中,是全公社各校透過統考後才能升級的。
當年教育界提出復課鬧革命,學校抓起了教學質量。那時候,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教學要改革,教育要革命,”縮短學制,小學為五年,初中為兩年,高中也變為兩年,同時改秋季入學為春季入學。各級畢業時間從夏季七月份延長到了冬季的一月份了一畢業就是過年。
那個年代的考試,沒有試卷。考試題由老師用粉筆寫在黑板上,學生抄題答卷,基本都四大題或五大題。答題用時四十五分鐘。學生就在下面逐一抄題解答。那次升學數學試題是四大題,每題二十五分,百分卷。不知怎麼搞的,最後一題我竟然答錯了,沒有取得好的成績。依我記憶題目解答是對的,但考試下來透過和同學對正,我把題看錯了。
這次考試,幾個學校要聯評比賽成績。因我看錯題目,沒有拿到好的成績,學校也失去好的名次。我受到了老師嚴勵的批評。
從六年級到七年級,學校對教學質量抓的緊,我學到了許多知識,以至於現在都對那個時候的知識內容熟記於心。對學過的知識要點,至今都沒有忘記。所以也能對現在讀初中的學生,進行輔導,解答疑難問題。
那年升上六年級,學校把原先一個班分為甲、乙兩個班。我被分到甲班,語文老師是王志學,同時是班主任。
那年代上學,早起沒表看時間。睡上一覺醒來,不知時間,就起來去叫上同伴同學——同族中的小叔、小姑、哥哥、姐姐一路六、七人,步行五、六里路來到學校。經常是來到學校時,月光皎潔明亮,學校大門還緊閉著。就在大門外等著學校的大門開啟。過了不久,副校長董守德老師打著哈欠才出來開門。夏季還好,一到冬季,衣服單簿,一般人家孩子都穿一件老套子棉衣棉褲,不保暖,難擋刺骨寒風,個個凍得瑟瑟發抖。
初中畢業大約是1974年底,正是“四人幫”橫行的年代,講政治掛帥,升學已不再透過考試進行,而是實行政治審評,推薦升級。那一年我沒有被推薦上。當時我暗自在想,我家本貧農成分,父親又是老黨員,老革命,而我卻沒有被推薦升入高中,就奇怪了?
一氣之下,我也不念書了,剛十六歲就去關平溝參加生產隊修反坡梯田。
新年開學半月有餘,家門中一叔父前來換我,讓我回家前去陽峪中學,時稱“五中”(乾縣第五中學)報名上學。我的輟學,後來被村支書及公社書記知道,他們就給“五中”推薦了我,才使我得以繼續上學讀書。
高中兩年,在白卷先生張鐵生的影響下,讀書無用論的思潮風行社會。高中全年級四個班,分農業班,體育班,農基班,還有文藝班。我在三班農業班。班主任是徐啟民老師,大學時學的俄語,他由俄語教師改教語文。副班主任是鄭光遠,他是北師大高材生。先分到了乾縣羊毛灣水庫接受勞動鍛鍊,後調劑到北部偏遠的陽峪中學任教。教物理,我們全班有六十多名學生,我記憶裡比較清晰的同學有孫權利,王志軍,峰陽的有薛光煒、徐俊輝、陳述學、劉具縣、乙興龍杜林校、吳西峰。注泔有王文述,羅文遠等。那時男生女生基本不太說話,所以對女同學就很少有記憶。
當時,峰陽,注泔,吳店,梁山,鐵佛四個公社的學生都是住校生,陽峪中學在陽峪駐地,大部分是通生(跑讀生)。我家離校近有十里路,晚上住校,中午回家吃午飯。
住校生來校時背乾糧。家庭條件好些的每週就能背四、五個麥面鍋盔,不好的也有秋面饃,如高粱面饃,糜面槓子饃。學校也有學生灶,早上有玉米榛子,中午有稀湯湯麵,晚上開水泡饃。睡覺一班一個大房間,麥草通鋪。那時每人只拿一床被子,沒有鋪墊。倆人一合,一鋪一蓋。我和王文述合鋪。薛光煒和吳西峰合鋪......
那時,我家人口較多,生活困難,常年少吃沒穿。我上學經常拿的是秋面饃。饃熱了還能吃,冷了很硬,很難啃下。就這還時有時無。我經常得到王文述同學的接濟。他家情況好,一週來時就多拿一個鍋盔接濟於我。他對我的恩惠使我終生難忘。
那時學習抓的不緊,都不好好學。學校還緊跟政治形勢,經常組織學生參加勞動,走五七道路。組織學生到峰陽的五峰山,梁山的瓦子崗種莊稼。那裡山高地廣,土地面積寬裕,學校在兩地都有實習基地。我們時不時地前往五峰山、瓦子崗收種莊稼。學校距離兩地都有幾十裡遠,學生浩浩蕩蕩地步行著去。有時候一天時間還不能打回轉,就在五峰山腳下的黃村過夜。夜晚可以望見溝對岸的一片燈火,我們不知何地。就問峰陽的同學,同學答覆說對岸是“南坊”。南坊是禮泉縣北邊一個公社。當時我只知道祖國的江南統稱南方,不知溝對岸就是南方。哦,原來此“南坊”非彼“南方”。
記得在高二那年,學校又組織學生去五峰山林場植樹,白天在山坡上栽樹,說說笑笑,打打鬧鬧,還算熱鬧。到了晚上,就住在山上的破窯洞裡,點上蠟燭照明。山風吹來,光亮一閃一閃,弄不好就被野風吹滅。
山中蟲鳴鳥啼,特別是貓頭鷹的叫聲,非常驚恐。那叫聲一陣陣傳來使人毛骨悚然。天籟之音中夾雜著“嗚嗚”的幾聲狼嚎,人人心驚肉跳,徹夜難眠。
半月有餘,植樹活動結束。人人心喜若狂。
在回家的路上,鄭光遠老師帶隊,心情不錯,邊走邊唱起了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聽到的最好聽的歌。歌詞好,旋律優美。我就問起鄭老師,為啥這幾年沒有聽過這個歌?他說有人不讓唱,他這也是偷著唱的。叫我們要保密。這是1976年的事了。
1976年,中國發生了很多大事件。唐山大地震,中國三個偉人相繼去世,華國鋒成為毛主席的接班人。之後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我也在1976年年底臨近畢業的時候報名參了軍,那年我18歲。從此再也沒有機會進過學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