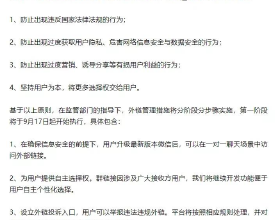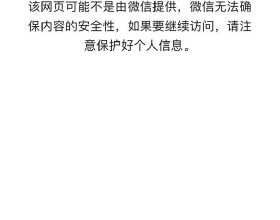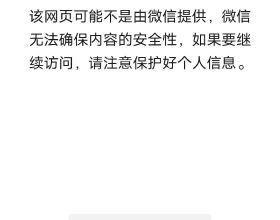魯迅先生最討厭善於獻媚的貓,更蔑視只會溜鬚巴結的狗。但他對牛,卻是十分的喜愛,因為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並誓言“俯首甘為孺子牛”。
本人雖不敢與魯迅先生相提並論,但實話實說,我也討厭貓,更反感狗,對牛亦是十二萬分的喜愛,其喜愛程度,較之魯迅先生,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之所以對牛情感深沉,起因於牠對我恩重如山——助我完成了大學學業啊!
回想此生,一個出生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農村娃,命運註定坎坷艱辛,尤以我的求學生涯為最:小學靠“雞屁股銀行”支撐讀完;中學全仗“賣豬換錢”助力畢業;中學畢業該高考了,上面卻通知不讓直接考試,而是城裡學生要下鄉,農村學生要回鄉,統統“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由他們推薦上大學。相信有過“推薦上大學”經歷的同齡人,都會像我一樣,那段不堪回首的時光,會在各自的生命裡烙下怎樣的記憶?
回鄉參加勞動其間,我為了能被“推薦”,不得不拼命表現:春日田裡插秧溺草,螞蟥爬滿腿腳,巴掌拍掉,鮮血直流,不敢跳腳驚叫,忍著懼怕堅持;夏季割麥,手掌磨出的一茬又一茬,彎腰疼得要折不能聲張,直一下趕緊伏身再割,生怕比別人落後半步;收秋施肥,十七八九歲的單薄身軀,被百餘斤的紅薯、玉米、穀草、土肥擔子壓成彎弓,也得咬牙挺住;打麥場上,揮鍁撒稻揚麥,汗水灰土滿臉滿頭,麥芒稻屑鑽進衣衫,癢疼難耐,忍著不敢吭聲;進出倉庫搬運糧物,稚嫩的脊背被一兩百斤的小麥、稻穀、黃豆、化肥袋子壓成“之”字,脖臉憋得通紅,也得忍著眼裡的淚水,不能有半點退縮……
我這樣的積極表現,自然獲得群眾的認可與首肯。每年都有村民推薦上大學。我得的票數隊裡最多。然而經由大隊、公社再評,最後上大學走的卻不是我……就這樣,我五年拼命勞動,五次推薦失敗。五年裡,我不知哭過多少次,多少次絕望到極點。我家無錢無勢,父母親百方使盡,無可奈何,看我萎靡可憐的樣子,竟勸我說:娃兒,你沒上大學的命啊!給你好賴找個媳婦,成個家吧!我哭著死活不從:我從小學、中學一路走來,多難啊!我一直努力,不想就這麼算了。我也堅信上帝公允,老天會眷顧我的。果然幾年之後,鄧小平力促恢復高考。我終於在1977年冬天參加高考,1978年春天圓了我的大學夢!
記得後來有個電影,名叫《高考1977》,說的就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後參加高考的事。影片中的小根寶、陳瓊、潘志友等,為了能被“推薦上大學”,他們遭受的磨難與我何其相似啊!所幸的是他們其中的不少人跟我一樣,經由努力改變了命運。不過,在此我要多說一點:雖然這些下鄉知青與回鄉知青的命運差不多,但大學畢業工作之後,有些待遇還是不同。比如知青下鄉期間,可以計算工齡;而回鄉知青就不能算;還有知青沒有考上大學,後來還能回城工作,農村經歷也算工齡;而沒能考上大學的回鄉知青,又無機會當民辦教師,就變成真正的農民了。這是否一種幾千年延續下來,對於農民的一種不公正呢?當然,這是後話和另外一個問題了。
還說我考上大學的事情吧。對我來說,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學費怎麼解決呢?這可不比小學中學,靠養雞養豬肯定不行了。雖然第一學期去報名,先出去借點兒,再賣點糧食湊湊,可以暫時對付,但後續生活費用怎麼辦啊?去大學報名走的前幾日,父親母親跟我,每天都商量到深夜,仍然想不出什麼好辦法。後來他們寬慰我:既然考上了,咱就考得上。學費生活費你甭管了,一定會有好辦法,你只管好好上學就是了。
就這樣,我興高采烈並深深憂慮著,帶著父母的囑託走進大學,開始追逐陽光之旅。
暑假回家,走進村頭。妹妹弟弟迎著我,神秘地說:哥,咱家才買了一頭牛。
我一聽,很驚訝:家裡給我去信,咋沒說過這事兒?
妹妹笑著說:爹媽不叫跟你說,說怕分心你學習哩!
我沉吟,笑著說:好呀!現在分田到戶,實行承包聯產,咱家沒牛,種靶地老是求人,買一頭牛,爹媽幹活就省勁了。買的黃牛還是水牛?
我老家桐柏屬於南陽,過去生產隊養的大都是南陽黃牛。南陽黃牛身高體健,力大無窮,耐勞肯幹,是全國知名黃牛品種。但桐柏又與湖北交界,氣候相近,稻田較多。黃牛適合旱地勞作,幹稻田活兒卻不如水牛,因此,隊裡也養了一些水牛。
弟弟說:不是黃牛,是水牛,還是母水牛。這頭牛是專門為你買的哩!
我又疑惑了:給我買的?還是母水牛?給我買母水牛有啥用處?
妹妹弟弟都笑了:咱爹咱媽打算了,叫牠供你上學吶!嘻嘻嘻!
帶著滿腹疑問進家,與父母相見,傾訴完思念之情,彙報過大學生活,便向父母親問起買牛的事兒。父親吧嗒著旱菸袋道:這是你媽的主意。我將目光轉向母親。母親嘆口氣說:娃呀!你上大學,花銷準定很大,四處轉借不是法兒,養雞養豬隻能救救急,大宗花錢咋整哩?跟你爹想來想去,養牛是個好法兒。就為你買了頭母水牛,水牛比黃牛皮實,受摔打,春天配好種,秋後就能生崽兒。一隻牛崽二百多,你一年的學費就有了。
聽母親如此說,不由心頭一陣沉重:那——買這頭母水牛,要花不少錢吧?
父親叼著菸袋,故意輕描淡寫:也不多,三百多。一年就把窟窿捂上了。
父母說著話,帶我去看牛。牛養在由豬圈翻蓋成的牛圈裡。搭眼看,牠黝鼻鈴眼,一身灰黑,兩個彎月般的牛角盤展頭頂,牛角下面,兩隻扯風長耳左右斜立。牠身個雖無公水牛那般高大威武,卻也骨架緊湊,四肢壯碩,有一種鍾靈毓秀的女性美與柔順感。這頭母水牛,幹活可能不如公水牛有勁,但和別家的牛配對兒,拉車,打場,肯定綽綽有餘。犁耙耩地,收耕播種,也能替父母親省點力氣。有了牠,如能助我上學與幫父母幹活兩不誤,也算天大的好事兒。因此初次照面,我就對牠有了認同感與親和力。
牛看見我們,碎步朝圈門走來。父親母親愛憐地摸摸牠的頭,妹妹弟弟淘氣地拍拍牠鼻子,牠都不急不惱,還溫順地舔觸他們的手掌。看來他們之間,已經混得很熟了。唯獨對我,有點生疏,我去摸牠,竟然揚頭躲避了,還睜大鈴鐺般的眼睛,眨巴著詫異地瞪著我,似乎在問:你是誰啊!我怎沒見過你?
離開牛圈,母親說道:母牛已經配種了,秋後就能生牛崽兒。
我心裡又是一陣發熱:可憐天下父母心,他們為我想得真仔細呀!
這個假期,除了幫父母割麥、揚場、種秋之外,還經父母同意,由我代替父親,一早一晚放牧水牛。老家養牛,一般冬天草料飼養,春夏秋草青季節,依靠放牧為主。而且夏暑天熱,只能起早貪晚放牧。
於是暑假期間,我就當起了牛倌兒。每日天麻麻亮起床,牽了母水牛,迎著初升旭日,走上不遠處綿延的坡嶺,讓牠吃露水草。半晌時回家,讓其於牛圈裡反芻歇息。下午後半晌,再牽著牛上坡,吃曬熟燙的茖焉草。天擦黑回家,再喂點水料,就可以了。
正值酷暑時節,即便下午後半晌,空氣依然暑熱難耐。我下午牽著牛出去放牧時,牠竟然犟著不上坡嶺,而是去稻田、水塘等周邊找草吃,熱急了,就臥在稻田、水塘邊泡一會兒。我生怕牠跑到稻田裡面或者水塘深水處,就緊緊握緊栓牠的牛繩,不敢有絲毫的大意和懈怠。然而,有次我還是大意了,母水牛竟然拖著我手裡的麻繩,朝水塘深處遊。我拽不過牠,又不會鳧水,生怕掉進水裡被水淹嗆,就丟開了麻繩。母水牛一直游到塘中央,全身舒服地沒於水中,只露一個腦袋,賴在那裡不出來了。
這可咋整?我想跳進水塘,將牛趕出來,可我不會鳧水啊!想回家喊父親,讓他來趕牛,又怕有人把牛偷跑。無有良策,只好死死守在塘邊,等著父親前來救援。一直等到夜色黑盡,才看見遠處手電閃閃爍爍,父親還有弟弟喊著我的名字,朝這個方向跑來。我趕緊朝他們喊叫。他們到後,父親雖沒像我小時候那樣兇狠地罵我,但語氣裡分明帶著氣惱:咋弄哩你?跑遍坡嶺找不著人,咋到水塘這邊來了?
我囁嚅著,把母水牛不聽話,非要往稻田、水塘邊吃草,掙脫繩索遊進水塘不出來的情形,都給父親說了。父親這才不說啥了,脫了上衣,跳進水塘,朝母水牛游去。弟弟卻在一旁嘻嘻笑了起來。
我怨怒交加道:你娃子幸災樂禍啥?
弟弟止住笑說:哥,我看你是讀書讀傻了。咋恁笨哩!我給你出個主意吧!
有話就說,有屁就放。賣啥關子呀你?
以後,母水牛再想掙脫你,你就順勢拽住牛尾巴,牠遊哪兒,你跟哪兒,牠甩不掉你,水也淹不著你。要是你累了,就爬上去,騎到牛背上。牠在水裡呆一陣,涼快了,就聽你指揮,自己游出來了。
胡扯吧你!牛那麼高,我咋爬上去?
真是笨到家啦!牛在水裡,還那麼高呀?只露個脊樑蓋兒,你一縱身子,就上去啦!
那——牠要是急了,踢我咋整?
哈哈哈,不會的,水牛比黃牛綿善,又不是生人,咋會踢你哩?
父親將母水牛趕出水塘,我把弟弟說的辦法說給他聽。父親這才露了笑臉,拍了弟弟一巴掌道:你這小子,歪點子不少,要是都用在學習上,就跟你哥一樣上大學了。然後又對我說:你弟這個點子不錯的,你往後就照這個法子整。
隨後再放牛吃草,我果真就按弟弟說的方法,一旦母水牛想掙脫我往水塘深處去,我就雙手緊拽著牛尾巴,隨著牠往水塘深處遊。牛在水裡遊,我在水中漂。到了深水處,我試著往牠身上爬,牠真的沒反應,很順利地騎上去了。那感覺真的爽極了。果然,牠在水裡呆一陣,涼快舒服了,就自己游出了水塘。
那個暑假餘下時光裡,我天天牽著母水牛放牧吃草,早起晚歸,親密相處,漸漸地,之間也開始廝混得熟稔。後來再出去放牧,不用牽繩,牠都會跟著我走。在坡上、稻田、水塘邊吃草,也不往遠處跑了。偶爾下水塘涼快一會兒,很快就上來。我不想下水,就不再跟牠,自己坐在石頭上,或者躺在樹蔭裡,一邊歇息乘涼,一邊賞玩天上的雲彩。
母親曾對我說,天上的星星就是世間的一個人。一個人出生了,天上的星星就會多一顆;一個人死了,天上的星星也少落一個。那麼,天上的雲朵也是世間的一個人嗎?我是這些雲彩中的那一朵呢?算了,我不想當天上雲朵了,但願雲朵能知我的心,幫我實現今生的夢想。
轉眼之間,暑假結束。我要回校上課了。離家那天,我特意去跟母水牛道別。我撫摸牠的面部,輕拍牠的頭顱,牠居然也伸出舌頭,像舔觸父親和弟弟的手掌一樣,舔觸我的手掌了。那一刻,我興奮極了:我終於成了牠信賴的朋友。
回學校的幾個月,我一直惦記著母牛的訊息。弟弟終於來信,說母水牛生了,生了一頭跟牠媽一模一樣的小牛崽兒!我欣喜若狂:老天保佑,母牛爭氣,我的大學生涯無憂了。
很快到了寒假。我急不可待地買票乘車,到家見過父母弟妹,就直奔牛圈,去看望母水牛和牠的小牛崽兒。母牛看見我,似乎還認得,又蹀躞過來,舔我手掌。小牛崽兒不認識我,害羞似的偎著媽媽,瞪圓稚氣的眼睛望著我。
冬寒季節,不出去放牧。我就跟隨父親,學著為母牛鍘草拌料,親手飼餵。以報答牠給予我的恩惠。晚上沒事時,我也長時間守在牛圈,藉著馬燈光亮,看母牛反芻,小牛吃奶,並給牠們說一些我在大學裡的新鮮事兒。我以為牠們聽不懂,但看牠們被我吸引、聚精會神的樣子,又似乎知道我在說什麼吧!
大學四年間,每個暑假回家,我都要放牧那頭母水牛,一早一晚與牠相伴,以此投桃報李。每個寒假回家,我都要為牠拌料鍘草,陪牠說話,藉以感恩戴德。直到大學畢業。
參加工作後,回家次數漸漸少了。但仍然惦念著那頭母水牛,往家裡寫信或打電話,總要問起牠的近況。父母說牠挺好的,我才心裡覺得安生。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牛有旦夕禍福。幾年後,弟弟突然給我打電話,說那頭母水牛死了,是生崽時難產而死:這次母水牛生崽是倒生,後蹄出來後,腿和屁股再也不出來了。母牛累的兩腿發顫,站立不住,躺倒地上呼呼喘氣,眼裡只是流淚,可憐巴巴望著爹,嘴裡不時地哞叫,好像哀求咱爹:趕緊救救小牛崽啊!爹心疼得背過身,不忍與牛對視,只能緊拽牛鼻圈,讓人攥住小牛的蹄兒,拼命用力往外拽,可還是沒有半點用。村民說,趕緊向鎮獸醫站求助吧!或許他們有辦法。父親就去村部打電話。等了半天,獸醫站來人了,卻說已經過了黃金八小時,不僅牛崽沒救了,母牛也已經被感染,可能活不長久了。獸醫臨走時開了些中藥,讓煎了給牛灌了喝。但是藥煎了,也灌了,母水牛也沒能救過來……
聽完弟弟的敘述,我好久好久說不出來話。心裡的傷感像利刃,一下一下切割著五臟六腑,我忍不住潸然淚下:過去連生幾胎,不都好好的嗎?這次怎麼就難產了呢?難道母水牛是蒼天派到人間的使者,讓牠助我完成大學學業的嗎?看我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老天就收回了成命?只是這頭母水牛太可惜了,牠為我的學業了付出一切,自己卻……
記得希臘神話裡,記載有普羅米修斯偷取天火,造福人類,卻遭宙斯懲罰,用鐵鏈將其鎖於高加索山的岩石之上,讓兇惡的蒼鷹啄食其皮肉和五臟。中國古代神話有夸父追日,他決心要將灼熱的太陽摘下來,為民眾驅寒止冷,然而最終也沒追上,自己反而渴累而死,身軀化為綿延的山嶺,手杖變成千裡桃林。而我家的這頭母水牛,亦是一個“陽光使者”,牠傾其所有,助我追逐太陽光輝,雖則最後難產而死,但卻永遠銘記我心。
不由再次想起魯迅先生對於牛的評語:“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並一生身體力行,“俯首甘為孺子牛”。不由再次想起,我曾在暑熱的夏日,騎在我家那頭母水牛的脊背上,在涼爽怡人的水塘裡,來回穿遊,恣情迴旋……不,不僅是在水裡。是我騎著牠,飛離了水面,飛向了天空,實現了曾經的夢想,並永朝陽光,翩飛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