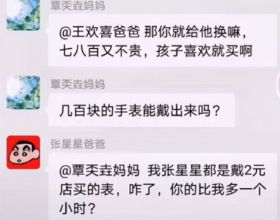老兄老弟
文/頻陽子
外爺家姓李,兄弟兩個,大貴和二貴,大貴比二貴大十多歲。大貴外爺生性怯弱,卻好交朋友;二貴外爺內秀,善於管家和經營農事。
外爺的老家在湖北神農架南邊的丘陵地帶。神農伏羲氏的後裔善於農事,卻在祖居之地難以安生,養活不了自己。清朝後期朝綱腐敗,民怨鼎沸,太平軍橫掃江南,連年戰火,生靈塗炭。加上江漢平原水患不斷,湖湘人口大量外逃。外爺的父親挑了擔子,前筐坐著3歲的次子,後框盛著一歲的妹妹。大貴外爺牽著母親的衣襟,步履蹣跚,走走停停,爬過秦嶺,一路乞討,風餐露宿,輾轉流離半年之久,才到渭北平原的紅苕窯落腳。
那時候紅苕窯兩三戶人家,都住下地窯洞。初來乍到,一窮二白,外爺的父親靠大埝搭了草棚,把家就算安頓了下來。他租了附近大堡子財東六畝旱地,繼續著神農氏的事業。冬季閒暇,他按照當地老戶的規範,開挖下地窯洞,偌大的一個窯院,上萬方土,一鍬一鍁地開挖,一筐一筐地挑出來,大貴和母親,用框往外抬。度過了漫長的三個冬天,父親挖好了窯院。開挖了三孔窯洞,安置了院門,在院子的一角,打了水井,安裝了轆轤。在窯院和門前、窯背,栽植了一些樹木,天寒遮風,炎夏庇廕。父親為大貴二貴兄弟奠定了一份堅實的基業。
人忙總覺日月短。轉眼之間大貴成年了,二貴也十幾歲了。父親給大貴娶了媳婦,給二貴領了一個童養媳,幾個妹妹也在周圍找了人家結了親。忙忙碌碌一年,慢慢能夠吃飽肚子了,逢年過節人來人往,父親在農事之餘,也在附近建立了他的人脈。
等到二貴成家的時候,父母雙親先後離世。兄弟二人擔起了這個家的擔子,繼續著父親創立家業,興旺家族的艱難歷程。父親省吃儉用,老來買了幾畝地,大貴二貴兄弟陸續添置了幾畝,兩代人積累了十畝旱地,買了一頭大黃牛,小家日子開始有了起色。
民國初年,軍閥混戰。走馬燈似的政府官僚們,幾度鼓勵農民種植罌粟,製作煙土。渭北平原各處先後設定了煙局煙店,軍閥官僚們以煙養兵,也以煙肥私。很多民眾也學會了吸食鴉片,買菸販煙。本來就貧困的鄉村,搞得人心惶惶,雞犬不寧。
大貴當了甲長,村裡十幾戶人家當兵納糧,種煙收土,處理村民之間的各種糾紛。紅苕窯再無第二個人能夠擔當此任。
外爺家也種了煙土。二貴外爺為了多賣幾個錢,把自家日子過得比別人好一點。大貴外爺開始吸食鴉片,不過他避著弟弟。弟弟當家,他有顧慮。大貴外爺吸菸經常溜到老朱家,也和老丁搭夥結群。幾個人擠在牛圈裡,或者鑽進菜園瓜庵子內做賊似的。二貴外爺心裡明白,只是沒有說出來。
大外婆在外爺家生活了幾年,沒有留下子嗣,經常病病懨懨。那個時代缺醫少藥,物質匱乏,人們的健康狀態聽天由命。儘管大貴外爺呵護有加,她不到而立之年就病逝了。
二貴外婆心靈手巧,自小被姑姥調教得通情達理。紡線織布,納鞋繡花,村裡的大姑娘小媳婦無不嘖嘖稱道。她來自陝南秦嶺深處的鎮安縣,在小惠鄉中惠村有她堂叔堂伯,十天半月就你來我往。小惠鄉上唱戲、雜耍或者節日集會,孃家人就會牽頭毛驢,披了駝毛氈小鞍子,來外爺家接外婆過去看熱鬧,她和堂伯堂叔一家十分親熱。
大貴外爺天黑就上炕睡覺,每天天不亮就起來了。給牲口添過草料,他就進了灶膛燒水,柴火把他的臉膛映照成黑紅。等二貴外爺起來,大貴外爺鍋裡的涼水就燒開了。大貴外爺沖洗了茶具,切好茶水,他坐在茶几旁默默吸菸,靜靜等待弟弟過來。弟弟圍坐上來了,他才會自己端起茶杯,陪弟弟喝清晨的早茶。一邊喝茶,一邊打算當天的農事。待茶水喝過三五輪以後,天色大亮,他們就一起出門下地,新的一天的勞作就開始了。有時候聽到鄰居老朱家的院子有了響動,那肯定是老朱的父親起來了,老朱沒有早起的習慣。大貴外爺會站在自家的窯院,呼喊朱家老人過來一同喝茶。
有一年夏季,保長領了一幫保丁來收繳公糧。帶了繩索棍棒,佩著短槍長槍。大貴外爺撒腿從外邊跑回家,悶頭就往牛圈裡鑽。二貴外爺正準備牽牛下地,大貴外爺要他把自己埋進草堆裡。二貴外爺問出了什麼事情?大貴外爺說保長又來催糧了。那保長催糧你領路就行了嘛。大貴外爺臉色煞白,氣喘吁吁地說:會出人命的!原來紅苕窯沒交公糧的三戶人家,都是新來的逃難戶,家貧如洗。租種的旱地,交完地租,老婆孩子吃了上頓找不著下頓,哪有糧食給保長上繳!
大外婆去世三年了,給大貴外爺說媒續絃的同鄉好友日益增多,知道家境還不寬裕,大貴外爺不好給弟弟開口。姑姥倒是坐不住了,三番五次給二貴外爺提及兄長的親事。姑姥家在曹村,老姑父在涼州經商,大兒子在西北農學院讀書,家裡就她和一個病懨懨的小兒子。姑姥生性潑辣,行事幹脆,想事長遠。她大半年時間在孃家幫老兄老弟一家。她比二貴外爺大兩歲。給弟弟說話,從來不會藏著掖著。
二貴外爺不哼不吭,不露聲色。大貴外爺急得火燒火燎,閒了打掃院落,給牲口剁草,搖轆轤打水,在家待不住了就往老丁家裡跑。大貴外爺不會吹牛擺龍門陣,和大劉老丁們抽菸、打牌九。
一個夏天過去了。秋季在窯背上鋤草,二貴外爺給姑姥說,大哥應該續絃了。咱是小戶人家,沒有多餘的錢財胡整亂花。讓他把大煙忌了!他不再偷偷買菸土了,續絃的錢糧我給想辦法。
姑姥把弟弟的心思告訴了兄長,大貴外爺臉紅得像個做錯事的大孩子。他拍著胸脯給妹妹說:得!那東西又不是飯、不是饃。他做出了一副很有志氣的樣子。讓妹妹監督,他要改抽旱菸。
大貴外爺在曹村集市上買了一把旱菸袋。姑姥還專門讓集市上的工匠給大哥的銅質菸袋鍋雕刻了一條盤龍,買了個瑪瑙菸嘴。大貴外爺拿著簇新的煙具樂得像個大孩子,不住地用衣袖擦拭金黃色煙鍋和半透明的瑪瑙菸嘴上的浮塵。回到家裡,大貴外爺自己動手,連夜加班,用舊衣破布縫製了一個半尺長的煙荷包。
開始戒菸下油鍋似的煎熬難忍。大貴外爺跑到金華山,給大姑姥家裡在山中挖地。掄圓三斤多重的頭,日日去消耗自己的體力。小外甥泉兒給他送飯送水,煙癮來了他伏地閉目,貼著山坡經歷撕心裂肺般的折磨。泉兒驚恐得大喊大叫。山谷空曠,草木青青,霧靄山嵐忽近忽遠,忽明忽暗,徘徊瀰漫。他有時候將沉重的頭顱伸入泉水,讓清流蕩滌。他聽到山雀的聲聲呼喚,好像徜徉在明媚的春天。那是神農架山地的和風,先祖慈祥的手掌在撫摸他子孫的心靈。竭力回覆內心的安寧,他在大山裡待了七七四十九天,挖出了十五畝荒地。一個健壯的大男人,整整瘦了一圈半。
二貴外爺在門前窯背的空地裡,栽植了半畝多旱菸葉。大貴外爺手腳勤快,沒事就去搖轆轤,挑了井水澆煙苗。也將牛糞雞肥,一鏟一鏟圍在根底。旱菸長得一人高,菸葉子就像芭蕉扇。老丁和老朱、大劉經常過來看稀罕,他們鼓動大貴外爺乾脆種旱菸算了,都說大貴外爺的旱菸長勢在渭北平原前所未有。
大貴外爺終於填房了。新娶的續絃是曹村附近的一個姑娘,濃眉大眼,總是笑咪嘻嘻的,為人和善。她與二貴外婆妯娌二人相處得像一對親姐妹,姑姥就喜歡在家裡對他們大呼小叫,指手畫腳。
大外婆外表好看,卻是眼拙手笨,不善於做家庭主婦。做飯需要大外爺經管,縫衣納鞋,要姑姥引導。然而幾年過去,她給大外爺生育了三個兒女,大外爺雖然忙外忙裡,處處都操心,卻有了天倫之樂,還是對大外婆充滿感激之情。
有一年秋天,外爺家連續被盜,兄弟二人十分惱火。二貴外爺仔細查看了四周,發現盜賊是從南邊的一棵棗樹縛了繩索,攀援而下,沿繩索在窯院溜進溜出的。老丁也發現了盜賊的路線,他說外爺家是紅苕窯第一大戶,肯定是盜賊下手的首選目標。農具丟了,糧囤被人動過手腳了。外爺們寢食不安,一直在琢磨對策。
中秋之前的那天夜晚,月明星稀,涼風徐徐。後半夜二貴外爺正想起身小解,忽然聽見院子裡有輕微的腳步聲。他警覺出情況了,赤條條衝出窯門,飛身跑到棗樹下方,把那條懸垂下來的繩索守住。
大貴外爺聽到弟弟的呼喚,翻身起來,在門後拉出土槍,跑到院子,朝天扣動了扳機。“咚—隆”,整個夜空好像都被槍聲震碎,火藥味四處瀰漫。
“大哥,饒命!”院子的一角有黑影遊動,他撲通一聲雙膝跪地,兩手下垂,頭顱搗蒜般地叩頭求饒。
槍聲震動了紅苕窯。半個村子的男人們都迅速聚攏過來,人們把盜賊反吊在窯門前棗樹上面,要嚴正懲罰雞鳴狗盜之輩。
老朱要把盜賊扒光衣服遊村示眾,老丁要他賠償外爺家丟失的所有財物。大外爺氣憤得渾身顫慄,挽起衣袖就要拿皮繩抽盜賊。大舅那時候剛上私塾,他向盜賊扔磚頭。
二貴外爺阻擋眾人的作為。他放下繩索,給盜賊鬆了綁。盜賊領著外爺走上窯背,在不遠處的一個被廢棄的半截井裡,丟放著他所偷盜的外爺家的農具,偷走的幾鬥糧食,老婆孩子在家餓得嗷嗷叫,盜賊許願來年夏收時節,加倍還給外爺家。
事件過後,才搞清楚,那盜賊是北窯村人,距離紅苕窯不到三里地。他老家在大水峪,舉家遷到山下才一年。家徒四壁,一貧如洗,在周邊地區舉目無親。後來每年的夏收秋種,那位偷盜過外爺家的大水峪人,都來紅苕窯給外爺幫工。他有的是力氣,幹活異常賣力。外爺此後也把作務農田的各種技藝,一一教給那位大水峪人。期待他能脫貧致富,活得有個人樣出來。
紅顏命苦,好人不壽。二貴外婆生養了四個子女,三女一男,不幸患上了肺結核,二十七八歲就不治身亡。她被安葬在祖墳裡,松柏青翠,長草萋萋。二貴外爺卻在她的墳頭栽植了兩棵白楊,白楊樹堅挺,鑽天抵雲,春夏天高風輕,粉白色的樹葉嘩嘩作響。
七八個子女,大的十歲,小的才兩三歲。外爺家後繼有人,大人們卻十分不幸。一群小孩,吃喝拉撒,穿衣洗涮,姑姥和大貴外爺要全心經管,大外婆只會做幫手。
外爺家又買了十幾畝土地,買了一匹大騾子,日子有聲有色地向前過著。
秋冬閒暇,外爺趕了騾子上山馱碳。山高路遠,外爺和張村的騾馬馱隊搭夥,夜晚出發,摸著夜路進山。天亮趕到礦山,裝好馱簍,吃飽喝好,中午時分開始回返。一個對時,來回一趟,第三天去附近的村莊賣碳。老兄老弟,輪流換班。外爺們給大騾子繫了銅鈴,轡頭上兩撮紅纓,馱了煤炭簍子的大騾子昂首挺胸,赳赳而行,一路走來紅纓飄飄拂拂,大銅鈴鐺叮咚作響,招惹得忙碌在田間地頭的人們無不駐足羨慕。
老丁大劉們給二貴外爺提親填房,二貴外爺堅決不肯。姑姥也鼓動弟弟儘快續絃,總不能讓老姐給你們當一輩子家奴。老朱父親步履蹣跚,拄著柺杖到家裡苦苦相勸,二貴外爺平靜地笑了,他說我家的孩子多,都是些嬌生慣養的傢伙,我怕後孃對他們不好,鬧得一個大家庭雞犬不寧。
二貴外爺失去外婆鰥居時候,他才三十多歲。此後他一直精心於農事家事,終生沒有再娶。
金華山的大姑姥病逝了,老姑父也不在了,小外甥泉兒被堂叔收養,他給堂叔家在山裡放羊。天天起早貪黑,爬山越嶺,要走過幾十里山路。外爺們心裡不安,老兄老弟合計了一番,二貴外爺連夜上山,和那個堂叔吵了一架,硬是把小外甥背下山來。大貴外爺厲聲給泉兒說:再不要上山了,就住在舅舅家。去小惠鄉上讀書,將來長大了,舅舅給你蓋房子、娶媳婦。小姑姥把泉兒當親兒子看待。
臨近解放,外爺家要蓋青磚大瓦房,這在紅苕窯可是開天闢地以來最隆重的事情。左鄰右舍都來幫忙,外爺們的親朋好友前來祝賀,人流如潮。上大梁的那天中午,鞭炮響過,宴請賓朋,大貴外爺抱著罈子喝酒,眾人勸說不下,他喝得酩酊大醉。忽然他在門前雙膝跪下,放聲痛哭,面朝南天,三叩其首。二貴外爺見此情景,淚如雨下。
大舅是二貴外爺的獨子,他上過三年私塾,後來跟了外爺的好友學中醫,在小惠村醫療站做鄉醫。二舅和三舅是大貴外爺的兒子,他們所處的時代變了,陸續讀完小學、中學,二舅和三姨同齡,他們中學畢業後一同考上了銅川衛生學校。三姨是二貴外爺的小女,畢業不久就到任丘油田做了教師。三舅畢業後回鄉當團支部書記、民兵連長、大隊會計,幾年後在小惠鄉學校任教。
大貴外爺身體弱,不到七十歲就去世了。他和二貴外爺一生都在一個鍋裡攪勺,一個桌子上吃飯。臨終他告訴弟弟,把他安葬在父母祖墳的下方,他要陪伴一輩子受苦受難的父母。二貴外爺買了最好的柏木板材,給大貴外爺做了棺木。大貴外爺下葬當天,瓢潑大雨,二貴外爺扔掉雨傘,披麻戴孝,手舉招魂幡,走在送葬隊伍的最前邊。
大貴外爺的三個兒女,二貴外爺給他們娶妻成親。二舅娶了一個大家閨秀,三舅岳父親自跑到外爺家,要將自己的獨生女兒嫁給李家。三妗子如花似玉,聰明賢惠。三舅考上了公辦教師,每月縣財政給統發工資。
二貴外爺活了九十六歲,五世同堂。
八十歲後,二貴外爺仍然管理家事。騎腳踏車、上街買菜、忙裡忙外,對家裡家外大小事情都牽心。他去西安、逛北京、下河南河北,八十年代後遊歷了大半個中國。他是這個家族的精神支柱。他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一個家族的命運。同時他見證了紅苕窯近一個世紀的新舊變遷和人事浮沉。他是新世紀來臨後才平靜地離開這個世界的。臨終他留下了五萬元存款。外婆的一雙繡花小腳鞋,他在櫃子裡珍藏了近六十年,兒女們全然不知。他給子女們交代,把那雙繡花小腳布鞋,最後放進他的棺材裡。
渭北平原靜靜地橫臥在秦嶺北麓。風生水起,年年春色不減,季季綠肥紅瘦。皇天后土,雲淡風清,生生不息。
外爺們走了很多年了。他們創立家業的歷程已經往事如煙,隨風而去。他的家族和後代們,現在仍然是紅苕窯乃至小惠鄉的風流人物。他們在市場經濟的社會大潮中,仍然獨領風騷,為周圍人們所仰慕。
頻陽子,男,文化學者和作家。主持某省級學術和文學期刊。文學作品有散文集《遠去的鄉村》,中短篇小說集《故鄉事》,電影文學劇本《天佑》《孟姜原》等。
來源:《陝西文譚》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