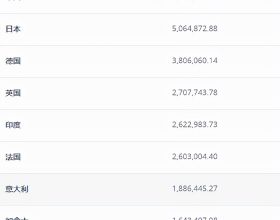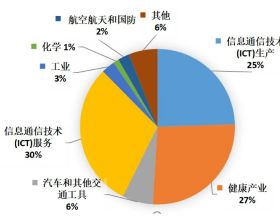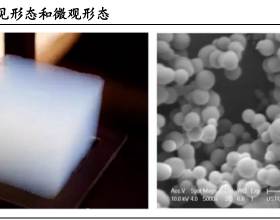李中躍
《紅樓夢》被譽為傳統社會的百科全書,深受社會各階層的喜愛。除了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家族,《紅樓夢》也有較多的軍事描寫,顯示了四大家族的軍功背景。比如《紅樓夢》第七回曹雪芹借尤氏和焦大之口,道出了寧國公的軍功背景:“他從小兒跟著太爺出過三四回兵。”第二十七回賈蘭因賈寶玉嗔止他追射小鹿,便以軍功風尚給自己解圍:“這會子不念書,閒著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第五十五回探春以先輩軍功艱難為由,主張厲行節約:“又好好的添什麼,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下來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馬揹著主子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告訴他,我不混添減,混出主意。”這些描寫不僅體現了賈家的赫赫軍功,也顯示了後期軍功作風的蛻變。
為了深入解析《紅樓夢》,近代以來大家習慣用文史互證的辦法來探討。自胡適以來,學界多將《紅樓夢》與清國史掛鉤,認為曹雪芹是清代曹寅家族之人,而曹家就是賈家的原型,以赫赫軍功起家。那麼曹寅家族在真實的歷史中有沒有軍功?軍功是不是如目前所傳“戰功赫赫”?曹寅在曹家武運上起到了怎樣的作用?紅學與清學的契合度有多高?等等問題至今多是糊塗賬。接下來我們就儘可能以明確史料為基礎,穿過歷史的迷霧,去追尋這一著名家族的軍旅足跡。
高大的先祖
曹寅的先祖曹振彥和曹璽等人,在清朝開國之際曾跟隨努爾哈赤、皇太極和多爾袞等人,參與對明戰爭。學界對曹振彥和曹璽有沒有立下軍功,存在兩個極端看法:一種認為此二人“軍功赫赫”,一種認為此二人並無“戰功”。這兩種看法似乎都不太合適。
“軍功”和“戰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帶有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我們從清代的軍功規定可以看出:“戰功”指官兵前線作戰的功績,具體指殺敵取利和攻城略地;“軍功”的範圍要廣,不僅包括“戰功”,也包括“招撫功”,甚至“官兵勞苦”,至近代以來既包括作戰功績,也包括勤衛功勞。
尤其是“招撫功”,即官兵能夠招降敵軍,不戰而屈人之兵,實為不流血的戰功,非常划算。早在皇太極時期,它就被納入軍功範圍內。到多爾袞時期,招撫功被清晰地列入軍功制度內。順治五年規定:“招撫兵一千名以上,船五十隻以上,及官民未徙之全城者,統兵主帥分發將領,及將領下遣去招撫之人,俱準敘功。”按照這個寬鬆的規定,即便“下賤包衣”若能勸降敵兵,也能獲得軍功獎賞。
目前零星的清史資料難以證明曹振彥、曹璽是否創立了“戰功”,但是無論以當時標準還是近現代軍功觀來看,曹氏父子還是有“軍功”的。何以為證?
1、明清遼東曹氏有深厚的軍功傳統。馮其庸先生透過梳理《五慶堂遼東曹氏總譜》、清實錄、明清地方誌等史料,已成功證明了曹振彥創立軍功,有時代背景、地緣業緣和家族人脈的優勢。
2、軍功規定的制度便利。曹振彥作為王府包衣,當過多爾袞的“旗鼓牛錄章京”等職。按滿族規定,在主子作戰時他必須聽從調遣,或前線協同作戰,或從旁勤務招降,按清初寬泛的軍功規定,有立下“戰功”“勞績”而得“軍功”的制度便利。
3、曹振彥“因功加半個前程”。“半個前程”是清初低階世襲爵位,對一個下級包衣小官來說,可謂重大賞賜。一個漢族包衣小官,只有立下重大功績,方能獲得如此殊榮。黃一農先生綜合考證後,認為曹振彥極有可能憑藉出色的語言能力和特殊的血脈關係,在招降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如此曹振彥則立下了“招撫功”。
4、曹振彥的軍政履歷。曹振彥曾當過八旗軍內的“教官”,後又升到“旗鼓牛錄章京”,被皇太極特別允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後又轉做知府、鹽法道等文職。曹振彥在八旗軍政系統中的上升,反映了後金權貴對其軍政“勞績”的認可和獎勵。以清初軍功標準來看,其招降功或勞績被視作“軍功”,沒有不妥。而以近現代的軍功標準來看,曹振彥有軍功是毫無疑問的。
5、曹璽扈從多爾袞平定姜瓖之亂。康熙朝《江寧府志》和《上元縣誌》的兩篇《曹璽傳》都記載曹璽曾以“侍衛”身份“隨王師徵山右”,在平定姜襄叛亂中“建績”“有功”,因此被順治帝提拔為內廷二等侍衛,管理鑾儀。這是曹璽軍功一個比較有力的佐證。聯絡戰爭的客觀需要、曹璽的自身優勢、與多爾袞的主奴關係、文獻不言戰功多贊文能、曹璽戰後又能敘功,可推知:曹璽作為侍衛,帶有警備性質,本職當為護衛多爾袞,親臨前線戰鬥的可能性不大;在扈從多爾袞征戰大同姜瓖等部時,初出茅廬的曹璽,雖無赫赫武藝,最終卻能建績有功,應當是憑藉出色的文言能力,協助清軍繕寫漢語文告或入城勸降,疏通內外滿漢交結事宜,最終才得以戰後敘功領賞。雖不排除曹璽射殺立功的可能性,但綜合史事邏輯,其“功”似偏指“勞績”或“招撫功”。無論曹璽的“功”是“勞績”“招撫功”還是“戰功”,以清初軍功標準,均可算作“軍功”。至於事後的曹振彥,目前的史料並不能證明他親自參與了作戰平叛。順治九年的曹振彥奏本,可證明其為清軍提供了善後支援,是平定山西中的一環,所有功績當屬“勞績”,談不上“戰功”。
以上可見:曹振彥和曹璽戰功不明,軍功有據,即便沒有清朝嚴格意義上的“戰功”,但也應該是有“軍功”的。而以近現代軍功觀來說曹氏有軍功,基本上沒有問題。不少學者認為“曹家以軍功起家”,並非完全無理,只不過他們獲取軍功的途徑多來自政務後勤能力,當屬“勞績”或“招撫功”,而非直接的“戰功”。曹氏軍功多屬勤衛輔助型,對軍事有其佐助之功,然後受到上司賞識,成為晉升的一大基礎,豈曰與軍功毫無干係?
但曹振彥、曹璽的軍功也談不上“軍功赫赫”。《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在《凡例》曾說:“尼堪等姓,軍功顯著者甚少。”聯絡曹氏的包衣身份、宦途經歷、極少的軍功記載以及曹寅的回憶,可推知:曹振彥、曹璽的軍功實際上並不多,且含金量也不是太高,遠不如五房曹恭誠一脈,相比滿漢名將更是不值一提,否則其後代應當會大加宣頌。可從現有的清廷封告、旁人評說、曹寅詩文中看不到此類記載,因此不能誇大曹氏軍功。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曹氏之所以能夠評敘軍功,主要是因為滿洲大兵得勝和相對模糊寬鬆的軍功則例,以及多爾袞等權臣的聲望,才能勉強混在官兵中分一杯羹,實際上作用並不突出,更絕非不可替代。故若說曹振彥、曹璽“戰功赫赫”或者“軍功世家”恐怕離史實太遠。但曹氏經歷了戰爭磨礪,多少還是繼承了先祖的一些軍功風尚。那曹寅在曹家武運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軍功泡影夢
康熙十三年,吳三桂、耿精忠等相繼叛亂,引起天下震動。曹寅《句容館驛》一詩說明當時曹寅已離京南下,協助乃父曹璽籌辦防務。有學者認為曹寅到句容,是協助乃父參與揚州或江淮防務。此說不妥。曹寅和乃父參與的應該是江寧防務。為何?當時清廷在江浙的兵力和戰防中心以江寧和杭州為中心,而非揚州。從諭令來看,江蘇揚州雖鬧過水災,卻基本無警,守衛價值不大,因此康熙並未釋出防守揚州的諭令。康熙十三年,康熙徵調江寧兵力馳援浙江平定耿精忠,造成江寧防務空虛。江寧一旦有失,大局恐有決裂。這引起了康熙的高度警覺,故多次下旨令包衣左領、八旗軍等前往支援。史稱十三年在京部分侍衛奉命參與了江寧防務。曹寅是包衣兼侍衛,本身就是禁旅一員,是有很大機會的。再就政治地理來講,二人所到的句容隸屬江寧省,是其東南要衝,臨近浙江耿精忠部,因此成為南防耿精忠北上的要地,構成了江寧大防守的一環。所以他們當時參與的應是江寧防務,而非揚州防務。
由於江寧無戰事,所以父子倆在當地從事的主要是後勤工作,沒有戰功。而相比要員曹璽,青年侍衛曹寅在戰防中的角色無足輕重。雖然如此,年輕的曹寅卻常常想快馬彎刀立軍功。
康熙十四年三月前後,北京外圍爆發蒙古察哈爾王叛亂,而“禁旅南征,宿衛盡空”,形勢危急。康熙聽從孝莊太后的意見,派圖海徵集了京八旗和“家奴之健勇者”,揮師北伐,不到兩個月就粉碎叛亂。勝利後,康熙大加封賞。但多愁善感的曹寅卻從未在詩文中提到這次戰役。根據史料推演,弓馬嫻熟的青年曹寅錯過了這次戰役。一種原因可能是當時曹寅不在北京,尚在南京與曹璽協助防務;察哈爾王叛亂髮生後,康熙因慮京防空虛,將曹寅在內的不少禁旅重新召回北京;曹寅奉命北返後,叛亂已被平息了,故沒有平叛的親身經歷,也就談不上印象深刻,卻因南北奔波備嘗軍旅反覆之苦,沒有時間寫詩抒情,導致他兩年間基本未做詩,直到康熙十五年北京局勢穩定後才開始增加詩文。另一種可能是曹寅已在北京,未能參與前線戰鬥,卻因扈從雜役,備受軍旅煎熬。《不寐》曾雲:“曉車如秋潮,雷鳴過空堂。塵役苦無厭,附躬自彷徨。”
曹寅雖未經歷蒙古平叛,但卻經歷了漫長的三藩戰爭。不過曹寅心有餘而力不足,被圈在京城扈從康熙,不能親身參與作戰殺敵,只能以旁觀者的角度看待這場戰爭,也就無所謂什麼戰功了。
儘管如此,曹寅身在樊籠心在外。他創作的《宿來青閣》《冰上打球三首》《聞恢復長沙誌喜四首》《喜雨紀事》《過甘園》等詩歌,與戰爭密切相關。曹寅用詩歌體現了自己關注戰局的進展,對重大戰績深表欣喜,欽佩和頌揚康熙的光明偉大正確,對戰亂中的百姓多表同情,對陣亡的親友更是深感難過。不過若要認為曹寅以天下為己任,時刻關注戰局和民生疾苦,以至於積極毛遂自薦南下作戰,未免異想天開。他所做有關戰時民生疾苦的詩文並不多見,且給人的感覺多像官樣文章,是寫給別人看的,不敢揭露清軍的腐敗無能。其詩文主要部分還是反映他在京城中的侍從、交遊、偶感和閒時趣好,恰好反映了他的生活偏向,透露出青年曹寅對京城生活和個人狀況的關注度,似比國家大事和民生疾苦要高。這與他的身份背景、狹小的生活圈子以及森嚴的制度密不可分。《圈虎》等不少嚮往閒適自由的詩,襯托出他京城生活的期盼與無奈。
面對三藩戰爭,他很羨慕那些建功立業的人,希望有朝一日創立軍功,光宗耀祖。《宿盧溝題壁》說得最為直白:“十年馬上兒,門戶生光輝。明朝挾弓矢,應射白狼歸。”但有意思的是,在說完豪言壯語之後,往往一轉身就去與文人僧侶交結唱和,拍康熙的馬屁,沉湎詩酒,然後不時做些閒適叫苦甚至愁怨的詩。因此“軍旅詩”的比重要明顯低於“閒怨詩”。這種反差體現了他對自己的軍功夢亦即亦離和內心深處的掙扎。他曾酒後賦詩:“人生貴自足,所獲良不誣。”或許正是掙扎之後聽天由命的選擇吧。
曹寅之所以說“貴自足”,就是因為在三藩戰爭中,面對戰事的不利乃至親友的被殺,實際上曾有多次的“不知足”,很想效仿先人,殺敵建功,萬古留榮。曹家祖孫三代,始終有一心結,即改換“下賤包衣”的身份。曹氏作為滿人家奴,表面看似風光無限,但實則在夾縫中生存,生死榮辱全憑帝王的無常喜惡,稍有不慎便會家破人亡。若能南下立功,曹家從此揚眉吐氣,可藉機脫籍出頭,走出包衣家奴的陰影,洗刷身份恥辱,建立相對穩定的家業,實現“門戶生光輝”。
可是康熙始終沒有給他這個機會。誠如鄭天挺先生的分析,包衣制度滿足了滿族權貴既想避免宦官干政之禍,又想得宦官內務之實用的雙重需要。作為包衣的曹寅,文武兼備,滿漢皆熟,性格忠順,可謂是服侍康熙、充當眼線的優秀人選。深諳帝王心術和康熙豈有輕放和不用之理?在這些情況下,曹寅幾乎沒有南下作戰立功的機會,被康熙牢牢地拴住,無法改變家族的政治社會地位,只能繼續扛著父輩身上的低賤標籤,被康熙反覆利用。曹寅終其一生,為康熙當牛做馬,勞績甚多,更因連續接辦康熙南下花銷,以致敗家,但康熙直到其臨死都未讓他及子孫脫籍出頭。這是曹寅的人生悲劇,更是滿洲權貴強加給他的悲劇。
漸變的後代
中年的曹寅,心態已老,再也不願涉足危險的軍旅,使曹家的軍功風尚逐漸從主家轉移到旁支脈。康熙三十五年,曹寅二弟曹荃於康熙三十五年扈從康熙參戰平叛噶爾丹之役。康熙三十六年春,康熙第三次親征噶爾丹,其間曹寅曹荃之親叔曹爾正也參與其中。康熙三次親征噶爾丹期間,清軍普遍缺水,不少部隊還常有缺糧的問題,以致大批官軍兵困馬乏,吃盡了苦頭。康熙第二和第三次親征的時間均選在了春季,正處西北少雨乾旱時期,軍中乾渴可想而知,且又因路途遙遠,大軍糧餉接濟困難,以致不少部隊人馬飢疲。像曹荃曹爾正這類低階扈從,捱餓口渴在所難免。而戰時有不少人直接陣亡,或因缺糧水、染病身亡。曹荃曹爾正見到死屍為正常事,從死人堆裡走出來是說得通的。這段特殊資歷對曹荃爭奪家權、繼承家業有了更多的人脈和資本。
儘管兩兄弟履歷如此豐富,但曹家的軍功教育並不到位。一則康熙後期,八旗的軍事教育普遍下滑。二則曹荃英年早逝,曹寅子嗣凋零,曹家苟安享樂。曹寅等人對後代的騎射教育,主要是在家內進行,訓練強度不大,技術難度不高,更未將其推進軍旅進行艱苦磨礪,學習真正的作戰本領。他們演練騎射,多是按例而行,實已退化。曹寅後人喜歡抓“巧宗”,走捷徑,選擇花錢買官,不會對家業之難有多少切身體會,反會進一步加速衰敗。若曹氏後人反思家族興衰的話,應該會重點提及軍功風尚的蛻變。
巧合的是,曹雪芹多次在《紅樓夢》中追念家族軍功史,批評軍功教育的退化。第七回、第二十七回、第五十五回的軍功追憶便是例證。周汝昌先生認為第七回影射了曹家扈從西征的軍旅史,可作參考。另外,第七十五也描寫了賈珍“較射破悶”的鬧劇,與曹家後代荒廢變質相近。賈珍因居喪無聊,邀集紈絝“比箭較射”,暗地裡吃喝玩樂。賈赦、賈政不明就裡,“反說這是正理,文既誤矣,武事當亦該習,況在武蔭之屬”,遂命寶玉等人跟著習射。不料賈珍卻將較射蛻變成賭博,非但武功未成,反令賈府丟錢。比起尊重焦大的尤氏和念苦改革的探春,這些腐朽的鬚眉濁物,真是“上辱先人,下誤後人”!
曹雪芹在反覆提及賈家軍功風尚的衰退,並非是無意的,是有意藉此反思。他借焦大、探春等人,痛苦地反思歷史,進而警示世人要居安思危,飲水思源不能忘本,為人莫苟且,時時要努力!
清朝歷代都高度重視軍功,對立功人員往往格外施恩,使其進可升官發財,退可降罪保命;對內可拓展基業,對外可光宗耀祖。曹氏先祖傳承了先祖風尚,文武兼修,以致家業興隆。但是到了曹寅,在內外不利條件和苟安心態下,最終還是沒有成功,轉型失敗。後代受內外影響,不願參與軍旅謀取軍功,多選擇花錢買官,奢侈享樂。等到曹家後人醒悟過來,可惜歷史已經不給曹家多少機會了。高鶚後四十回有關探春遠嫁平海疆和賈家復興的續寫,可以看作是對賈家悲慘結局的同情。但小說歸小說,現實歸現實。無論《紅樓夢》與曹寅家族史是否吻合,歷史事實是殘酷的。曹寅一脈後期一蹶不振,而高鶚的續寫不過是一廂情願,再也無法實現了。
這也提示我們要區分好文學演繹和歷史現實的區別。文史互證,需要建立在確鑿的證據之上,而宏觀的歷史構建更要強調證據鏈的存在和完整。目前曹家所遺留的史料多屬片語殘跡,難以形成完整流暢的證據鏈。後人據此建構的圖景非常有限,且再建的圖景到底是否屬實,也是疑問,很難與小說細節完全對號入座。非要這樣,必會走火入魔,究竟能得到什麼?誠如紅樓的《好了歌》: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曹公編修紅樓,本意是想幫助世人洞明事實,“走出紅樓夢”,邁向真善美,構建更美好的社會。若我等自覺或不自覺地重新“扎進紅樓夢”,回到那個派系林立、爾虞我詐的世界,於人於己皆有不利,恐怕不是曹公所期望的。所幸人有常識理性。以往不少研究紅樓的英雄好漢,在紅樓內外磕磕絆絆數十載,最後都轉向寬恕與平實,無論對與錯,都是好事。若能都做到這些,真相大白於天下之日可能也就不遠了。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