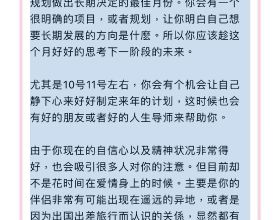“
法國無疑不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只是個由不同時期兼併而來的省份組成的聚合物,而哈布斯堡君主國則被描述成“一個由令人昏亂的異質元素組成的有輕微向心力的黏結團”,那是羅伯特,埃文斯概括哈布斯堡君主國的多元化時說的話。我們只要念一念約瑟夫二世的頭銜,就能很好地體會這個君主國的多元化程度:
約瑟夫二世,羅馬皇帝,匈牙利、波希米亞、達爾馬提亞、克羅埃西亞、斯拉沃尼亞、加利西亞、洛多梅里亞使徒國王,奧地利大公,勃艮第、施泰爾、克恩滕、克賴恩公爵,西本彪根大公,摩拉維亞藩侯,布拉班特、林堡、盧森堡、蓋爾登、符騰堡、上下西里西亞、米蘭、曼託瓦、帕爾馬、皮亞琴察、瓜斯塔拉、奧斯維茨與扎托爾公爵,士瓦本侯爵,哈布斯堡、佛蘭德、蒂羅爾、亨內高、基堡、格爾茨與格拉迪斯卡侯伯,神聖羅馬帝國藩候,布林高、上下盧薩蒂亞藩候,那慕爾伯爵,溫迪施邊區、梅赫倫領主,洛林與巴爾公爵,托斯卡納大公。
為了防止萬一漏寫某個頭銜,這樣的清單通常會以“等等”的套話結尾。哈布斯堡的屬地包括今天的比利時、盧森堡、荷蘭、德國、奧地利、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波蘭、烏克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塞爾維亞、黑山、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和義大利的全境或部分地區。正知哈羅德•坦鉑利爵士所論、哈布斯堡君主國井不像是一個國家,倒像是自己形成了一個大洲。
法國或許已經“差異大到了荒謬的地步”[費爾南,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語],其中一個重要差異就是語言,法國有兩種明顯不同的法語(奧克語和奧依語)、四種外部語言(巴斯克語、布列塔尼語、弗拉芒語、德語),以及多達30種互相無法交流的方言,然而這種多樣性與哈布斯堡王朝需要努力解決的語言萬花筒比起來,就算不上什麼了。暫且不算奧屬尼德蘭說法語和弗拉芒語的居民,可以確認的主要語言族群有5個:說德語的人口聚居在奧地利和阿爾卑斯諸省,在波希米亞、匈牙利的城鎮和特蘭西瓦尼亞也有不少;義大利語使用者在南蒂羅爾(但這在當時包括—一現在也同樣包括一個“拉丁人”少數群體,他們說一種類似於瑞士羅曼什語的拉丁語)、米蘭、帕爾馬、皮亞琴察和托斯卡納形成了一個相對同質化的集團;講馬札爾語'的在匈牙利和特蘭西瓦尼亞;操羅馬尼亞語的在特蘭西瓦尼亞;最後還有使用各種斯拉夫語的人。最後提到的這個族群還可以被細分成三個部分:擁有持久存在的文化身份意識和書面語言的部分,比如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捷克人,或加利西亞的波蘭人;擁有尚處胚胎階段的獨立身份意識,但沒有明確民族自覺意識的部分,如匈牙利王國的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還有那些因文盲而被忽視的“湮沒民族”,比如加利西亞的羅塞尼亞人(或烏克蘭人)、匈牙利北部的斯伐克人,他們的存在得等到19世紀才會被民族學家發現。此外,在加利西亞、匈牙利、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還有人數頗多的說意第緒語的猶太少數群體。這還不夠,拉丁語通常在學術和宗教講話中使用,在匈牙利,它也被用於行政和司法。實際情況比這個分類還複雜,因為各個地區之內,語言也是混雜的。特別是在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廣闊的匈牙利王國與特蘭西瓦尼亞等地,有著不同文化和語言的群體帶著不同程度的相互仇視生活在一起。
截至1648年,哈布斯堡王朝已經成功擊敗了存在重疊的兩個群體:新教徒和“世襲領地”上的貴族。世襲領地也就是主要說德語的核心領土[上、下奧地利,福拉爾貝格( Vorarlberg ),蒂羅爾,施泰爾,克恩滕和克賴恩]和“聖瓦茨拉夫王冠領地”(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西里西亞)。這並不是一個可以預知的結局,因為16世紀晚期時,奧地利貴族主要是新教徒,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在位)也同情新教。關鍵的日期是1620年11月8日,當時,一支由巴伐利亞人、西班牙人、瓦隆人、德意志人、法蘭西人(其中還有笛卡兒)和奧地利人組成的多民族天主教軍隊擊潰了波希米亞起義軍。儘管花了很長時間,但聯手的天主教和王室權威最終還是被強加到了世襲領地上。次年6月,27名波希米亞貴族和市民在布拉格舊城廣場被公開處決,處決景象被人以畫作形式記錄下來,以便給時人及後世子子孫留下恐恐怖警告。大學校長揚·耶森斯基 [ Ján Jesenskg,亦作揚·耶塞紐斯( Jan Jesenius)]的舌頭在斬首前被拔了出來,釘在了墊頭砧上。1624年,官方宣佈天主教為唯一合法宗教,3年後,依然不信奉天主教的波希米亞貴族和市民接到命令,要麼改宗正確的信仰,要麼移居國外。據估計,有20%左右的波希米亞、摩拉維亞貴族(大約85個家族)和25%左右的市民選擇了流亡。在白山會戰後的幾年裡,共有約15萬人流亡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