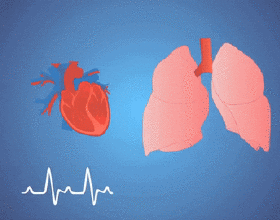1912年9月28日,中華民國參議院透過的《國慶日紀念日案》正式公佈,該案仿效美國紀念十三州獨立建國、法國紀念大革命的先例,規定以武昌起義日(即公曆10月10日)為國慶,舉行放假休息、懸旗結綵、大閱、追祭、賞功、停刑、恤貧及宴會諸事。就在3天前,上海革命黨人所辦的《民立報》刊登主筆徐血兒撰寫的評論:“吾望國民早日預備,以示吾民對於共和之熱忱”。如何慶祝共和,一時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在不到半個月的極短時間籌備慶祝事宜,自是社會觀瞻所繫。
百十年後察看時人記錄,對時局看法的分歧赫然在目,與民國感情的親疏有跡可循,文字機鋒可堪玩味。時為溥儀宮中內務府大臣的紹英就寫下當天“為陽曆初十,民國國慶日,國務院請茶會,並送入場券一紙”,他藉口“早間進內,且大、常禮服均一時不便”推辭不去,在家休息。任職北洋政府教育部僉事的周樹人(魯迅)尚無資格參加總統府、國務院舉辦的活動,他與朋友一行五人“觀共和紀念會,但有數彩坊,而人多如蚊子,不可久駐,遂出”。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刊行的《魯迅全集·日記》中,編者有如下注釋:“指中華民國首屆共和紀念會,在北京琉璃廠廠甸舉行,到會群眾約十萬人。宋教仁擔任大會主席。會場內設陳列館、運動場、演劇場等。”這一說明大體準確,但失之過簡。在臺灣居住的掌故家高拜石寫過《記琉璃廠第一屆國慶》一文,對於事情的前因後果敘述稍詳,指出孫中山、黃興均應邀為籌備會發起人,紀念會會期為三天。高的文章有所本,披露了一些細節,如慶祝大會“原定以天壇為會場,後以地址遼闊,改在琉璃廠舉行”。不過,為何會場“遼闊”就必須改換場地?作者語焉不詳,讀者未免疑惑。近年不斷有人談及民國首屆共和紀念會,卻存在史料不夠全面,敘述間或有誤,甚至有建構史實的傾向。恢復這段歷史的本來面目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在琉璃廠舉行的共和紀念會不是由民國政府組織,不能視為官方活動(儘管獲得了政府要員的金錢贊助),而是由原同盟會(新改組為國民黨)會員所領導,經費也由他們籌集。9月初,革命紀念會在北京成立,發起人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張繼、陳家鼎、田桐等,陳家鼎、張繼是關鍵人物。經與孫中山面商,陳家鼎撰寫刊佈了《革命紀念會發起意趣書》,認為國民知曉國史,國基才能穩固,歷史觀念、美術教育對於培養國家認同非常重要,“非有歷史的警惕、美術的觀感,則遺忘共和於腦後、橫齷齪於胸中”“我國最大最速之革命,自應有最高最久之紀念,方足示天下、昭來茲”。陳氏又稱,革命本來是在野之事,政府設立稽勳局代表國家賞功褒忠,在野人士組織革命紀念會則是“存神聖革黨之精神於社會,垂雄偉莊嚴之大訓於千古”。據《民立報》報道,陳家鼎負責草擬章程、聯絡溝通及籌集款項等日常具體事務,“鼓吹運動不遺餘力”,故被推舉為紀念會總理。紀念會職員分為總務、庶務、會計、交際、文牘、接待等,各司其職。紀念會宣稱自己不是政治組織,但不少成員是來自南方的同盟會會員,尤以湖南籍人士為多。紀念活動的非官方性質,當年《時事新報》說得非常清楚:國慶典禮之事,由革命紀念會主辦,而由政府協助。該報解說原因有二:一是民國政府尚未得到列強承認,不便接待外賓;二是當時政府財政困難,民間主辦可節省費用。
其次,由組織方取名可知,原擬召開的是“革命紀念會”,但在開幕時卻變為“共和紀念會”。這倒不是北洋政府施壓,淡化意識形態色彩,而是出於革命黨人主動自覺。黃興來京訪問,參觀過琉璃廠擬用會場,被推舉為大會主席。9月27日,黃興致函陳家鼎建議活動更名。10月6日,黃興離京抵津,陳家鼎徑電其所寓利順德飯店,告知經全體會員商議,同意黃興的提議,並希望其派代表主持。黃興此舉為何?這與他的政治判斷有關。黃興認為建設“共和”迫在眉睫。他在9月9日同盟會天津支部歡迎會上稱,“共和兩字乃理想中的空名詞,如欲達成真共和,尚須人民之實力”。不過,觀察現存紀念會場的攝影照片,雖然琉璃廠彩坊上均題為“共和紀念會”字樣,但是門前飄揚的大旗上“革命紀念大會”赫然可見,這就是說“革命”“共和”曾一起出現在歷史現場。黃興的另一重要建議是將會期改期。革命紀念會成立後,一直定在9月29日開會。在陳家鼎等人看來,紀念需使用陰(舊)歷,這天即陰曆八月十九日,正好距武昌首義一週年。革命黨人仇亮所辦《民主報》25至27日刊出的紀念會廣告,舉辦日期都是29日。黃興建議避免不必要的新舊曆之爭,而是按照參議院決議執行,“以歸劃一而垂永久”。據《民主報》《申報》在28日登載的廣告,開會時間已經變為雙十了。延後舉辦,籌備時間更多,所以有人提議更換地點,轉場到具有象徵意義的天壇。不過一旦如此,不少在琉璃廠的投入就要化為烏有,天壇寬闊,修整裝飾所需巨大的人力物力將是棘手問題。雖獲知政府將予以資助,陳家鼎等人還是堅持照舊在廠甸舉辦紀念會,但將提燈遊行、施放煙花等活動地點定在了天壇。
再次,有人撰文認為北京舉行的追祭儀式中,佈置有象徵“五族共和”宗旨的綵樓、陳列“中華民國為國死事諸君靈位”體現的是北洋政府的意志,認為靈位名稱不能很好表彰革命烈士,“而且曖昧地包括了北洋軍戰死將士”。這實是倒讀歷史、純屬猜測。這座靈位設立在琉璃廠中,名為“追悼臺”。《革命紀念會發起意趣書》中明確指出,革命成功應歸功於全體人民,“本會大旨,南北軍人死於戰地者,皆為革命功人,不以方隅囿也……東西南北何地不可建光復之碑,新舊官民何以不可與獨立之祭”。組織方排演戲劇《共和魂》的說明書也透露該劇結局將是“敘五族大同,南北一家,用作新中國無上光榮之永永紀念”。據《時報》所刊專電,在籌備時原擬展示南北交戰的海陸軍“戰利品”,有人因“恐傷南北感情”提議中止。另據《申報》事後披露,陳家鼎邀請民族大同會的恆鈞加入紀念會辦事,還在會場懸掛遜位隆裕太后、前攝政王載灃的照片,“以示大同而彰美德”。陳家鼎等人在清末編輯《洞庭波》《漢幟》時動輒呼籲“驅滿酋”“殺漢奸”,但這時主動伸出橄欖枝,格局顯然變大了。為了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紀念會邀請內蒙古章嘉活佛等人到現場演說,號召蒙古族、藏族“共享共和幸福”。眾多喇嘛在追悼臺誦經、做法事長達數小時。三年之後的雙十這天,立場相對中立的上海《新聞報》發表評論總結:“第一屆國慶,中華門開幕而外,以琉璃廠之共和紀念會為熱鬧,……是為黨人全盛時代。”
晚清民初的“共和”一詞具有極其複雜的含義,在歷史文獻中要視具體語境來理解。除去學理解釋,回到歷史現場,不難發現時人心目中的共和,也有“團結”之意。另外,革命黨人還保持有鬥爭精神,並非簡單“和稀泥”,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有著堅定立場。陳家鼎等人一直主張追究黎元洪串聯袁世凱,在殺害革命黨人張振武、方維一案中的責任,指摘其在民國成立後犯過“十大罪狀”。這一斗爭不僅在議會辯論、報刊輿論中展開,也在紀念會場中體現出來。一方面,會場展示的武昌首義元素不少,尤其所設計的“黃鶴樓”模型精妙絕倫;另一方面,槍斃張振武的照片在陳列館(地點在琉璃廠工藝局內)裡予以特別展示,在會場中則“不設黎副總統像”。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讀者想更多的瞭解民元北京舉辦包括琉璃廠共和紀念會在內的首屆國慶節的往事,不妨找來《民立報》連載“國慶日之北京”等專題報道一讀。
(作者左松濤,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