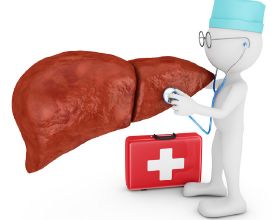應該在一九六六年以後罷,認識了張學銘先生,他剛從監獄放出來,我的貓頭鷹案子還未有結果。
怎麼認識的,誰介紹的,忘記了。可能是跟我有過來往的他家兩位公子的介紹,想想又不像;可能是在那個時候崇文門新橋飯店東向的西餐館認識的。也記不住認識的過程。總之是認識了,來往了。
抽菸斗的大畫家黃永玉
壹一坐就是一整天
我和他不一樣,我沒有後臺,日日惶惑;他不同,他的哥哥是張學良,有周總理時時關心照顧;丈人是朱啟鈐先生。朱啟鈐先生我憑什麼有膽提起?他是新建築系統的祖師爺爺,做過中國的總理和一系列的大官,只要講大白話,老百姓聽了就明白了:北京大前門是他蓋的。
張學銘先生常常到當年我那個侷促的罐兒衚衕家裡做客。我那個住家窄小到任何客人做個小移動,屋裡頭全體人馬都要站起來讓路。張先生高大的中型胖子,見過全世界大場面的人,那時候能找到個隨心交談的人真不易,居然一坐就是一整天,上午來,聊、聊、聊,吃中飯,喝茶,再聊、聊,吃晚飯,吃大西瓜,再喝茶,再聊,九點鐘,起立,再見。我們送他出門。
我去過他家,見過洛筠夫人,傢俱陳設都很講究,床頭牆上隨隨便便掛著兩幅龔半千。房子位於東四八條111號。我說這四合院不是普通的大,不要說以前沒見過,聽也沒聽過。解放那麼多年了,就那麼從容闊亮在太陽底下,一點不受驚擾,尤其是從沒受到街道居委會的掛念和關心,這是非常難得的。
太陽按規矩每天從東邊照到西邊,隨便哪進繞院子小小跑個圈很容易累得主客不分。這是個比喻,是個估計,說明院子大得非同凡響。做客喝茶是有的,跑圈沒發生過。
我一輩子記地址的天分很低,常來常往的地方竟然把一個那麼有名的地點忘記了,再也叫不出名字。仔細想想也不能光怪天分。舊時代,全中國大大小小城市,中間重要馬路無論寬窄不叫中山路就叫中正路,我從小認馬路的習慣讓孫中山、蔣介石的名字搞混了,這又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一輩子的事。解放後沒聽說哪個城市、鎮大馬路用國家主席的名字取名字。用偉人與名人名義做這做那很容易搞亂記憶,淡化輕重,這是事實。朱先生在我心中的分量太重了,尤其是我尊重的長輩講到朱先生時也不斷地詩一般地讚美。
從文表叔有次對我說:“朱啟鈐先生的子孫繁衍,換家人家是養不活的。光是女兒就有九個,加上兒子媳婦,要多少房子裝?聽說,女兒、兒媳清早起來穿的是牡丹花苞的漳絨料子旗袍,中午換成盛開的大花,晚上換伏收的朵子。”話不一定真,不過傳得很美。實際上只有他們一家做得到。
你知不知道漳絨是什麼?天鵝絨的料子按設計的花樣用剪刀平平貼貼地剪出高低層次的花樣來,這是種很珍貴講究的手工技巧。
請原諒我把話扯遠了。想想看,寫張學銘不提一提朱老先生豈不欠打?專門要寫,幾十萬字的厚本本也不夠,這位那年代忘不了的文化高峰。
學銘先生在不同時代做過東北的大司令,小司令,大大小小不同的官,做過天津市長,警察局局長,顧問,人民公園主任。值得一提的事:委託章士釗先生轉請毛主席題了“人民公園”四個大字,做成黑底金字掛在公園正門下方。這恐怕是毛主席親筆為國內公園題寫的唯一匾額。
我們認識以來從不提上頭說過的那些事,頂多是我從熟人口頭或報章雜誌上看到的。這些過去的事好不值得來回細論?他只談他年輕時代和有趣的人的交往。
貳活現“王道源故事”
他說:“我當天津市長的時候還很年輕,一個人到日本去玩。別瞧我在天津發號施令神氣活現耍大王,到了東京住進旅舍就孤家寡人單獨一個,找到了你們畫家王道源。”
我說:“王道源先生我在廣州見過,他在廣州華南文藝學院教油畫,一臉大鬍子,一頭捲髮,有點馬克思的神氣。”
“是那麼回事!很有點氣派,有他在一起,我放心了一大半。他這人有個特點,喜歡玩派頭,愛把走在一起的朋友當作馬弁跟班,大街上昂揚至極。完全甩開走在一起的朋友。你清楚我是個愛吃的人,我們兩個個都不小,整個禮拜簡直吃遍了東京著名的大小餐館。有一天吃完午飯他說:‘我帶你到黑社會的黑龍會咖啡館喝咖啡去!’我問他:‘熟不熟裡頭的門道?’他說:‘管他媽的熟不熟,去了再說。’”
這咖啡館名叫“A、Z、Q”,一進去黑不溜秋,又寬又矮。座位全是藤躺椅,中間擱了張小咖啡桌,算不得神秘,也不簡陋。我們兩人各自躺下,王道源大概是剛才的午餐吃累了,閉下眼睛。我怎麼睡得著?看看吊燈,看看牆上掛的神怪畫,聽那些怪腔怪調音樂。
這時,咖啡送來了。茶具頗為講究,王道源睜開眼睛,小調羹在杯裡攪了攪,既不放牛奶也不放糖,猛猛地舉起杯子喝了一口,眼看杯子裡頭剩下小半,擱著不動。煙盒裡取出支大雪茄,點燃抽將起來。火點得大,抽得威猛十分。我咖啡裡放了糖,也放了牛奶,用勺子攪了攪,輕輕呡了一口,覺得不錯,正欲躺下閉目養神,忽然來了位赤膊胖漢,上半身刺滿紫紅色游龍刺青。雙手撐住王道源一左一右扶手上。臉孔、鼻子相隔五六寸光景,像似在交換呼吸,一邊抖動上半身肌肉,讓“游龍”生猛起來。
你說我那時怎麼辦?我嚇得動彈不得。
王道源一聲不響狠狠抽了口煙,噴出個又圓又大的菸圈,優雅地,準準地套在那漢子脖子上,那漢子起身撥了一撥;沒想第二個大圓圈又套上了,那漢子剛撥開第二個大煙圈,第三個菸圈又跟上來……王道源從容吐著大煙圈,看也不看那漢子一眼。
那漢子一聲不響地溜了。
“你這兩手,我還真沒想到!”我對王道源說。
“抽菸吐個大圓圈,這算得什麼本事?”王道源說。
“你最近見過王道源麼?”張學銘先生問我。
“我只是解放初在廣州見過他。知道他在日本多年,在中國美術界活動得轟轟烈烈、多姿多彩,是位滿腔熱血的畫家和教育家,為民主革命做過不少貢獻。就是他跟畫家、金石家錢瘦鐵先生把郭沫若先生掩護回國的。聽說他沒逃過‘反右’劫數,1960年死在勞改農場。”
後人懷念他,稱他作“美術史中的失蹤者”。他一生在文學藝術界非常活躍,實心實意參加各種益人的藝術活動。快活複雜的身世,後來向組織方面交代起來,令人感到生鄙和很不耐煩,更加上不善於政治語言表達,這都是一些遺憾的事……
“你想想這個王道源!黑龍會咖啡館當年噴菸圈的派頭和膽子也不曉得縮到哪裡去了?”張先生說。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啊!”
“跟你來往無害,不江湖。”他說。
叄“他去世了?我怎麼不知道?”
“北京崇文門內新橋飯店東門開了家西餐館,過得去。西直門那家莫斯科餐廳,黃油雞卷、羅宋湯。地方遠了點,費鞋。”問他城裡幾家本地西餐館,他聽了輕輕說:“豈!”說“豈”,他又常在那裡請客。“地方家常”,“公安局後臺,安全。”
幾乎北京大飯館,沒一家不認識張二先生。今天哪家出什麼菜?他說可以,或不可以;說今天他們進的鴨子不新鮮,青島對蝦放了四天!他哪兒來的訊息?你受不受得了!怪不怪?
那時期過日子緊張,得他的指點很得益處。問他:“您等於一年到頭不在家吃飯。師母怎麼辦?”
“她?她吃飯有頓沒頓的,打電話叫館子送。飯碗,菜碗,湯碗,調羹筷子都撂在大桌子上,飯館來人各認各的碗回去,有時還吵起來。”
有天,張先生一大清早來罐兒衚衕找我:“快……快!今天崇文門外XX屯趕集,我們去那兒選只小豬回來烤著吃,快點!”我說:“我不想去,麻煩,走那麼遠路,回來還要背只小豬,還要花時間殺豬,洗呀,烤呀……”

“你看你,還是個年輕人,還打獵。你騎腳踏車,我坐公共汽車,到崇文門換車,換不到車不過十里八里!哎呀!回來全部的事有我嘛!沒有你,我自己也不幹,就圖的這份味道。你,你,好,好!多可惜呀你,你看你,你看你……”
“你該找允衝、鵬舉兩兄弟陪你弄這些玩意,他們年輕。”
“你想想!他們配嗎?他們有這種興致修養嗎?我怎麼會叫他們兩個?無聊,我做夢都沒想過……”
在我家吃飯,梅溪出名的手藝,他不說好也不說壞,飯量顯得出眾,一碗一碗。
有回聊天,提起一件事,他有點生氣,“‘文革’時期,北京某個大學出了本大辭典,張學良這一專案裡頭說:‘張學良從小當大官,是個花花公子,已去世。’這簡直豈有此理至極。說他從小當大官,是個花花公子,我沒意見,說他已去世,怎麼他們知道,我做弟弟的反而不知道?張學良如今好好地活著。怎麼回事啊!王八蛋!狗日的!”
這話我找不到角度安慰和勸勉他。
朱啟鈐先生去世好些年了,後來某一進四合院給人住了。有本事住進這院子的絕非凡類。果然。原來是我們湖南鼎鼎大名的唐生明先生。他的哥哥是唐生智。我從小知道一件事,家母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師範畢業頒發的紀念品銅墨盒,上面清清楚楚刻著唐生智贈的大名字。
唐生明在抗戰八年是位出名打仗的將軍。我再長大一點的抗戰八年之後,又聽說蔣介石曾派他到漢奸汪精衛那裡去混,立了不少抗戰功勞;全國解放之際,唐生明先生在湖南和平解放中起了不小的作用。特別精彩醒目的是一篇他在汪偽時代如何毒死大漢奸李士群的文章。他一輩子過的都是風花雪夜的日子,恰好運用這種花花公子擅長的天分進行對革命有益的工作,何樂而不為也?
我有一套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講的都是這類有趣的人間奇蹟。
大概是張先生向唐生明先生講過我一些瑣事,唐先生想約我有時間到他那裡喝下午茶,我去了。
見到唐先生,晉了禮;夫人徐來是畫報上的熟人,也行了禮,坐下了。
我說:“我媽是桃源省二師範的學生。”
他說:“現在有些老頭子居然說自己是省二師範畢業的,簡直荒唐,無異講男人生男人。根本不清楚省二師範是個專門女子學校。比如現在的高幹子弟學校101中學校長楊代誠(王一之)就也是省二師範的。我以前開賀龍的玩笑,他常到桃源省二師範去找女朋友……”
我說:“王一之先生是我媽同班。她還有很多同班,鳳凰陳渠珍的大夫人楚玉美也是當時的同班。”
咖啡來了,喝咖啡。
唐先生問:“聽說你平常常出城外打獵,北京有什麼東西好打的?”
“有,有,北京到冬天,麥子割了,郊外一展平,幾家農屋,幾樹山裡紅柳。打得到兔子,雁鵝,居庸關一帶山崖上還打野山羊……”我說。
“那太辛苦費力了。”他說。
“我平時除教書之外自己還刻木刻,小刀子對著大刻板,眼睛離板子頂多六七寸,慢慢容易弄壞眼睛。禮拜天夾著獵槍到城外走走,一目五里、十里,眼睛給調整好了,對工作和身體都有益處。”
“我也打獵,兔子,巖鷹,野雞,鵪鶉,山羊,都打過。”他說。
“剛才你不是說過,打獵你經不起累。你怎麼打得下那麼多東西?”
“你忘了我是個當官的?滿滿一座嶽麓前後山,哪裡沒走過?我用得著走嗎?我不會坐在轎子上麼?轎伕抬起我滿山走,見什麼打什麼,打不著後頭跟著的大隊護兵不會補槍嗎?不會打不中的。坐在轎子上瞄準很舒服,容易屏氣,槍就放在膝蓋上。轎伕也見機行事,走著走著,東西一出現,馬上停住腳步讓我瞄準,上山打獵,要緊的是靈活的轎伕。”
我回香港住了幾年,回北京之後,這些先生們都沒有了。
(黃永玉 寫於2021年9月11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