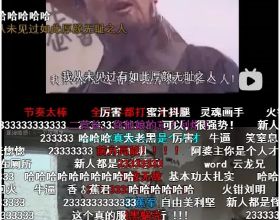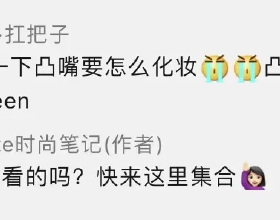說起合影殺手,一般遵循這樣的路徑:
普通人被網紅殺、網紅被小明星殺、小明星被大明星殺、大明星被超模殺、那超模呢?
被傳奇演員殺……
對,這個傳奇演員說的就是蒂爾達·斯文頓(Tilda Swinton)。
走路帶風、制霸秀場的傳奇超模琳達·伊萬格利斯塔,跟她在一起,變成了大姨…
家世優越、貴為香奈兒座上賓,從十七歲起就躺著賺錢的卡拉·迪瓦依,跟她同框,變成了城鄉結合部小妹…
被人誇讚坐在木桶裡都能讓木桶變時髦,氣場強大、sense頂級,以168cm的身高闖蕩巨人國且順風順水的凱特·莫斯。
在她旁邊,被襯出了絕望主婦的感覺。
那麼超模天花板吉賽爾·邦辰呢?也是很順利地成為了一名經紀人…
合影亂殺的情況,當然並沒有止步於超模圈。平時沒少讓其他演員心塞的大魔王們,也同樣難免被打擊的命運
這是凱特·布蘭切特:
這是查理茲·塞隆:
難以想象,女王們的鋒芒和氣場,就這樣被輕易地化解掉了。誰是真正的大boss,一目瞭然。
總之,她在哪裡焦點就在哪裡。管你是伏地魔:
小鮮肉:
小美人:
比她高、比她壯:
還是比她有錢:
她都能讓你變成她的陪襯。讓你的C位,像是她有意讓給你的…
那麼問題來了:
蒂爾達·斯文頓的美究竟是從哪裡來的,怎麼能做到如此獨樹一幟、無堅不摧。
為了解析她的美,我們需要引入一個美學概念,那就是——間離感,即把她從人群和環境中區分出來的那種感覺。見之忘俗,描述的就是這樣的特質。
有關她美的一切要素,都與其有意無意製造的間離感有關。並非人們通常所說,是由其貴族及文化精英背景,鑄就的“玄學“結果。
她跟別人不一樣,但又不會那麼不一樣。其中的度,其實是在表情、服裝、髮型妝容,這幾個方面一點點磨出來的。
年輕時的她,臉上還有失落和憂愁。
但六十歲的她,只有淡然、堅毅和慈悲。在一眾充滿了慾望和煙火氣的臉中,瞬間被“間離”了出來。
另外,蒂爾達的原生髮色其實是棕紅色,但後來常常選擇以自然髮色中最超現實的白金色示人,這其實也是在追求一種間離感。
至於服裝造型,她“出眾”的高大身材當然是重要基礎,但剪裁的不俗和材質的精益求精,才是讓她成為一尊移動雕塑的關鍵所在。
我們常常用來形容杜鵑的“清冷”,其實是間離感的一個子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她成為內娛合影殺手的原因。
不過相比起蒂爾達,杜鵑的間離感並不那麼純淨,還是存在一些破綻的。
比如某些瞬間的輕蔑:
刻意:
和高傲:
都讓我們感覺到,她高嶺之花的好氣質,在很多時候其實還是在人的範圍內、在煙火氣的範圍內被討論的。
因為上面這些情緒都需要對面有人接著,才能成立。
而不是像蒂爾達·斯文頓那樣,讓我們感受到幾乎全然陌生的真正的高高在上,讓人恨都恨不起來,因為我們知道,“神不在乎”。
與此同時也就產生了某種崇拜的情緒,進而轉化為對於她魅力的高評價。
但要解釋為什麼蒂爾達和杜鵑總是會在合影中勝出,我們還需要了解間離感的對立面,也就是現實感。
所有她們合影中的手下敗將,無一不是輸在,與她們相比起來現實感過強。
比如這張著名合影:
楊冪是精緻傲嬌的小公主、董潔是由奢入儉的貴婦、春夏的臉上則寫著社恐的無助。
這些“人設”、氣息,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少見。
她們的笑與不笑、神情舉止都與他人的評價有關,因此不管是取悅還是反抗,都籠罩著強烈的現實感、都是接地氣的。
但杜鵑和蒂爾達就不一樣了。我們很少會在人群中見到這樣,不是為了證明什麼,自然而然活在自我世界裡的人。
愛恨糾葛、輸贏對錯、正義邪惡,都不是她依傍的東西。高冷和熱情都不是選擇,而只是反應。
她們就是“木秀於林”裡的那個木,而達科塔·約翰遜、楊冪、董潔、春夏們則組成了林。二者之間形成的對比,就是間離感。
更進一步的,把布蘭切特和蒂爾達作比較。我們依舊能在前者的臉上看到更多的現實感,比如“渴望洞察他人的慾望”:
但蒂爾達呢,她只是看著你。看你跟看一隻貓、一棵樹,似乎並沒有什麼區別:
我們常常所說的脫俗,其實就是這樣的感覺。間離感,也就指向了一種偏離常態的存在。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間離感的存在空間其實很狹窄。當偏離常態擴大到一定的程度,間離感就會變成荒誕或者怪異。
比如這樣的蒂爾達是有間離感的:
但這樣的她和這樣的Lady Gaga其實指向了怪異:
那麼在這種時刻,與她們的合影,就變成了“正常人”和“怪人”的合影,而不是“正常人”和一個“擁有著奇異美感的正常人”的合影。賽道不同,那麼比美紅利也就消失了。
所以製造間離感的重要原則是:
看上去有現實感,但又不那麼現實。簡單來說,就是把現實進行一定程度的陌生化,而不是完全再造現實。
說到這裡,有一個人不得不提,那就是瑞典導演羅伊·安德森。他的電影美學,幾乎就是建立在間離感之上的。
透過分析他的電影,我們可以更加直觀地瞭解到間離感是如何產生的。
比如電影《寒枝雀靜》中有一個場景是,一個肥胖的中老年男人在看外面紛紛揚揚的雪花,妻子在廚房裡忙碌。
聽上去很平淡吧。但我們看羅伊·安德森的具體表現:
是不是有一種很神奇的感覺。房子內的陳設、大家的穿著、所做的事、窗外的環境,都在暗示我們,這個場景是真實存在的。
但整體感覺又讓我們意識到,沒那麼簡單。整個畫面就像是紀錄片和動畫片的結合,現實,但又不那麼現實。
這是怎麼做到的呢。答案就是對那些浮在現實表面的元素,進行輕微的戲劇化調整。
比如把人臉塗成略微誇張的白色,把畫面裡的所有色彩統一在日常很難見到的某種灰調內。
以及將履行日常生活常規節奏的人,與0.75倍速的主人公進行對比等。
這樣的場景,在他的電影裡比比皆是。
比如下面這個舞蹈教室:
乍看上去很“正常”,但多看幾秒就會發現裡面的不對勁。
大家的動作為什麼像慢放一樣平緩,窗邊的女人為什麼會對著空氣指手畫腳,還有正前方這個蹲著的男人,為什麼看上去如此垂頭喪氣。
還有這個街頭軍官的鏡頭:
依舊是統一在灰調內的佈景,和偏離了常態的有特點的主人公(駝背、略微緩慢的動作等)。
總之,這些場景都讓我們意識到,眼前所見,大機率是一個被設計過的現實。
比起真正的現實,它擁有了深意和某種哲思氣質,讓我們看到了現實除去日常煙火氣之外的其他質感。
至於間離感與荒誕、怪異的邊界在哪裡,羅伊·安德森的電影也向我們提供了一些參考。
比如那個坐在地上打電話的白臉清潔工:
和突然闖入咖啡館的古代國王:
前者的氛圍主要是間離感,而後者則是荒誕。
除了視覺審美邏輯,間離感之所以會讓我們產生美的體驗,還因為透過製造和體察它,可以讓我們發現世界的豐富層次,“哦,原來它還可以是這樣的”。
進而體會到,“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驚奇。
與此同時,也不得不承認,這類創造間離感的美法,在當下這個講求互動效率的網紅經濟時代,很多時候其實都顯得有點不合時宜。
畢竟人們的時間、注意力就那麼多,有的是開朗親切主動取悅她們的美麗面孔。
所以有些美學現象之所以能夠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除了審美邏輯的完備,還包含了某種堅持。
審美在某些時候除了眼光,似乎還需要一些胸懷。就像陳奕迅在《打回原形》裡唱的那樣,“若你喜歡怪人,那麼我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