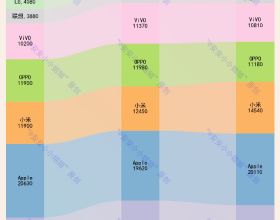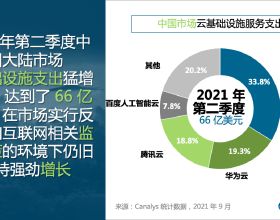還沒休假,我就把日程都排滿了,早起健走10公里,血壓偏高,跑是跑不動了;下午聽聽音樂,看看書,做做家務。那就這樣吧,多開心的假期啊!聽著小說,愉快的走在前住法界寺的鄉道上,一個月沒走,銀杏葉落了一半,秋日的美景展現無遺!
突然,前方迎面走來一個高大的身影吸引了我的目光“早啊,溫老師”我興奮的大叫,手不由自主的伸了過去,那個男人也緩緩伸出手和我握在一起,嘴裡遲疑地說:“你是哪個?我記不得你了”“我是四中十八班的,你教過我們政治的!”“腦梗了,一樣也記不得了”那個遲疑的聲音依舊緩慢的說。溫老師的滿頭白髮修剪的整整齊齊,灰白色的衛衣,黑色運動褲,和認識他的時候一樣,依舊乾淨整潔,左手依然擺成那個熟悉的姿勢,但神態已判若兩人。雖然,他已認不出我,但我拉著他的手捨不得放開,也許,有的人,一轉頭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了。看著他轉過身,把手裡的香菸遞到鼻子下聞一聞,扛到耳朵上,步履蹣跚的繼續向前走,嘴裡喃喃自語“老了,老了”,我忽然渾身無力,坐在路邊的石頭上,思緒已飛出了很遠很遠。
認識溫老師那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年紀啊,90年暑假過完,我15歲,剛走進初三校門的我離畢業只差最後一年,對走入社會外出打工掙大錢充滿了希冀和幻想。校園廣播裡反覆播放著戀曲1990纏綿的歌聲,教室裡,家境好的同學用我們想都不敢想的精美筆記本抄著港臺歌曲的歌詞,女孩子還在本子裡貼滿了黃日華、翁美玲的頭像。單位裡的幾位同學該玩就玩,該混就混,大不了讀個技校,一樣的進廠當工人;農村來的孩子家境好的都有了打算,回家經商的,辦廠的;我們幾個山裡孩子聚在一起,嘴裡聊著你家挖了幾擔土豆,我今年暑假在哪找到一窩雞樅,心裡卻很酸楚,再過一年,打工的路在何方。家裡的一畝三分地,連祖輩父輩都沒有吃飽,我們回去臉朝紅土背朝天一輩子,同是九年義務教育出來的,真的不甘心。
新課本和課表發下來,隨手一翻發現初二的法律常識換成了政治,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名稱,那是因為總聽收音機裡說這個詞,但一直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家裡的大人都沒上過學,肯定也不知道,哥哥姐姐們也說那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不用管,一副很神秘的樣子。隨著上課鈴聲走進教室的是一個高高瘦瘦的男人,大約30歲的樣子,誰知道呢。他戴一副近視眼鏡,穿著打扮記不住了,只發覺乾乾淨淨的,散發著一股好聞的香味,現在我知道,其實那就是肥皂的味道。他把左手攏在衣袖裡,自然抬起放在左腹腰帶位置,和我在電視上看到的一個偉人類似,後來才知道那是因為他左手殘疾,不能抓握任何東西,刻意藏起來了。“同學們好,我姓溫,大家可以叫我溫老師,也可以叫我老溫。今年我教大家政治。什麼是政治,其實我教了這麼多年,我也解釋不清,講了你們也聽不懂。但是由於這門課中考要考,關係到大家的中考成績,所以我希望同學們跟著我的節奏走,中考拿個50多分(總分60分)問題不大。不想上的也不要緊,你在下邊安安靜靜做其他的,不影響其他同學就行。”“老溫,老瘟”同學們已經在下邊竊竊私語了。老溫並沒有照課本講課,只是按步就班的翻開課本,讓大家把哪頁哪段哪幾句話劃下來,讓大家一起讀幾遍,然後同桌間互相督促著背,背熟的就自由活動,但下節課開始要先抽查的。於是,我們的政治課上的就很有意思了,大家用10分鐘把上節課勾畫的重點背一遍,用20分鐘把今天新勾出來的內容背熟,課堂上便都是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背誦聲。“既然大家都背熟了,提前下課又影響不好,與其吹散牛,那我給大家吹點閒篇吧。”老溫說。於是,老溫又在課堂上給我們深情朗讀《巴爾扎克之死》《小鳥的朋友》等世界名著,甚至有一次,老溫不知從哪找到一本反映抗日戰爭侵華日軍罪行的影集,用了整整一堂課給我們講解。老溫在學校裡沒有什麼朋友,從他每天在學校裡獨來獨往的,大家都知道,但慢慢的我卻喜歡上了這門聽不懂也記不住的課。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我的成績不好也不壞,永遠在中間,考中專吃國家糧不可能,技校沒機會,高中就沒意思了,多讀三年,增加家裡負擔,最後還是出去打工,十五歲的我,真的好茫然。上學期快結束了,那天又是一個週末,白天上山砍柴的時候我不小心把唯一的一雙力士鞋弄破了,大腳趾露在了外邊,腳趾上還有一個口子,要返校了我才拎桶井水沖洗一下,抓幾粒鹽撒在傷口上,穿上淋著水的破膠鞋往學校跑。“小李同學”剛到學校門口就被一個聲音叫住了,抬頭一看,溫老師戴著紅袖套站在門口,原來是他值周。“老師,我沒有遲到啊?”我看看其他進校的同學,疑惑的看看老溫。他卻叮著我不斷往後縮的腳說:“不是這個,我找你有點事,現在跟我到宿舍一趟。”
我的作業交了,課上的內容我也記住了,上週沒交英語作業那是因為我沒錢買本子了,可這應該是英語老師或班主任該管的事,老溫,他要幹什麼。跟在老溫後邊走著,我很忐忑。老溫的宿舍是典型的單身漢的樣子,不足十平方的房間有床,有做飯的爐子,有書桌,最顯眼的是靠牆的一整個大書櫃,講真的,我活了十五年,就沒見過那麼多書,侷促的我站在書櫃前看著書目就不會動了。“站著幹什麼,坐下!”不知什麼時候,老溫手裡拿著一瓶白酒站在我對面。“老師,我不會喝酒”,其實我是喝過的,老溫莫名其妙找我喝酒我實在不明白。“坐下,把鞋子脫了”這是不容我解釋的命令,我坐在小板凳上,把脫下的破膠鞋悄悄踩在腳下,看著自己被冷水浸的發白的雙腳。“咬著牙,忍著點”老溫擰開瓶蓋,把白酒緩緩的往我腳上的傷口滴下來。“哦,疼,疼”我呲牙咧嘴的大喊。“老師這裡沒有藥,用白酒可以防止發炎,你忍著點”,在我眼含淚水的時候,老溫又手拿一雙回力鞋站在我的面前“這是我穿過的,破的地方已經補好了,換上吧,大冬天的穿溼鞋怎麼成。”一雙普普通通的白色回力鞋,洗的很乾淨,右腳上有一塊補丁,襪子,居然還有一雙白襪子,我突然想暈過去,夢中多少次沒有想到這是我人生的第一雙襪子。我心裡沒有了任何防線,穿上襪子和回力鞋,它可真暖和啊,我敢保證,我的腳這輩子都沒有這麼舒服過。
“談談吧,有什麼想法,我發現你人不笨,怎麼學習不大上心呢”老溫一如上課時的語氣。我還能說什麼,把家庭的情況,個人外出打工的想法,甚至對某個女孩子的感覺全部倒了出來,少年的心裡忽然很舒坦,平靜了很多。“你們還太小,很多東西你慢慢體會,不管怎麼難,但書是一定要讀的。或許你讀了高中也不一定考上大學,但學校裡的老師總沒有壞人,不會教你走歪路,一旦走入社會,這輩子就徹底毀了。……”後來看了大話西遊,我發覺,唐長老和某個人很像,想在想到,我卻笑不出來了。拿著老溫送我的一套《悲慘世界》走回宿舍,那晚我卻失眠了,都怪腳太暖了,我含著淚水想。最後一個學期,我忽然不喜歡打找朋友(撲克牌的一種)了,每天只會刷題,看書,週末安安靜靜的回家砍柴、做農活,感覺不到苦和累。後來,一切都在預料之中,考個高中重點班,考個負擔少點的學校,找個連衣服都不用準備的工作,一干就是二十五年。這麼多年由於工作和家庭的各種鬧心事,雖然參加了幾次同學會,看著這樣長,那樣總的同學,我都是找個角落坐下來,自己安安靜靜的喝一口,趁沒人注意的時候,悄悄離開,連走上前和各位老師握個手,敬口酒的勇氣都沒有。
再朝老溫離開的方向看了一陣,我眼睛又溼了,老溫一生沒什麼朋友,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全名,成家與否我也不知道,但他活的乾乾淨淨,坦蕩從容,他就是我們成長路上的一道光,一生照亮了多少人他已記不得了,但總有一個人還記得他。這麼多年自己活的這麼累,不正是在追隨他的腳步走嗎,我應該堅持下去才對。淡淡笑,淺淺愛,從容面對生活的一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