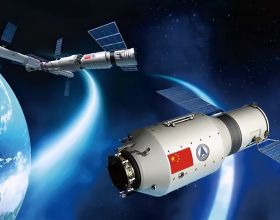採寫/錢昕瑀
編輯/計巍
1992年,長春大學特教學院中文系合影
盲人學生讀了大學後命運會發生改變嗎?
32年前,天津市殘聯聯合長春大學發動過一場“盲人中文班”的教育實驗——從全國各地的盲校中選出了17名成績拔尖的學生,為他們提供普通高中及大學教育課程,試圖以此彌合當時盲人學生畢業後大多隻能做按摩的落差,給予他們改變命運的可能性。
對於這些學生來說,選擇這場教育實驗意味著先要走出固有的盲人圈層,參與選拔考試,成為216萬分之一進入大學深造;接下來,他們還要離開大學校園,進入“叢林法則”支配下的社會,尋找自己的立足點。
這對任何一名參加實驗的盲生都是不小的挑戰,機會與風險並存。32年間,經歷了升學變故、學業困難、融合難題、就業瓶頸、社會壓力等現實問題後,他們命運的走向不盡相同,有人成了歌手、教師、政府幹部、企業員工、自由職業者,也有人重回按摩行業。
他們很難說清楚大學給自己帶來的影響究竟是什麼,但大多數人都提到,現在仍保持著每天閱讀的習慣——這源於大學時期對書籍的“著魔”。還有很多人說,大學生活讓自己的眼界更開闊,思考問題時更全面,與視健者相處起來也更融洽。
學生尹斐斐在回憶自己曾經的經歷時,這樣說:“記得小學時,老師經常提醒我們不要斜肩彎背,不要無意識地搖頭晃腦,這是很不好的‘盲態’……我把這視為自己必須避免的最大的‘盲態’。”他希望自己能夠更有自信,更好地融入自己之外的那個大世界中去。
這也正如這場教育實驗的發起者之一今年77歲鄭榮臣所說的那樣:“我所能做的就是為他們提供和普通人一樣的教育,參與社會生活,平等地去追求自己應該追求的東西。然後,看他們自己能夠走到哪一步。”
1989年,“中文預科班”合照
逃離按摩
1989年10月10日,天津殘疾人職業中專的開學典禮暨成立儀式上,14名從全國各盲校選拔出來的盲生第一次見面了。簡單打招呼後,尹斐斐發現班裡的很多人之前都認識——有5人參加過1988年全國盲人中學生智力競賽,還有2人作為省優秀盲童,參加過全國第一屆盲童夏令營。
他們坐在一起,聽著開學典禮上領導的致辭。那天,除了中國第一位盲人作家鄭榮臣作為校長髮表致辭外,到場的還有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副主席黃乃、天津市副市長陸煥生等人,規格陣勢頗大。令尹斐斐印象深刻的是,校長鄭榮臣提及中文預科班的培養目標:要讓盲孩子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融入普通社會,終極目標則是讓這群孩子離開按摩。這讓尹斐斐心頭一陣狂喜,他覺得他來對了。
對他而言,與其說是討厭按摩,不如說是討厭被動的生活。
8歲失明那年,尹斐斐總是不由自主地重複同一個動作——用力閉緊雙眼,兩手使勁捂在眼睛上,他想重新體會一下“黑的感覺”。但他感受不到,如同耳朵、臉部的面板那樣,他的眼睛只能感覺出冷熱、輕重。父親不忍心看他那麼無助,說,“待在家裡面算了,以後養起來就行了。”
尹斐斐彷彿能一眼洞穿自己的未來:去按摩,去賣唱或者去盲人福利工廠糊紙盒。可他還有渴望。他希望能找到一個抓手,至少讓自己不用那麼被動地待在既定軌跡裡。而這個抓手,就是教育。
在武漢盲校就讀小學、初中期間,尹斐斐成績穩居班級第一。他去北京參加過1985年全國第一屆盲童夏令營,獲評過“武漢市三好學生”稱號,還與視健者同臺競技,在“楚才杯”作文競賽中四次獲獎,在全國華羅庚數學競賽中獲三等獎。
令尹斐斐失望的是,1989年初中畢業時,針對盲人的高中教育仍缺失,全國沒有一所盲校開設文化高中——直到四年後,中國殘聯與教育部行文委託青島盲校才試辦全國第一個“盲人普通高中班”。當時的尹斐斐只能升入盲校的按摩中專,成為中專一年級的學生。
在後來這群被“盲人中文班”錄取的學生中,大多數都是像尹這樣綜合成績優異、希望用接受高等教育來改變自己命運的盲生。也有一些人在初中階段就對中文展露天賦,出於對文學的愛好進入了班級。
當代盲人歌手及作家周雲蓬也是後來“盲人中文班”的學生。在瀋陽鐵西區的工人大院裡,鄰居是個愛文學的年輕小夥,經常為他讀尼采、叔本華、斯賓諾莎等現代哲學家的著作。在瀋陽盲校讀初二時,周雲蓬就在《盲人月刊》上發表多首詩歌。1987年,得知長春大學開辦特殊教育學院,向殘障人士開放音樂專業後,他坐火車跑去天津,找到中國第一位盲人作家鄭榮臣,問詢他是否有可能建議成立長春大學中文專業。此前,周雲蓬聽過鄭榮臣的講座,覺得他對於盲人教育很有自己的觀點,而且在政治、文藝界都有一定影響力。
對於按摩,周雲蓬實在提不起興趣。照他的話講,“有時候給人按了半天,人覺得像沒按一樣。”當可以逃離按摩時,這些渴望改變命運的盲生也變得“孤注一擲”。
1989年9月12日,是令尹斐斐難忘的一天。按摩班的中醫基礎課上,班主任老師帶著一份天津寄來的公函,告訴全班:天津殘聯和天津職業高中在天津聯合辦班,學制兩年,是預科性質,教授高中課業,畢業後成績考核合格,擇優可以去長春大學讀中文三年。那天下課後,尹斐斐沒有和家裡人商量,就衝去找班主任報了名。
同月,還有其他盲生陸續收到天津職業高中的招生簡章,或見到親自來校面試的校領導。這些盲生中,有已進入福利工廠工作的初中應屆畢業生,也有人在按摩中專已讀至二年級。面對“天上掉下的餡餅”,學校裡的同學及老師或多或少都有些懷疑:“這個中文預科班靠譜嗎?真的有可能升入大學嗎?”“讀中文出來將來能做什麼?之後還不是回來做按摩?”
周雲蓬當時已是按摩中專二年級的學生,作為班長的他成績優異,還有一年就可以畢業。知道預科班訊息後,家長以太冒風險為由強烈反對,但他還是堅持從按摩中專退學,“因為我一心渴望讀中文專業,哪怕承擔風險,我也願意。”
1989年的秋季,14名盲生收到預科班的錄取通知書,從北京、天津、上海、武漢、瀋陽、大連、南昌等盲校,先後抵津。其後,又有3名盲生經私下打聽,拿著簡歷向校方自薦。最終,17名學生進入了這個“中文預科班”。
新班級
這個班級的建立,與一群人以及幾個約定有關。
1988年的夏天,長春大學校長王野平和特殊教育學院院長甘柏林找上盲人鄭榮臣。鄭榮臣當時是天津市殘聯宣教部部長,也是兩人的共同好友。1987年,長春大學特教學院建立後,兩人發現:盲人高中教育的缺失,讓特教學院特招模式下的生源質量很難得到保障——招生進行到第二年,學生質量便出現明顯滑坡。所以,他們找到鄭榮臣表明意圖:希望能協助辦起一個大學預科班,為長春大學輸入穩定的優質生源。
這一提議正中鄭榮臣的下懷。作為一名中文系畢業生,鄭榮臣唯一的建議是:長春大學開設的第一屆預科的直升專業為中文。三人一拍即合,約定成立盲人預科班,學制兩年,學生學成後送往長春大學中文系深造。
經批准後,他們創辦了天津市殘疾人職業中專,下設鋼琴調律班、家電維修班以及中文預科班。
“其實,這更像是一場試驗。”如今77歲的鄭榮臣談起創立這個班級時坦言,“在這些孩子性格各方面還沒有完全成型的時候,我所能做的就是為他們提供和普通人一樣的教育,參與社會生活,平等地去追求自己應該追求的東西。然後,看他們自己能夠走到哪一步。”
來到中文預科班後,盲生何川發現預科班的配置幾乎和普通高中一模一樣。兩年時間裡,他和同學每天在五十平米的教室內,從早到晚平均要上11節課,一週課時量達67節。任課教師都來自天津市重點中學,對他們要求嚴格。數學課上,何川和同學要用特製的盲人作圖用具畫幾何圖形,他也因此第一次知道了蝴蝶長啥樣、橋長啥樣;語文課上,他們被教授漢字的用法,第一次知道了盲文“六個點”之外的世界;地理課上,他們第一次透過觸控中國測繪局贈來的觸控地圖,摸到了山川河流……
他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和視健者之間的“接近”。很多年以後,盲生周雲蓬仍會做關於當時數學考試的噩夢:“快考試結束了,數學題還沒答完。”
這些課堂教學模式及內容,與鄭榮臣的教育理念有很大關係。他自幼曉曲藝,善學習。盲校初中以班級第一的成績畢業後不久,他被安排到天津社會福利第二紙品廠,給盲人工人做夜校教員,與此同時與視健者一起進修高中課程。在自己的爭取下,1979年鄭榮臣進入天津電視廣播大學學習中文專業。在那裡,他抄了700多萬字盲文筆記,最終從2000多名視健者中以綜合成績第一的成績畢業,並在三年後寫出盲人愛情題材長篇小說《琵琶琴》,成為當時社會宣揚的“正面榜樣”。高等教育帶給他的不僅是專業知識的積累,更是關於盲人教育的思考:作為盲人,如何才能融入視健者的世界中。
1979至1982年,鄭榮臣在大學裡抄的盲文教材,共700多萬字
有次和盲人朋友的交流,給鄭榮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對方姓“諸葛”,四十多歲。半開玩笑地,鄭榮臣問:“你知道你的姓是哪兩個字嗎?”那個盲人回答:“這還不簡單,不就是姓朱的’朱’,皮革的‘革’嗎?”
這讓鄭榮臣哭笑不得,又深有感觸。盲人從小就在盲校學習,學的都是盲文,不識漢字。僅僅是文字上的差異,已經與視健者的世界謬以千里。“盲人的資訊無障礙絕對不單純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系統工程。”他說,“盲校這類特殊教育不是不需要,而是要越早結束越好。”
鄭榮臣一直有個想法,讓盲人接受高等教育,和視健者一樣的教育,看看他們是否能夠真正融入社會,走出自己的道路。而這,也是他聽到王野平談及需要一個預科班時,立刻答應並付諸實踐的原因。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伴隨中文預科班的成立,他的夢想和盲孩子的夢想在同一時空裡實現了。
馬立榮和劉麗
17進12
最初,很多人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進了中文預科班。有人說班裡最後一定會淘汰幾個人,因為招生簡章上說了會“擇優錄取”。也有人表示自己是鄭榮臣校長親自面試招生,被承諾過一定會有去處,如果不能上長春大學,也能去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繼續唸書。但大半年後,懷疑的聲音漸漸減弱,他們都發了瘋似地學習。
預科班要求兩年內學完三年高中課程,無論從知識量還是學習難度上,對盲生都是很大的挑戰。學生劉麗畢業於天津盲校,家在天津。第一年她還和大家一起住在六人間的宿舍裡,到了第二年,她扛不住大家制造的競爭壓力,選擇走讀。在她的印象裡,凌晨一點到三點是寢室最熱鬧的時候。凌晨一點多,有室友熬夜抄筆記,肚子餓了,就開始用電熱杯煮泡麵;凌晨兩點多,有室友從教室學習完回寢休息;凌晨三點左右,又有室友定了鬧鐘早起,從床上爬起來背筆記。
何川是後來報到的三位盲生之一。為了能補上前面落下的地理和歷史課程,他和同樣後到的同桌馬立榮兩人互相鼓勵,每天用盲文抄學科筆記抄到凌晨一兩點,然後再複習功課。有時候到凌晨三點,他實在困得受不了回去休息了,馬立榮仍在教室裡繼續抄寫、背誦。“那時候不用老師督促,幾乎沒有人在12點之前睡覺。”何川說,“有時候你熬不住早睡了,第二天還會自責,覺得對不起。”
變故發生在預科二年級寒假後的春季。
1991年3月,長春大學的招生簡章對外公佈。預科班學生黃強收到了原南昌盲校同學的一封信,同學說自己打算報考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下的按摩專業,還提了一句:“我在特殊教育學院下沒找到中文專業。”
訊息傳遍整個班級,所有人警惕起來。學生何川聯想到前幾天的開學摸底考試,也察覺到一些端倪。原來任課老師非常嚴厲,考試結束絕不多給一分鐘,直接搶過試卷收上去。可是那次考試時間到了以後,她竟和何川說:“沒事,沒寫完是吧?你慢慢寫,寫完給我就行了。”
尹斐斐是當時的學生會副主席——由於他初中成績足夠出彩,進入預科班後,被老師指定為學生會副主席。在班中小道訊息四起的時候,他跑去校長辦公室向鄭榮臣詢問情況。得到的回覆是:“不要急,你們回去等一等。”
學習的弦一下子鬆了,而且好像失去了再次拉緊的動力。班裡有同學開始鬧罷課,說要要挾學校,或要求給長春大學施壓。面對情緒激動的同學,班長周雲蓬主張保守一點,他向同學分析:“咱們該上課就上課,你不上課對你也是損失。凡事都應該知道妥協,你太過於激烈維權,你到時候絃斷了更沒法談判了。”
同月,有訊息稱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鄧樸方將來天津視察。周雲蓬當時就想到了一個主意:寫聯名信,然後交給鄧樸方。尹斐斐邏輯性強,負責寫信的初稿;周雲蓬文筆好,負責在初稿基礎上潤色、定稿;許立勇等男生個子大,膽子也大,負責送信。於是,在鄧樸方來到天津殘聯時,一封學生髮起的聯名信越級送到了他手中。
對於學生進行的活動以及私底下的聲音,鄭榮臣都瞭解但也無能無力。其實,很少有學生了解,早在1990年底王野平校長退休時,這場變故就開始發生了。鄭榮臣當時就跑去長春找到甘柏林商量解決辦法。但由於當年三人沒有定下紙面協議,王野平退休後對於特殊教育學院的招生也沒有了發言權。長春大學繼任校長上任後,並不接受這一協定。鄭榮臣很著急,但也沒有發言權。當得知鄧樸方將要在天津召開調研會後,鄭榮臣把班長周雲蓬叫來:“你可以代表中文預科班,把你們的情況反映上去。”
寫聯名信再加上週雲蓬在座談會上的反饋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很快解決了這件事。但當時大學已經實行國家計劃招生,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一共面向全國招收66個學生。在多方協商下,最終放出12個名額給這個“中文預科班”。
就因為這樣,17名學生參加了一場長春大學自主命題的升學考試。最終,12名學生考進長春大學特教學院中文系就讀。
諸多原因的影響下,這個“中文預科班”和長春大學特教學院中文系都只存在了一屆。直到2004年,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率先在國內開展融合教育,為視障大學生開設特殊教育、漢語言文學、英語3個輔修專業後,才有盲生取得大學中文專業輔修學位證書。
1992年,長春大學特教學院中文系在雪裡的合影
“八仙過海”
大學,給他們帶來的體驗豐富又複雜。課堂上,他們仍是認真、聰慧的尖子生。課堂外,在一個更加開放的環境中,他們人生的走向開始發生變化。
何川一進入大學,感覺周邊的一切新鮮而充滿朝氣。學校裡有外語學院、師範學院、文學院、旅遊學院……周圍再也不僅是和他一樣有視力障礙的同學。接觸的老師、學生很多都是視健者,男生愛打籃球,女生愛讀書和做針線活。不過,作為特殊教育學院的學生,他並沒有感到有競爭劣勢。“我們會樂器、會寫詩、會畫畫,在學校反倒更受歡迎。”他說,“用現在的話說,我們那時候都是文青。”
在大學裡,何川和周雲蓬兩人是好朋友。兩人常常一同參加活動。周雲蓬愛寫詩,也愛舉辦詩歌交流活動,他們曾一同辦過校園文學刊物《失眠者》,面向全校師生收集詩歌。對文學以及詩歌的共同喜好讓他們認識了很多朋友。
大學裡自由、開放、平等的環境,也激發了他們更多的“慾望”,比如說,著了魔似地讀書和獲得更多的知識。“可能我們盲人還是有一種潛意識的本能,要靠書來救贖自己。”周雲蓬說。
很多年以後,尹斐斐仍記得寒假送班裡同學沈志剛去火車站時的情形:沈志剛把外套系在腰間,揹著一紙箱用尼龍繩紮好的書,行走在擁擠的人潮中。外套被人流擠掉了,他也沒來得及管,雙手護著身後的書一直上了火車。
他們看不見,便面臨一個現實問題:無法自己讀書。特教學院中文系的課程大綱完全按照普通中文師範班制定,每門課都需要閱讀大量書籍。
陳立萍是長春大學文學院的教師,當時負責給“盲人中文班”上《當代文學》和《古代漢語》兩門課。在她的印象裡,這些盲生每個人都像海綿一樣。“如飢似渴都不能形容他們當時的勁頭,從來不會嫌我講得多。”她說,“他們總讓我再多講點社會上的事。我說你們要聽哪個方面?他們說無所謂,哪個方面都行。”
他們抓住每個機會向課堂和外界獲取知識。但如何解決讀書的問題,還是難住了幾乎每個人。“到大學以後就靠你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自己找門路學習。”如今回想這段大學生活,尹斐斐感慨,“(找門路)不行,就只能沒有機會了。”
大學時期的劉麗愛好外語,經常沒課就跑去外語學院旁聽。週末,外院的同學會帶著她乘十幾站公交,來到紅旗街上的紅旗書店,挑選中外文學經典。久而久之,他們除了給劉麗讀書外,還會帶她去見他們的外教、參加他們的舞會。
而何川和周雲蓬都會吉他,在預科班時他們抽空就會在宿舍練習。進入大學沒辦法讀書,周雲蓬就想到了一個辦法:在沒課的時候,透過教人彈吉他來和視健者進行交換,讓他們幫忙讀書,教一小時吉他,對方讀一小時書。後來證明,這是個成功的方法。周雲蓬和何川教彈當時的流行歌曲,換來許多人排隊為他們讀書,從莎士比亞、博爾赫斯、卡夫卡、托爾斯泰、米蘭·昆德拉,一直到穆旦、張愛玲、錢鍾書。班裡其他男生也開始效仿他們的模式,或藉助他們找來的朗讀資源,解決了讀書難問題。
一些差異也因而逐漸產生。
在17進12的考試中,尹斐斐雖然以全班第一的成績進入了“盲人中文班”,但在周雲蓬還沒開始“吉他換朗讀”的方式時,他每天的讀書渠道非常有限:聽收音機,聽講座,或者請班裡弱視的同學幫忙讀。
他記得大一暑假期間,除了周雲蓬和他,其他人都回了家。周雲蓬為了讀到書,每天乘車到長春人民廣場給人按摩賺零花錢,然後花錢僱人讀書。而當時的他,除了在周雲蓬找到朗讀人之後和他一起花錢讀書,幾乎一點辦法也沒有。
也是從那時起,尹斐斐開始給自己找退路。他打聽到一個大他兩屆的音樂專業盲生才能突出,卻沒有被分配到工作,最後回去幹了按摩。他擔憂起未來自己的出路,碰到不那麼感興趣的專業課,就逃課去特教學院的按摩教室,學習一些按摩手法。
時隔近三十年,當我和尹斐斐聊起他的大學歲月,問他:大學期間,有沒有覺得自己融入了更廣闊的校園生活中?他幾乎毫不猶豫地給出答案:“沒有,我沒有途徑。因為他們會的我都不會。我的成績可以,但我的能力遠不如周雲蓬他們。”
大學裡時期的周雲蓬
進還是退?
“陳立萍 梁偉 顧煥戈 尹斐斐……”在發行於2004年的個人首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的同名曲裡,歌手周雲蓬唸了一連串和“盲人中文班”相關的人名。那是他在非典期間感受到地鐵車廂空空蕩蕩的情景後,腦中閃過的名字。那年,距離他大學畢業正好十年。
1994年,國家試點並軌制改革,大學不再“免學費”和“包分配”。這意味著,這12個即將畢業的盲生需要自謀出路。由於每個地區的執行程度不盡相同,“盲人中文班”中,有8人還是被分配到了鄉鎮殘聯或戶籍所在地的盲校工作,而周雲蓬、何川、尹斐斐、馬立榮4人則需要自己想辦法。
在畢業多年後的隨筆中,尹斐斐曾寫道:“在那些詩一般的、充滿了無數斑斕色彩夢想的歲月裡,我曾不止一次私下裡嘀咕,沒有了眼睛,不見得就不行嘛!(但)巨大的反差,彷彿毒蛇咬齧著我的心。學校,是個相對封閉,相對純潔的環境,走上社會,對於一個盲人來說,更像一葉扁舟駛入了波濤洶湧的大海。”
何川向盲文印刷廠毛遂自薦,從普通校對工一直做到現在的中國盲人協會副主席,主持中國盲人資訊無障礙、盲人閱讀推廣、盲人文化研究所等工作。馬立榮在回家幫哥嫂帶了五年孩子後,孤身一人來到北京打拼,在做按摩工期間尋求到留學印度的機遇,現在是“黑暗中對話”企業工作坊的教練,也是“七色花盲童早期教育”專案的創始人。
大學畢業後,尹斐斐選擇回到以前的母校——武漢盲校按摩中專,報名參加了四個月的按摩短訓班。
命運彷彿和尹斐斐開了一個玩笑,他回到了當初他最想逃離的職業上。但那時的他也更明白:盲人想要娶妻生子、養家餬口,過上和普通人一樣的生活,就只能比普通人做得更好。南下廣東,他做按摩、買房、開店、結婚、生子。如今的他,在廣州市白雲區經營著一家按摩店,每天從早上十點一直到凌晨。
如今的周雲蓬是著名歌手兼作家,同時也是長春大學的客座教授,生活在雲南大理。“相比於在老家待著渾渾噩噩過一輩子,我更願意去外面闖一闖,那樣的人生才更精彩。”他說。
畢業後,他揹著吉他成為“北漂”一族,來到北京成為街邊賣唱歌手。他想象自己就如古希臘盲詩人荷馬彈唱《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那樣,坐在北京大學外彈唱著當時的流行歌曲。當時他最期待的事是回家數錢,像財務總監一樣的女房東每次在他回來後都非常熱情:“哎呦,小周,回來了?來,看看今天掙多少錢?我幫你數。”有一回,他們還在一堆硬幣中發現了一張不認識的紙幣。詢問周邊的人後,才知道那是一張美元,“one dollar!”
周雲蓬逐漸適應並喜歡上這種生活,不可控,但更鄉野化、更自然、更接地氣。他最喜歡的一本書是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裡面的“媚俗”理論讓他印象深刻。“媚俗就比方說討好群眾或者討好觀眾。其實我自己是視障人,也經常會有那種心理:你要感動自己,感動自己可能就是為了感動別人。”他說,“所以,我會常常讓自己自警,不要總自我感動。”
今年77歲的鄭榮臣
更充實、更堅定的人
2014年,國家教育部首次印製盲文高考試卷,被稱為“盲人高考元年”。在此背景下,盲人除了透過大學“單考單招”報考針灸推拿等特殊教育專業外,也可以透過申請盲文試卷參加普通高考進入大學,和視健生一同就讀大學開設的各專業。那之後,每年都有數量不等的盲人申請盲文試卷:2015年8份,2016年5份,2017年7份,2018年2份,2019年10份,2020年5份,2021年11份。
對於視障考生而言,學習非特殊教育專業後,最大的顧慮仍是畢業後的就業問題。反觀“盲人中文班”畢業27年後的的現狀,這場教育實驗或許能呈現一些答案。
這個在中國盲人教育歷史上只存留一屆的“盲人中文班”中的12個學生,現在分佈在政治、教育、文藝、公益、按摩等領域。學生黃強現在是南昌盲校的副校長,劉麗成了上過電視的金牌教師,周雲蓬在成名後與何川聯手創辦起“全國盲童夏令營”,馬立榮投入了大量精力在盲童早期教育上……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動著盲人教育的發展。大學中文專業帶來的影響並不能在多數人的職業中得到直接的反饋,卻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人生目標、處事方式以及生活態度。
大學對他們最大的改變,很多人都談到一點:眼界更開闊了,思考問題的方式也更全面,這也使得他們在工作、生活中和視健者相處得更融洽。許多人已經組建了自己的家庭,找到的另一半都是視健者。平日裡,他們在班級微信群裡交流家庭動態、社會時事,有時候聊聊家中高三孩子的備考情況,有時討論起使用導盲犬遇到的問題,或分享最近讀過的書。
班中大多數人現在仍保持著每天閱讀的習慣。科技的發展,讓他們過去的讀書難題不再成為問題。1995年以後,隨著電腦和讀屏軟體開始進入中國市場,何川把從中關村買來幾張書籍盜版光碟放進電腦以後,一下子可以聽到近千本圖書。他重溫以前讀過的《懺悔錄》、《約翰·克里斯朵夫》等名著,也聽起日漫等以前不好意思讓他人讀的“閒書”。
每天零點停止營業後,尹斐斐會來到客廳,把電腦音量調至最低,聽上三到四個小時書。他喜歡看歷史、科學類的書籍。給客人按摩時,有時也會根據客人的喜好和對方聊聊天。從過去的豫東戰役到最近的阿富汗局勢,尹斐斐都能接上客人的話。有時客人會對他知道這麼多感到很新奇,這會讓他稍稍有些竊喜。“我覺得按照當年我的閱讀量而言,我應該達不到大專中文系畢業水準。”尹斐斐說,“但是,幾十年過去了,我也讀了很多書,包括之前沒讀的推薦書目,我覺得我已經達到了。”
當重新談起盲人按摩這件事時,他們也會持和曾經不同的態度。在何川看來,他自己最後走上了不錯的事業道路,但其實一路走來戰戰兢兢。“離開主流之後,你看似走上了一條新鮮的道路,但不確定的因素很多。有時候我反倒覺得按摩更讓人安心,一門技術在手,萬事不求人。”何川說。
揹著吉他走遍中國諸多省市後,周雲蓬也重新檢視當年被自己排斥的職業。“盲人按摩至少生活穩定,不用四處為家。”他說,“每個工作最終都會看透,都會失去新鮮性。按摩,它還是實際解決了我們群體大多數人的就業問題。”
如今77歲的鄭榮臣正在寫他的第三部小說《神算居傳奇》,一個關於盲人算命師的故事。當他回望這場教育實驗,他覺得談不上成功與失敗。實驗結束了,起碼說明一點:盲人完全有能力透過高中教育參加高考,正式接受大學教育。至於之後的路,運氣確實佔一定因素。他也透露,當初預科班畢業後,他曾動用私交請部分盲校接收了幾個盲孩子當老師。
“你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那就絕不可能那樣一帆風順,這就需要你自己堅定不移地走下去。”鄭榮臣說,“作為一段歷史,對更多的人、教育人士來說,這可能只不過是一朵小小的漣漪。但在這些孩子們心裡,卻留下無數美好的記憶,教會他們成為更充實、更堅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