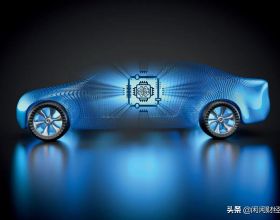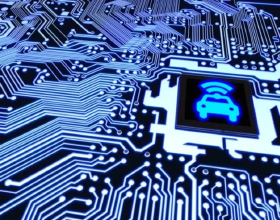發現紫米粒葉尖的秋天,是一個香暖的過程。
那天清晨,我在陽臺洗刷,窗外有爭吵聲不絕於耳,探身向窗下望。東窗下,一男子停電動車,一樓的女子不讓放。男子納悶,車子放在牆角空地,不礙事呀。女子吼,地裡種了野菜。女子一聲接著一聲叫,白種了白種了壓壞了,男子在女子驚叫聲中小心翼翼地把車子推出去,鬆軟的泥土碾出一道車轍,女子疼地直跺腳。我隔窗注意到,女子的窗下像個植物園。明朗的晨光中,大片的蛤蟆草,盈盈碧翠;紫葉天葵,葉質油光,遠觀,紫光爍爍;馬蘭菊花,密集而開,粉白一片,如小碎花棉布。有人路過馬蘭菊花叢,醉於滿園生機,駐足,詢問種這些野草的用途。女子弓腰輕輕撫平車痕,不刻意不做作不迎合,高聲大語,娓娓道來。蛤蟆草,泡水喝清熱解毒,那個不知道叫啥子,預防糖尿病,馬蘭是當菜吃的,我才種的茼蒿被車碾了……
我看著,聽著,很舒服,很享受。女子素面朝天,衣著樸素得體,甚至透出老土氣,可她真實自然,我對美的定義不是時尚,是自然是真實。她也是詩意的,陽光下,那片野草,熠熠生輝,芳菲鮮美,是她種下的詩歌。
女子掐了把翠嫩的蛤蟆草葉,攥著回家,我豔羨呀,她是採了捧春天回家,再心靈手巧地弄出美味來,平素的日子有了光和色。
女子的身影消失,我收目,無意間瞥到那盆紫米粒,驚訝地發現,前幾天茂如菜,神似太陽花。今早再看,葉距縮短,青莖變紫,葉愈加肥嘟,葉尖染了迷人的紅紫。那柔媚的紫,讓我想起兒時的秋日,一群田間拾秋(拾收割後的稻子,大豆,花生,紅薯)的夥伴,笑聲迴盪在秋割後的曠野,秋風颯颯,全不知皴了腮,洗臉時微痛,照鏡子兩腮紅撲撲,像樹梢的紅蘋果,那種對秋天味道的知覺,讓人冷不丁想到秋天綺麗的色彩,帶著疼,藏於心間,成了懷戀。再詩意地想起,昨夜秋風起,水岸蓼花紅,醉清秋。或者,秋風至,霜染柿子紅,露叢蘆花白,皆入詩入畫來。那種自然而野性的秋味,是我內心無力表達的美,隨著時光的沉澱愈來愈讓人懷想和迷戀。
紫米粒,葉尖小小的稚嫩的紫,多像兒時秋風皴的腮紅,以及晨起見到老屋後,柿子樹忽至橘紅,滿池塘蘆花飛白,自然而然地塗抹秋天的色彩,小聲地驚奇地告知我:秋,來了。
紫米粒精小玲瓏,智慧聰敏,急早感知秋涼,停止莽長,養精蓄銳,收斂,沉澱,準備好,向著季節深處。
紫米粒,是近年來流行養殖的多肉之一,花葉同賞。僅聽其名則很美,又名米粒花、 紫米飯、紫珍珠、流星,為馬齒莧科馬齒莧屬多肉植物,原產南美玻利維亞,阿根廷,巴西等地。
紫米粒的到來,像撿來的孩子,頗意外,亦溫暖。
同事琴愛養花,因家裡養花條件有限制,她常把花端到公司,放在得風得光的後門,我上下班去後門看花成了習慣。那日下夜班後,琴給花噴水,我在旁邊看她的花,這時同事娟過來,塞給琴一沓鈔票。她立刻喜上眉梢,咧嘴一笑,把錢裝進口袋,繼續低眉安然澆花,又遺憾地嘟囔一句,以後沒有了。原來是她和娟週末去做臨時工,結算錢,而那個公司被其它的同行收買,不需臨時工。
我以前對同事週末出去幹臨時工,有點不理解,以為她們不缺錢,如此死幹,不會享受生活。當有一天聽她們興奮地聊起在郵政打包快遞,無吃飯和喝水時間,一邊幹活一邊嘴裡含著餅乾嚼,水是上班前準備充足放在身邊,有時喉嚨幹得冒煙來不及喝一口。她們講著笑著,把苦錢甚至被剝削壓詐的親歷,敘述地很輕鬆。生活的哀怨愁苦歷經之後,變得不值得一提,過後敘說時像個玩笑。這不是麻木,是成熟,是樂觀,是積極向上。她們無興趣愛好,出力賺錢則是快樂之事,如同寫文章的人,一天不發表文章會失眠,她們一天不存錢會無安全感。我開始欣賞她們吃苦耐勞的生活態度,腰包的充盈,使她們有底氣,自信和愉悅。
琴接到鈔票時的和顏悅色,像風吹紅的果實,顯露出收穫的富有與甜蜜,那樣子把我感染地無比溫暖,嘆生活之不易之充實之歡樂。
晨曦斜照,她悠閒地澆著花草,討論著再到哪裡尋臨時工,噴壺的水霧,銀光閃閃,灑落到花草葉上,水珠晶亮欲滾,花草清新婉約,惹人想抱一盆回家。
這樣的情景閒適,踏實,人生累著,苦著,也樂著,因人間有草木,囊中無羞澀。
她每澆畢花草,再泰然自若地看會花,看到不喜的花草,或拔了送人,或薅了扔掉,再買心怡的,打臨時工的外快就是留這麼奢侈的。
她瞅著一盆徒長的紫米粒,亂糟糟地,似草,端起來往牆邊的灌木叢倒了。
當我發現時,乾燥的泥土,露出幾莖枝葉,蔫了,卻倔強地開著小花,頗妖的胭脂紅。
我扒開泥土,掐兩莖裝進上衣口袋。過了幾日,洗衣服清理口袋,發現了兩截癟軟的草莖,似曬蔫的馬齒莧,肉質,隨意地插入長蘆蘭的盆中。我只是為了履行自己對植物予以生存的義務,沒指望能活下來,或活下來不一定錦繡前程。
僅幾日,蔫蔫的紫米粒,擠在高挑的蘆蘭枝下,鮮活了,精神了。似乎是速長植物,幾天功夫,爆芽,徒竄,極速開花,純粹的胭脂紅,貌似太陽花,花朵比其小巧些,花開時間亦長些。紫米粒夏天的模樣與氣質,同太陽花極難辨清,極具草的野蠻,毫無多肉的可愛之氣,我有幾回想拔扔了。而紫米粒心態平衡,根本不在乎我對它的態度,居然隨即開花,隨即結籽,隨即生娃。老株如開花的小樹苗,幼苗而如亮澤針鼻,而如翡翠耳釘,密叢集居,於瘦高的蘆蘭同居一缽,別有一番趣味。
待到實在擠不了,重新移栽一盆。快速服盆,爆盆,開始野草的生涯。花開至霜降,葉漸紫,小如米粒,肉透,晶亮,似紅寶石,不斷爆崽,一碰小枝芽便嘩嘩掉,似米粒兒從指尖灑落,力量而深情,沾土即活,再次葳蕤,擠不下了。
有些愁呀,捨不得扔,且芽極小,有玉米粒大,需用筷子夾一粒粒栽種,費事和耗時。
落雨的天,我隔窗望女子的植物園,呀,素花毯子樣的馬蘭菊,遭到割除,一朵花不落下。木蘭的枯葉,闊大,噙著雨,落到收割後的馬蘭菊畦,空蕩,淒涼。我最愛的秋花——馬蘭菊,從我的窗下消失,疼惜時,也有異樣的情素撼心,不怪女子不雅興,她比我懂草木性情,忍疼割愛,助馬蘭菊儲存實力,來年愈風華。
由此,我想起頭條上看到的影片。一位漂亮淳樸的鄉村女子,音質優美,介紹對待徒長的紫米粒,像割韭菜,於根部完全剪了,再用菜刀,剁豬菜般,切碎,撒入泥土。
於是,霜降次日,我找回童年“剁豬菜”之感,把那些剁碎的小多肉,仙女散花般,撒入柔軟的泥土。它們紫溜溜的小身軀躺在芬芳的泥土間,像繽紛的糖果,泛著甜美的紫光,開始生命成長的美妙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