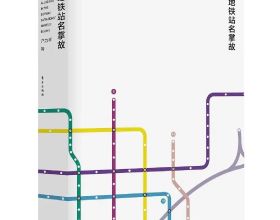王力平的《水滸例話》總共有65篇文章,題目都是取自《水滸傳》裡的句子。這些句子在《水滸傳》裡也許不顯山顯水,但被個別地拎出來,立刻有了不同凡響的感覺。
比如“姓魯,諱個達字”,僅六個字,作者說:“我更願意把這句自我介紹看作是對魯智深人物性格的白描。”他從人們對魯提轄的敬重說到“名諱文化”,說到魯達的知其一不知其二,懶得去弄明白,然後說,“話雖錯了,卻錯得有幾分可愛。若是中規中矩地說一句‘姓魯,名達’,反倒覺得寡淡無味,沒啥意趣了。”作者意猶未盡,又說出了四層意思來:若以第三人稱視角描繪這種微妙的人物心理幾乎是不可能的;中國古典文學總是藉助人物語言、行為以白描手法刻畫人物心理;施耐庵以一言當十言、百言,是憑藉對“這一個”的熟悉,為人物代言;為人物立心,有心之言,才是有藝術價值的語言。
作者顯然是借用《水滸傳》,談自己體味的寫作技法。《灑家去打死了那廝》談人物性格的塑造離不開特定的人物關係和環境,《坐了兩個時辰》談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統一性,《灑家特地要消遣你》是小說情節的曲折性和趣味性,《三拳真個打死了他》是談文學語言的音樂性……如此一篇又一篇,幾乎篇篇給人新鮮感,如淘不完的泉水。自然也由於《水滸傳》裡可說的句子太多了,隨便一首歌謠,都可在人物之間形成別有意味的關係,引出“實處落筆,虛處傳情,虛實相生”的分析來。
說是借用,細細體味,又覺得文章更多地屬有感而發。借用是作為局外人而言的,有感而發則是身居其中,與小說幾乎是同呼吸共悲喜了。文章的語言看似理性十足,但字裡行間分明透出感性的氣息。
比如《端的使得好》一篇裡:“從林沖大聲喝彩時的神采飛揚,到‘先自手軟了’的忍氣吞聲,之間是一個巨大的跌宕,也是林沖性格中的兩個不同側面。小說以林沖神采飛揚的性格側面,承接魯智深如長風巨浪、粗獷不羈的故事;以林沖忍氣吞聲的性格側面,開始他自己如陰雲低鎖、沉悶壓抑的情節,接合部的銜接過渡如水到渠成,了無痕跡。不禁要為作者高超的藝術手法叫一聲:端的使得好!”這當然是在由衷地為施耐庵的藝術手法叫好,但誰能說沒含了對小說人物情不自禁的愛惜呢。
數了數,涉及林沖、魯智深的篇章,竟有20篇之多。我想,與其說是施耐庵把這兩個人物寫得好,倒不如說是王力平的情感傾斜。相信他在閱讀和評價這兩個人物的時候,並未意識到篇幅的多少,怕是隻剩了滿眼的金句和人物的音容笑貌。
激情澎湃之餘,王力平也提到:“就人物塑造而言,《水滸傳》的人物塑造還基本屬於英國作家福斯特所說的‘扁平人物’。但顯然,施耐庵已經窺見了人物性格豐富性的魅力。”這一評價頗合我意,多年不讀《水滸傳》了,除了“扁平人物”,還由於對它寫人物心理的不滿足。
我對《水滸傳》也曾愛不釋手,對它寫人物的細節尤其難忘,後來,我被西方小說的心理描寫深深吸引,那確是一個更加微妙、深邃的世界。就在我以為《水滸傳》已被我徹底遺忘時,一本《水滸例話》重新開啟了我年輕時的閱讀記憶。我意識到,《水滸傳》對我寫作的影響一直都在,比如對人物、細節的看重,誰能說清這看重到底是來自東方還是西方?
《水滸傳》是古典的,對它的評點卻可以是現代的。在我看來,《水滸例話》的新鮮好讀,正因其現代視角。比如《把這件事不記心了》一篇,談到了林沖的“遺忘”,說林沖已有太多割捨不掉的眷戀和利益,所以幾日尋不到仇敵就把這事“放慢了”“不記心了”。“心理學研究表明,當受到某種情緒或特定動機的壓抑時,更容易出現‘遺忘’。林沖只能遺忘。”這種遺忘是什麼?是潛意識裡息事寧人的生存態度啊。而潛意識,正是現當代作家和評論家才會自覺關注的。《水滸例話》中多次提到“扁平人物”“敘事視角”“心理描寫”“人物關係”“人物性格的多面性”等,這些都是現當代作家熟知的詞彙,重要的是,在此,它們都指向了具體的句子或情節。就這樣,古典和現代有趣地聯絡在了一起。
(作者:何玉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