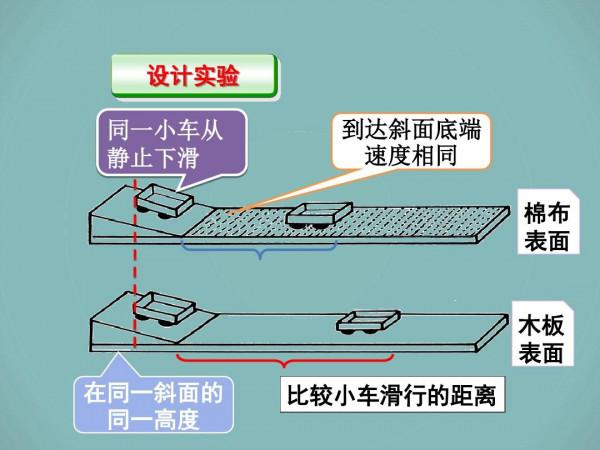1945年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曾與著名的民主主義教育家黃炎培先生有過一段關於中國歷史週期律的對話。當時黃老先生說:“我生六十多年間耳聞的不說,但說親眼見到的真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其實只要我們仔細分析就不難發現幾乎所有中國王朝在滅亡時幾乎會呈現出同樣的特點:官吏貪腐、財政紊亂、軍備空虛、權臣亂政、農民起義、外族入侵......這些基本構成了中國王朝滅亡的全部原因。
中國歷史從某種意義上就是在治亂興衰中不斷迴圈輪迴:秦王朝締造了大一統的中華帝國,然而卻落得一個二世而亡的下場;之後兩漢維持了長時間的統一安定局面,為華夏文明的後續發展奠定了基礎;黃巾起義使東漢王朝名存實亡,一時間天下群雄並起,幾番交鋒下來形成了魏、蜀、吳三足鼎立的格局;曹魏、蜀漢、東吳三方最終誰也沒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最終由司馬家開創的晉王朝完成了統一,然而僅僅三十多年後統一的西晉王朝就亡於五胡之手,中國歷史進入十六國、南北朝混戰的時期。
終結南北朝亂世的隋王朝和當初的秦王朝一樣有著諸多開創之功,然而隋朝在壽命上也和秦朝一樣短命;當初漢承秦制而損益更張,取代隋朝的唐朝同樣也在隋朝的基礎上開創了自己的盛世;唐朝滅亡後五代十國更迭頻繁,最終歸於趙宋王朝。宋朝最終亡於蒙古人之手,這其實開啟了另一個迴圈:明朝從蒙古人手中恢復了漢人江山,然而最終明朝又被另一個外族王朝所滅。鴉片戰爭後清王朝在內憂外患中一步步走向了滅亡,而在清朝覆滅之後各路軍閥的混戰再次把中國帶入亂世。
自秦始皇嬴政締造大一統帝國以來拋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那些割據一方的短命政權以外主要有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九個王朝:秦朝歷時14年;漢朝歷時424年;晉朝歷時155年;隋朝歷時37年;唐朝歷時289年;宋朝歷時319年;元朝從忽必烈定國號算起歷時98年;明朝作為正統王朝歷時276年,算上南明和明鄭時期歷時315年;清朝從清太祖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算起歷時296年,從皇太極改國號算起歷時276年,從清軍入關建立全國性政權算起歷時268年。
自秦以來的歷朝歷代中只有漢朝和宋朝是真正超過了300年的王朝。明朝算上南明和明鄭時期也算是超過了300年,然而明鄭時期的地盤僅限於臺灣一地且實際統治者已並非朱明皇族。從這麼多王朝裡面只有漢朝和宋朝超過了300年就可以看出一個王朝的壽命要超過300年是何其不容易。事實上超過300年的漢朝和宋朝還是分為兩段的:漢朝分為西漢和東漢且中間還夾著王莽的新莽王朝和劉玄的更始帝政權;北宋在公元1127年亡于靖康之變后皇族後裔趙構逃到南方建立了南宋王朝。
如果把西漢、東漢、北宋、南宋各自作為單獨的朝代進行統計,那麼自秦以來的歷朝歷代中就沒一個超越300年壽命的王朝。儘管中國歷史上罕有超過300年的王朝,但世界歷史上超過300年的王朝卻並不少:法國卡佩王朝歷時341年、普魯士霍亨索倫王朝歷時503年、俄羅斯留裡克王朝歷時736年、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歷時304年、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歷時508年、朝鮮半島新羅王朝歷時992年、朝鮮半島高麗王朝歷時474年、李氏朝鮮王朝歷時518年、柬埔寨吳哥王朝歷時629年,,,,,,
衣索比亞的所羅門王朝和日本的菊花王朝更是號稱有長達2000多年的歷史。日本的菊花王朝迄今為止仍在延續,因此日本皇室又號稱是所謂的“萬世一系”。當然日本皇室的歷史有沒有日本人所吹噓的那麼長是值得懷疑的,但至少從相當於我國隋唐時期日本派出遣隋使、遣唐使以來有明確文字記載可考的千餘年間日本皇室確實是從未間斷過。事實上中國的改朝換代現象不僅僅只是同日本皇室的千年不倒形成了鮮明對比,而是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種較為特殊的現象。
中國曆次改朝換代是後一個王朝推翻前一個王朝,所以兩個王朝之間並沒什麼親緣關係(隋唐兩朝是表親是例外);相比之下歐洲歷史上儘管也存在權臣篡位等問題,但一個王朝以暴力手段推翻另一個王朝並非歐洲歷史的主流。歐洲的改朝換代幾乎都是由於前一個王朝絕嗣,因此在父系血脈斷絕後由母系表親繼位,因此從母系血統上看仍延續著前朝的血脈基因。如今的英國王室從母系血緣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1066年建立的諾曼底王朝。
儘管在諾曼底王朝之後英國曆經了金雀花王朝、蘭開斯特王朝、約克王朝、都鐸王朝、斯圖亞特王朝、漢諾威王朝、薩克森-科堡-哥達王朝,直到1917年如今的溫莎王朝才誕生,然而這些王朝之間都傳承著來自於諾曼底王朝的征服者威廉的血脈,這和中國歷史上一個王朝推翻另一個王朝的改朝換代模式是完全不同的。與之類似的還有法國:儘管歷史教科書中告訴我們被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推翻的是波旁王朝,然而波旁王朝的血統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987年誕生的卡佩王朝。
同樣朝鮮半島的改朝換代也沒中國這麼頻繁:李氏朝鮮作為朝鮮半島歷史上最後一個統一封建王朝立國的時間是我國明洪武二十五年,也就是說那時還是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期,而在李氏朝鮮滅亡後的第二年我國就爆發了辛亥革命,這麼算下來李氏朝鮮王朝的時間跨度幾乎相當於我國明、清兩朝的總和。在李氏朝鮮之前的高麗王朝持續了474年,相當於從我國五代時期一直延續到明初。王氏高麗和李氏朝鮮這兩個王朝的延續時間加起來相當於從我國的五代時期延續到清朝末年。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王朝難以傳承300年以上這種現象是秦始皇嬴政開創大一統帝國以後出現的。秦以前的夏朝傳承了470年、商朝傳承了554年、周朝傳承了790年。先秦三代個個都在三百年以上,可為什麼到了秦以後300年就成了難以跨越的坎呢?事實上自秦始皇嬴政混一華夏以來中國歷史就成為了世界歷史中極為特殊的存在:當歐洲、日本、中東等地處於封建領主割據狀態之時中國在很早就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權。簡單來說歐洲、日本、中東等地的歷史更類似於秦以前的諸侯城邦割據狀態。
歐洲中世紀的封建采邑領主、日本歷史上的藩主大名們就類似於我國先秦時代的諸侯貴族。長期以來歐洲、日本、中東等地形成了王權與神權、君主與貴族持續的博弈交鋒狀態,然而中國卻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皇權獨大格局。恰恰正因為皇權的獨大導致其難以長久的命運:春秋戰國時代儘管諸侯列國之間打得火熱,然而在沒誕生絕對的天下霸主之前誰也不會去打周天子的主意,而民間百姓就更不會對作為名義上的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有多少反感了。
百姓切身感受到的是自家領主的剝削,至於天子彷彿就是一個神話傳說中的存在而已。諸侯領主、世家貴族的存在對王權起到一定製衡作用的同時也為王權分擔了一部分來自底層的反抗。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以來中國的貴族階層就處於日漸消亡的狀態。儘管在古代中國也存在門第高低之分,但這僅僅只是一種世俗觀念,而真正能對國家政治產生影響的貴族階層在中國則是不存在的,因為帝國的所有子民都是皇帝的私有財產。
皇權可以讓人生,讓人死,可以讓混跡街頭的韋小寶一夜間飛黃騰達,也可以讓一個偌大的鐘鳴鼎食之家頃刻間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卻使皇權直接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由於古代中國大一統的集權體制下皇權和民眾之間缺乏像歐洲、日本那樣的貴族階層作為中間角色,於是人們自然而然將自己生活的不如意都視為是皇帝施政的錯誤。當然自漢代以降的中國皇權會受到儒家倫理的一定約束,然而這種約束僅僅只是形式上的——其約束效力取決於皇帝本人是否願意接受這種約束。
另一方面儒家倫理思想也束縛著臣民的思想和行為,從而為皇權形成了一道無形的屏障。然而這種極為脆弱的屏障根本無法阻擋來自底層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吶喊。專制皇權一旦確立就必須時刻保持其絕對權威,然而這就猶如一張拉滿的弓弦一樣註定會有一天因無法承受反作用力而崩斷。在中國古代的皇權專制政體下一個立國上百年的王朝一般來說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積弊,有的王朝適時解決了一部分積弊,於是造就了中興局面。
然而這是緩解了部分積弊,並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所以王朝終究還是要覆滅的;而有的王朝沒能適時解決積弊,於是就成了短命王朝。這種治亂迴圈的反覆交替出現形成了一個看起來似乎是跳不出去的怪圈。這當然並不是說中國古代缺乏改革者,而是改革很難衝破這個無限迴圈的怪圈。在物理學中有一個能量守恆定律:能量既不會憑空產生,也不會憑空消失,而只能是從某一物體傳遞給另一物體,而在這一過程中能量的形式是可能發生轉換的。
在哲學中也有一個類似的概念叫做物質不滅:物質是不能被消滅的,而只會轉換為其他形態。事實從宇宙的誕生、地球的出現以及我們人類的進化歷程所遵循的是同樣的規律:歷史上任何一件看似與我們今天無關的事件其實都是人類大歷史程序中的構成部分,都和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的形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當我們開啟家裡的天然氣灶時我們只想著怎麼做一頓飯,我們不會首先想到世界上第一個發明生火做飯這種方式的人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了何等影響,然而這種影響卻是客觀存在的。
歷史上發生的任何即使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一點一滴匯聚才創造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世界,在歷史的發展傳承過程之中許多看似無關緊要的事卻彼此互相影響著,從而造就了滾滾向前遞進的歷史程序。在這一過程中歷史的演變遵循一定的規律——中國古人將這種規律稱為天命或天道。用我們現代唯物主義的觀念來說這是歷史發展所遵循的客觀規律。我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是不斷髮展變化的,所以即使是好的制度政策也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質。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乃至於我們今天都是在不斷與各種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打交道。我們學習歷史當然是為了以史為鑑,然而我們永遠不可能碰到和過去的人所面臨的完全一模一樣的問題。我們今天就不可能完全照搬當年抗擊非典疫情的經驗來對抗新冠疫情,因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情況和當初是不一樣的。歷史上很多開國之君都指望從制度上確保自家江山千秋萬代延續,然而這種念頭本身就違背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事實上沒任何辦法能保證一個王朝永遠長治久安。
只有當朝之人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不斷進行改革才能維持穩定。在我們的鄰國日本坂本龍馬和西鄉隆盛這兩個風雲人物曾有過一番對話。西鄉隆盛幾乎是以質問的口氣說道:“你前天所說的不同於昨天所說的,而昨天所說的不同於今天所說的。君子應當有堅定的意志,你如此善變怎能取信於人?”坂本龍馬回答道:“非也非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歷史正如奔流不息的長河,時間在推移,時代在變化。因此順應時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
君子並非墨守成規一成不變,而是需要因時因事而變。如今我們的黨和政府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順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歷史時勢,就是以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為基礎所做出的歷史性決定。君子之變不是亂變,而是順應時勢的因時而變。在變化的過程中不能忘記初心,但具體的方法手段永遠是要與時俱進的。然而歷史上的那些王朝都很難做到因時而變,也因此給今天的我們從反面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經驗教訓。為什麼這些王朝做不到因時而變呢?
在物理學上還有一個慣性定律:任何物體都要保持勻速直線運動或靜止狀態,直到外力迫使它改變運動狀態為止。也就是說物體在受到外力影響之前將保持其原有狀態不變,而物體質量越大則慣性也會相應越大。事實上人類歷史的發展同樣遵循慣性定律,因為締造歷史的人是具有慣性思維的。這麼說顯得很抽象,那麼我就為大家舉個例子:在我國的國企改制過程中很多原來的國企員工們其實都預感到了自己的鐵飯碗可能端不了多久,可仍有很多人不願提前自謀出路而是等著廠子破產後被動地再就業。
這是因為人天生會對不確定的事物有一種排斥抗拒的心理。儘管已有人意識到自己的鐵飯碗捧不了多久,可也還是選擇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事實上要讓一種高度成熟的文明體系進行自我改革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人們都有沿著老路走下去的慣性思維。商鞅曾對比當時被視為戎狄的秦國與中原文明的區別認為正是中原地區高度發達的文明養成了盤根錯節的世家貴族勢力,也就是說當文明發展到一定高度後反而出現了異化,而這恰恰正是“人亡政息”的最初征召。
縱觀歷朝歷代的興衰成敗不難發現:王朝初建之時君臣上下往往有一種勵精圖治之心,然而隨著時代的推移就會在朝中形成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久而久之國家就會逐漸喪失前進的動力。這時從小長於深宮之中嬌生慣養的皇帝和朝廷權貴們往往越來越無心國事,日漸追求聲色犬馬,於是對百姓的壓榨越來越嚴重。最終被壓迫的底層民眾迫於生計不得不鋌而走險,與此同時統治階層內部的爭權奪利也愈演愈烈。打天下的開國之君具有無比的威望,所以能壓制住文臣武將和後宮嬪妃們干政的野心。
然而王朝後期的君主們往往不具有這樣的威望,於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權奪利現象也就日趨激烈。所以隨著王朝政治的日趨腐朽必然會導致統治階級與底層民眾之間的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日益增長。直到有一天當君主無法再駕馭各方勢力之時要麼被底層的農民起義推翻、要麼被統治集團內的權臣架空。沉迷於聲色犬馬的南宋統治者直把杭州作汴州。當他們滿足於江南的歌舞昇平之時蒙古人充分學習借鑑漢人的火器、鎧甲,而漢人所不具備的嫻熟的弓馬騎射技藝也被他們掌握得遊刃有餘。
可當蒙古人接觸到中原的富庶繁榮之後也開始追逐起聲色犬馬的享樂,以致於不出百年就回到草原牧馬放羊了。明太祖朱元璋在驅逐蒙古人後開創了自己的大明王朝,那時的他是何等意氣風發勵精圖治,然而過了幾代人後長於深宮的皇帝們變得越來越驕奢淫逸:皇帝怠政、宦官弄權、橫徵暴斂......最終明王朝在農民起義軍和山海關外的清軍雙重打擊下走向了滅亡。清軍入關後平定三藩之亂、統一臺灣、滅準噶爾部......然而和之前的王朝一樣隨著江山日益穩固之後清王朝也迅速腐化墮落了。
類似的故事在中華大地上一再上演:開國之君百戰而有天下,後繼之君卻視天下為自己肆意揮霍之物。明明前面的王朝就是這樣滅亡的,後面的皇帝還不吸取教訓不是傻嗎?事實上人性就是如此的。很多時候道理誰都懂,可身處其中的人卻回不了頭。有人說像和珅這樣的大貪官早就對自己的下場有所預料,可就算料到了就能回頭是岸嗎?事實上當他置身其中之時就已註定回不了頭。人在聲色犬馬的誘惑面前有時並不能像我們這些置身事外的人一樣保持冷靜理智。
像和珅這樣的貪官作為個體無法遏制自己的貪慾,而當整個王朝都沉迷於聲色犬馬的享受之中時墮落已不可避免。王朝的長治久安實際上與追求享樂的天性構成了一對強烈的矛盾。在王朝專制政體下無法從根本上化解如此強烈的矛盾,然而歷史上的確有些朝代透過在某一段時間內緩解這些矛盾而得以續命。緩解矛盾的方法就是改革:透過對不合時宜的舊制度進行變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明代張居正改革、清代的攤丁入畝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緩解社會矛盾的作用。
然而一個朝代要拋棄已實行多年的傳統典章制度是需要相當魄力的,因為任何朝代在維持一定時間後總會催生出一個既得利益群體。即使是那些曾矢志變法圖強的改革鬥士也會因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走到改革的對立面:為什麼秦獻公時期最早提出廢除人殉制度等改革措施的甘龍到了孝公年間就成為商鞅變法最大的反對派?為什麼作為大秦帝國締造者之一的李斯那麼容易就被趙高說服而成為秦帝國的掘墓人?還不就是出於維護既得利益的需要。
變法後的秦國打破了原本存在於秦國貴族和百姓之間的階級壁壘,完全以軍功晉升官爵從而為那些毫無政治根基背景的寒門子弟提供了上升空間。秦國君主和這些新提拔起來的寒門子弟組成政治聯盟打壓世家貴族勢力,然而當這些寒門子弟晉升高位之後就在秦國催生了一個新興的職業官僚集團。職業官僚集團在其發跡的早期是一個朝氣蓬勃的群體——因為他們沒有世家貴族那樣的政治根基,只能透過政績來取得君主的青睞和百姓的認可,因此這時的職業官僚集團致力於積極推動變法強國。
可當職業官僚集團大權在握之後就日益走向變法改革的對立面,因為他們害怕進一步的改革會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大秦一統華夏的過程中立下大功的李斯那麼輕易被趙高拉攏成為秦王朝的掘墓人就是因為不願放棄到手的既得利益。正所謂“屁股決定腦袋”——既得利益集團成員的個體利益並不一定和王朝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利益集團成員儘管得以利用朝廷的威信使自己發展壯大,但當自身利益與王朝利益發生衝突時也完全可能成為王朝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