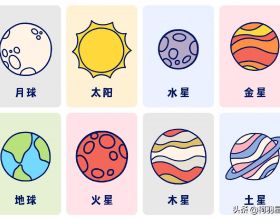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論語》
平凡人的最大缺點,是常常覺得自己比別人高明。
——(美)富蘭克林
人類本性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傾向,這傾向就是你習慣地自以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那麼你必是那樣的人。
——(美)愛默生
《論語》一書,是中國古代儒家文化的重要源泉,現今我們很多道德倫理、人生情趣和精神底蘊,都與之有著基因傳承的關係。在增強和踐行文化自信中,有必要探究文化基因的精髓,知道我們中國人的生命意義所在,人生志趣和人格理想為何,做一名中國人意味著什麼。
人生的修為之境,達致仁愛之大德,要以無私為前提;達致智之真得,要以無蔽為前提。無私非即是仁道,但仁德必是無私之公,大公無私;無蔽非即是智,然智必得無蔽之明,豁達通明。
在仁與智的人生修為上,孔子以自身的深厚學思閱歷和精神底蘊,告訴了我們達致人生仁且智價值目標的前提基礎和修為工夫。在“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的修為工夫中,“克己”既是“復禮”的基礎,又是成仁的前提。
“克己”之修為工夫,既然於人生價值和意義甚大,則就有必要探究“克己”的價值意蘊和深刻內涵。這一問題的答案,就體現在“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的論說中。
這裡的“絕”者,是杜絕、戒絕和根絕之義,意味著徹底的摒棄、絕棄。“毋”者,是不要有、不得有和必不有的意思,意味著自覺地節制、剋制和捨去。
“毋意”修為,旨在去己之私意而誠其意。
“毋意”之“意”,乃是私意或不良的情意。有私意,就會任意和自欺,而不能誠其意。意之為狀,不可勝窮。或為誠或為偽,或為公或為私,或有利或有害,或為當或為否,或是本或是末,不可得而盡其數。
從本性善、本性真上言,人的本心與情意二者未始不一,而有私蔽方使之不一。一則為本心之良,二則為私意之偽;直性則為本心之善,支離則為刻意之鑿;通達於是非則為本心之正,蔽塞狹隘則為妄意之邪。“毋意”則無私,無私而大公,“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
意之誠者,“由仁義行”(《孟子·離婁下》),必然無私意;而“行於仁義”,就是有所計較、臆度的私意。聖賢之“毋意”,就在達致真誠之至、仁愛之純,而無計較、貪圖之私。
心、意、志和性情,四者精神內涵接近,而可相互舉說。舉吾情之喜怒哀樂,若能誠其意而不自欺,裕其必發,達其必行,節其必止,自能“從心所欲而不逾矩”(《論語·為政》),無非道義之行。
在人生誠意正心的修為上,若能真心實意,則心意必然真慤;若能誠心誠意,則心意必然無偽;若能一心一意,則心意必然懇切;若能全心全意,則心意必然專注。
“毋必”修為,旨在去己之固執而必於義。
“毋必”之人生修為,就在於不專必而固執,不絕對肯定,不輕易下結論,不自以為是。堅守“義之與比”(《論語·里仁》)的信念,雖是無適無莫,然也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離婁下》)。固執於必,而不能靈活變通,就是剛愎自用。
“毋必”之“必”,也是心意之必的意旨,意味著人生念識和心意上必如此或必不如彼,必欲如彼或必不欲如此。斷斷必必,自離於義,則必失其時措之宜。大道無方,奚可定執?必信必果,無義不可。
君子之道,是有必不為,無必為。必不為者,在於求諸己由我裁斷而肯定不為,非在於假藉權勢以迫人必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此亦即是“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中庸》)的價值意旨。我不欲人強加諸我,吾也無強加於人。
君子之所必為,是進之必以禮,得之必以義,“居易以俟命”(《中庸》)。進之以禮,則無非循禮之進,而非是無故的必進;得之以義,則無非由義之得,而非是無理的必得。
人生的禍福吉凶,或有命數,故不求其必;人生的盡心儘性,“致命遂志”(《易·困卦·大象》),則是無非必然之功為。循道而必為,則是“惟道是從”(《老子》)的一貫於道。
小人之道,是有必為,無必不為。必為者,在於求諸人,而強物以從我,令人必從己。欲有為,則是喜怒橫行而乘勢以逞,故有大不韙之事。小人無有必不為的“毋必”,則是“行險以徼倖”(《中庸》),喜怒好惡無常,肆無忌憚。
“毋固”修為,旨在去己執迷之固而固於道。
“毋固”之“固”,是心識、情意上的主觀固執、執滯不化和故步自封。從主觀固執上言,是痴迷而不知反,如戀愛上的失去理智;從執滯不化上言,是偏執而不反省,如習俗的陳規陋習;從故步自封上言,是自察而自以為好,如思想學說上的固執己見。
固執而不能通明,便成為心識之蔽障。或為文字之障,桎梏於陳舊之窠臼;或有事業之障,如固守一業而不能相通;或有聲華之障,如追逐名利而不能解脫;或有格式之障,如陷入形式主義而脫離實際;或有道義之障,如捨本逐末而背離初衷。
人若是自固,往往自以為是,而拘泥固執,剛愎自用。 “毋固”之修為,乃針對心識的臆斷、剛愎而言。“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上》)執一而無權的固執,害道更甚。
聖賢的“毋固”,體現在出處語默上是唯義所在,無可無不可;體現在施為舉措上是“不可為典要”(《易·繫辭下》),而能“唯變所適”。固執而不能變通,其道必窮;固執而不能順化,其道不適。“宗原應變,曲得其宜”(《荀子·非十二子》),就在於“毋固”而權宜。
“毋我”修為,旨在去其小我而成就大我。
“毋我”之“我”,是私己之小我。人一有私我之雜念,則必以私小而害大公。有我之自私,則割離於人,不能人我一體,視人若我。人與我有間,便不能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聖人之所以能夠“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禮記·禮運》),就在於“必知其情,闢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達致這一大我的人格境界。
通人我之情,是“必知其情”。在《易傳》看來,只有“通天下之志”(《繫辭上》)和“類萬物之情”(《繫辭下》),方能達致情之通。通人我之利,見利思義,達致各得其利之宜,便是“闢於其義,明於其利”。
憂民之所憂,則可以“達於其患”。“舜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孟子·離婁下》)見人有溺、有飢而視為我之所致,便能有不忍人的仁愛之心,博施濟眾的大我之心。
聖人“毋我”之弘,乃是備天下於我,而不見私我於天下。知我之性容納天下,乃可以知聖人之“毋我”。大人所存,必以天下為度。“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聖人之推恩,旨在實踐大我之精神追求,達致博愛天下而後已。
聖賢之“毋我”,乃是見我也大,用我也弘。藉由“毋我”之修為,就能盡吾之生,竭吾之才,效其所知,而又不私其所能,故能達致“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人生境界。
無私無蔽,就能大公無偏而豁達通明。
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絕四”價值意旨,既是絕棄自私而達致無私,又是捨棄鑿智而達致無蔽。無私無蔽,彰顯了仁、智一體的思維意旨。意、必、固、我的私蔽一去,則廓然大公,鑑識而通明。
從克己之私上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在於克己情慾之私,而達致“容乃公”(《老子》)。聖人仁愛大公,固是無意、必、固、我之私。意、必、固、我有其一之存,便非能有誠之公明。四者盡去,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從克去識蔽上言,是“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荀子·解蔽》)人之為蔽者,“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遮蔽則不明,偏執則不公。
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能無私、無執而兼陳萬物,以使眾異不得相蔽而亂其倫。這一解蔽的修為工夫,就是“虛壹而靜”的“大清明”。聖人豁達通明,固是無意、必、固、我之鑿識,而以天下為天下。
在意、必、固、我之間的關係上,四者相為始終,乃是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成於我。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意起我立,則心識必固塞,而始喪其明,始失其靈。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實生蔽。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
絕止心意、智識之通病,大略就在“四毋”之修為工夫。人若喜動喜進,喜作喜有,偏執迷執,則不墮於意而墮於必,不墮於固而墮於我。墮於四者之中,則不勝其多。先聖隨人之所墮而正救之、止絕之,固有“四毋”的身教示範。
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修為之教,給予我們的人生價值啟示是:
人生最大的清醒,是反省自身是否自以為是。“平凡人的最大缺點,是常常覺得自己比別人高明。”(美國 富蘭克林)自恃高明,便必有意、必、固、我之私蔽和弊患。
人生最大的明智,是反思反省習慣性格。“人類本性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傾向,這傾向就是你習慣地自以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那麼你必是那樣的人。”(美國愛默生)偏執習慣、性格一旦形成,根深蒂固,就會成為自私自利、自專自愎之人。
中華文明五千年,歷經滄桑而綿延不絕,已充分證明中華傳統文化的頑強生命力,和迎接各種挑戰的開拓能力。這一文化內涵,既本自“學·思·觀”的探求真理而來,又呈現著“學·思·觀”的理性自覺和開放思維。讓我們齊心協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時代洪流之中,為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冷靜的思考,清醒的應對,果敢的鬥爭,無愧的付出。堅信“文化自信”,踐行“文化自信”,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實現偉大復興。
歡迎評論交流探討。文中圖片來自網路,感謝版權原作者。如有侵權,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