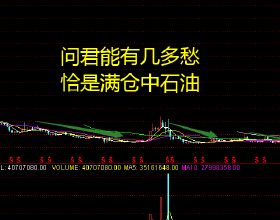葉廷芳(1936年11月23日—2021年9月27日),出生於浙江衢縣,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德語專業,師從馮至。留任助教後,於1964年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歷任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文學》雜誌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中北歐文學室主任、研究員。
葉廷芳那一輩學人的特殊貢獻
新京報:聽聞葉廷芳先生去世……
陸建德:我和葉廷芳先生很熟。我們都曾經住在勁松地區,我們那時候騎腳踏車上班,我經常跟他一起並排騎車。他因為一個手不方便,就單臂駕駛。我覺得葉廷芳先生真是太不容易了,他小時候跌了一跤,手臂跌斷了,有一個地方傷口有炎症,半條手臂就保不住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成就如此巨大,特別讓人敬佩。而且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這也是外文所老先生的一個特點。他們在專業領域成就特別多,寫研究著作、翻譯作品,而且葉先生散文寫得也很好。
我到他家去,印象特別深的是,他收集了很多畫冊,也有很多唱片。他對音樂藝術是特別熱愛的,包括建築。他散文寫得挺多的,出了好幾本散文集,散文集涵蓋的範圍特別廣,有文學、藝術、音樂、建築,特別好。他雖然帶有殘疾,但是他對生活有著一種出奇的熱情,他從來不認為因為自己有一點殘疾,就要受到限制,他一點沒有這個觀念的。雖然身體帶有殘疾,但葉先生身體特別強壯,聽到他離去的訊息我也是非常難過。
他是一個特別熱愛生活、專業知識非常精湛的人,而且跟人交往的時候,他特別隨和開放,我在外文所工作的時候,很長時間都是工會主席,我記得每一年我們外文所春節前聚會,大家聚在一起,會有一些節目,比如朗誦詩、說段笑話,有各種各樣的表演。葉先生每一年都唱歌,唱歌唱得特別好,如果請他來,他是毫不猶豫,馬上就來。
他也在殘疾人協會里面擔任領導工作,這個是要分不少心的。他跟藝術界的人士來往也特別多。我現在想想,他跟一些老藝術家來往密切,我們所聯歡的時候,他也會叫一些藝術家來做表演。葉先生是個精力過人的人,從事多方面的工作、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在參加所有這些活動的同時,他的學術研究又做得如此精湛。
新京報:一般讀者對葉先生的瞭解應該在於他是卡夫卡非常重要的譯者和研究者。
陸建德:卡夫卡是整個現代派裡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改革開放初期,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的時候,外文所有幾位老先生對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是特別大的。我稍微舉幾位人士,比如葉先生,比如柳鳴九先生,柳鳴九先生很早就開始介紹薩特,那時候對中國的創作界、思想界影響都很大。再比如說李文俊先生,李文俊先生要比葉廷芳先生稍大一些,今年大概有九十一二了,李文俊先生翻譯的福克納……他們(的翻譯)的影響完全超越了外國文學的範圍,對我們整個文學評論界、文學創作界都有著巨大的影響,所以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在很多方面得益於這些老先生對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而且也使得我們突然意識到有很多事情原來是可以這樣寫的,在立足本土的同時借鑑外來資源,不斷開拓新的領域。尤其像卡夫卡,他完全超越常人的想象,深深地種在我們的閱讀經驗裡面,這種經驗伴隨著我們成長。
我們要去問當代很多作家,他們閱讀這些作品的過程都是難忘的經歷,也跟他們的創作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所以,要紀念葉先生這樣的人物,我覺得不光是外國文學界,整個讀書界、包括中國當代作家們,都會感念葉先生,以及他們這一輩學人做出的特殊貢獻。
新京報:葉廷芳先生出過一本《現代審美意識的覺醒》,像葉先生他們對中國的文學審美走向現代性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陸建德:關於審美,有些人也在講中國傳統審美等等,但我們要超越國別的界限,我們的審美是不斷在演進的,而且是雜糅的。我們要看到,自己國家的審美傳統也有很多外來的因素,包括佛教的因素。到了19世紀末以後,審美現代性對中國的衝擊是很大的,而且它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我現在在杭州接電話,我吃飯的地方附近就是林風眠先生的故居。林風眠先生是中國20世紀的大畫家,他有中國傳統繪畫的根底,但他又糅合了國外的風格,他的繪畫裡就有非常鮮明的一種審美現代性。所以葉先生在那個時候提出審美現代性,是特別有意義的,讓我們意識到審美並不是一條直線,(不是要)完全適中,審美的預期也是一樣的,審美恰恰應該有大量的東西是要挑戰我們的預期的,突破預設的疆界,這背後是一種解放的力量。
像葉先生他們這一輩,在改革開放後提出審美現代性,讓我們意識到審美上我們完全可能有諸多的可能性,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恰恰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當代藝術的多元景觀,也跟葉先生他們所提倡的這些觀念是有著緊密聯絡的。這也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的審美其實是處於流變之中的,有著一定的延續性,但這種延續性時間久了又可能會僵化,束縛我們的審美想象,所以需要有一些新的東西來不斷挑戰這種預設或者傳承,走向一種未知的審美前景。
有了這樣一種開放的心態,我相信可以告慰葉先生的是,在今天或者以後,我們還會不斷迎來新的審美的現代性。

《現代審美意識的覺醒》,葉廷芳著,華夏出版社、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年。
譯者、寫作者與活動家
新京報:在日常生活中,你對葉先生有一個怎樣的印象?
陸建德:他特別喜歡跟人來往,有著作也會送給朋友,我也有他的著作。他的家鄉是衢州開化,開化有一種茶葉叫龍頂,我想起來,他原來身體比較好的時候經常到家鄉去,從家鄉回來就會給我帶他的龍頂茶,他一再強調龍頂茶比杭州龍井茶還要好。後來他身體不太好,行動就少一些了。
新京報:剛才聊到幾位非常重要的譯者。還是再具體問一下,你認為譯者在文化層面有著怎樣的重要性?
陸建德:太重要了。昨天我還在上海參加一個活動,上海譯文出版社的一個翻譯獎。大量讀者讀作品,雖然是讀卡夫卡的作品,但他畢竟不是讀原文的,要靠中文來認識卡夫卡,如果透過中文來讀卡夫卡,到底是讀卡夫卡還是在讀葉廷芳?這是一個經過葉廷芳消化的卡夫卡。譯者不可能完全抹去他的自我,所以像葉先生,他的看不見的精神其實都滲透在這些翻譯文字之間。我們在懷念葉先生的同時,要看到翻譯者有他們不可抹殺的巨大的功勞。一方面,他們對自己研究的語言有精湛的研究;另一方面,他們的中文寫作都是相當不錯的,這是外文所的傳統。像更早的馮至先生他們,中文都是特別好,有了好的中文才可以成為好的譯者。

《論卡夫卡》,葉廷芳編,葉廷芳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新京報:說到“好的中文”,剛才也一再提到葉廷芳先生的隨筆寫作,你怎麼看他的隨筆寫作?
陸建德:他的隨筆寫作是帶有抒情意味的,想象是發散性的。這裡我一定要強調的是,他對各個地方的文化事業也抱有關懷精神,比如說對北京古城的保護,他都有很多見解。除了寫作之外,他在文化上也是個活動家。
採寫 | 張進
編輯 | 青青子、羅東
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