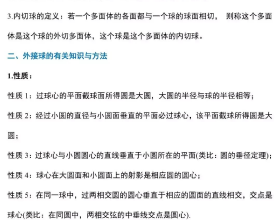作者:西夏王子
娘捏杏核似的,嘣兒嘣兒生下三個幹蛋蛋兒子,還不收心,一心想要個丫頭。饞娃還在娘肚子裡轉經的時候,娘有一種強烈的預感,這一胎保準是丫頭。開春,娘身子又不閒了。這次害喜與以往不同,重點是饞得慌,饞起來嗓子眼像貓抓。能吃不能吃,看見就想撲上去咬一口。婆婆給豬餵食,先往豬槽裡倒一簸箕粉碎的豌豆秸稈,再和進兩馬勺麩皮,最後將一盆滾燙的麵湯譁一下倒入。豬槽內瞬間霧氣升騰,騰騰的霧氣裡,夾雜著秸稈和麵湯混合的味道。不等婆婆攪勻,狫狫和它的一窩豬崽們,群蜂一樣衝上前來,圍得豬槽針插沒縫。娘腆著腹部,聞到她認為的香味,恨不得撥開豬崽子們,抓一把豬食放進自己嘴裡。人總歸是人,豈能和一群豬搶食?這是娘後來對饞娃一個人講的。春天,吃葛蘆芽、莧麻芽、苜蓿芽、苦蕖並不稀奇,但懷饞娃的娘,吃過涼拌的柳樹嫩芽和摻了山桃花花瓣的雞蛋湯。山桃樹漫山遍野,花開時節,白茫茫一片,空氣裡飄散著臭烘烘的氣息,娘卻迷戀這怪味。一碟子涼拌柳樹芽,讓娘鬧了三天肚子,喝完加過山桃花的雞蛋湯,雖然無大礙,但肚子脹了一晌午,她摸著緊繃的肚皮,一想到即將要來到人世的丫頭,倒不覺遭罪。
快手、抖音等霸佔人們日常生活的時候,千奇百怪的美食博主應用而生。饞娃突然想起娘來,如果那陣兒有網路,她絕對是第一個衝在前面的美食博主,山野裡叫上名叫不上名的花花草草,她都嘗過。娘懷饞娃時害喜的過程持續時間很長。夏天,娘嘗過狼毒花的根,開始麻麻的,辣酥酥的,後來舌頭木木的,像腫了一樣,吃啥也吃不出味道。蘇臺人管狼毒花叫狗娃花,有一回,饞娃捧著一束狗娃花回來,娘看見,一把奪過去,順手找來一根棍子,不由分說,往他身上抽,邊抽邊訓,再見你拿狗娃花耍,我剁掉你的爪子!
娘肚子劇痛一夜,於黎明十分生下饞娃,產婆把胖乎乎的饞娃掬捧給娘看,娘沒有看臉面,直接將目光投向饞娃的兩腿中間。天神,又一個幹蛋蛋!短暫的失落過後,娘喝了一缸子紅糖水,吃了一海碗雞蛋掛麵,將剛出生兒子疼愛地攬入懷中,開始餵奶。看著兒子如小狗娃一般在自己懷裡吧唧吧唧嘴巴,娘以憐惜的口吻輕喚一聲:我的饞娃?
饞娃的名字由此而來。
爹對饞娃的不請自來,沒表示稀罕也就罷了,幾次攛掇娘把饞娃送人。娘不捨。爹緊咬牙花子說,你養著吧,看長大後不把頭給你啃了!娘說,一隻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娘生怕爹把饞娃搶走送人似的,帶說著把他往緊抱了抱。有一天,娘放下饞娃,去後院的洋芋窯掏了兩籠子洋芋,上來後,拍天叫地找不見饞娃。她剛才在窯裡,隱約聽見“收——狗兒羊皮——”的吆喝聲。吆喝者是毛皮販子,常年累月遊走在各個村莊。他不光收動物毛皮,還兼職做一些不被人待見的事情,比如,把誰家瓜女子引到外地變賣啦、把誰家牛偷偷牽走啦,等等。人送外號馬糊塗。娘一想到馬糊塗,心裡一驚,忙忙往村口跑,緊趕慢趕,馬糊塗已經上了東山樑。上了東山樑,就到了林區,林區有進山人踩出來的路,穿過林區,出深谷,就到了另一個縣的地界。娘發瘋似的往東山樑跑。快到林區時,馬糊塗放下饞娃,自顧自溜了。後來,娘和爹的一次吵架中,爹不小心說露嘴,饞娃不是馬糊塗偷走的,是他送給他的。馬糊塗答應爹,下次來時以一隻馬籠頭和一片屜子來答謝。
從小到大,娘沒告訴過饞娃這件事,但饞娃還是聽村裡人說了。所以打心底憎惡爹。
饞娃的成長速度宛如五六月間的麥苗,只要雨水充足,並適當地施以尿素,雨過天晴,太陽紅堂堂一曬,麥苗噌噌往高竄。饞娃還是碎娃娃的時節,就能吃能喝,從不挑食,啥端到面前,呼嚕呼嚕一肚子。饞娃飯量驚人,三個哥哥加一塊兒,才能抵得上他。這種現象,一直保持到他長大。
饞娃沒進過一天學堂。剛成年,就撇下死牛鞭子,隨村上一幫老爺們兒出門務工去了,從小能吃能喝,身形並不單薄,與同齡人相比,大出一個型號不在話下。走哪都是裝卸工,火車站扛過麻袋,水泥廠裝過水泥,化肥廠裝過化肥。三個哥哥一個個娶妻成家,光有一身蠻力的饞娃猶如丟棄在荒漠的一塊石頭,在家裡成了一個多餘的可有可無的人。要不是娘在前頭為他撐腰,回到家連一碗飯都沒有。
娘離世時,不知得的啥病,肚皮脹如球,圓咕隆咚。她依稀記得多面前喝山桃花雞蛋湯的那個晌午,可是今早吃過啥,已全然不記得。娘走後,饞娃有家不能回,嫂子左眼不睜,哥哥右眼不抬。嫂子有時候指窗子罵門,說什麼養頭豬還能刮二斤肉;以往,有娘在,他才覺得家在,娘沒了,他不知道回來還圖個啥。再出去,就很少回來。爹無常後,饞娃放下對他的恨意,回來奔喪。三位哥哥相互扯皮,沒一個人捨得掏腰包給爹買棺木,饞娃站出來,買來棺木,請來眾鄉鄰辦理喪事,木匠連夜打造棺材……四天時間,爹得已入土為安。下葬時,饞娃洪亮的哭聲響徹山嶺,聞者悲切。
饞娃三十出頭,有幸找到媳婦,心甘情願當了上門女婿。打工回來,上繳錢財的時候,丈母孃眉開眼笑,恨不得把家裡好吃好喝的都獻給女婿。熱乎勁一過,丈母孃再看饞娃的眼神就不對了,咋看咋多餘,咋看咋不順眼。好在自個女人把饞娃當人,每到吃飯的時候,饞娃在上房吃過兩碗後,女人就喚他來廚房,蹲在灶火門前呼嚕呼嚕又是幾碗,直到鍋裡山窮水盡,直到飽嗝連連。
饞娃有喝罐罐茶的習慣,可是家裡只有一隻火爐,還放在老丈人和丈母孃住的上房裡。起初,饞娃只能在兩位老人過足茶癮後,悄沒聲兒溜進去,熬著喝它兩罐。如果哪天被丈母孃發現,雖不當面奚落他,卻要拿眼睛瞪一番。丈母孃晼人時的眼睛,活像一把鋒利的小刀。後來,女人見饞娃不受老人待見——尤其母親,她專門跑了一趟集市,買回來一隻電爐子,爐子和不鏽鋼缸子連在一起。電爐子放在她和饞娃住的廈房裡。這樣,饞娃早起喝茶的問題解決了。
好是好換來的。女人疼饞娃,饞娃也不是那不知熱冷的人,她給他一碗水,他便還她一碗油。饞娃再出門打工掙錢,更加不惜力氣,雖然乾的是能掙死驢的苦活累活,但他一想起女人的對他的好來,心尖尖像抹了蜜,一直甜到五臟六腑。饞娃越發有心勁兒,重物在肩,也不妨礙他吼兩句秦腔,看似大老粗一個,卻能唱出女單的音色:
他那二老去世早,送在我家把身存
我的父待他如瑰寶,我的母待他如親生
老丈人和丈母孃相繼離世。饞娃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讀高中的讀高中,上中學的上中學。他有種人民當家作主把歌唱的感覺!
饞娃繼續打工,繼續當他的裝卸工。有一天,不幸突然降臨,他開電瓶車轉貨途中,行駛至一個漫長的下坡路上,剎車失靈。情急之下,用力打了一把方向盤,車撞向水泥牆。腿筋受傷,緩三個月好了,但腰部受到重物擠壓,腰椎出現裂縫。一個強壯的男人,全靠一副好腰撐著。饞娃的裝卸工生涯就此結束。
四十五歲的饞娃,初次走進工地,當了一名小工。饞娃第一天進工地,中午飯幹掉四個饅頭兩碗米飯兩份菜,晚飯幹掉兩碗高壘山尖的兩盤炒麵條,工友皆震驚!饞娃體重一百八十斤,高(架)空作業就發抖,他抖的是身體,老闆抖的是心。老闆心好,安排饞娃整理庫房、拉電纜、噴漆等工作,只要不上高架,饞娃啥都樂意幹。經他整理的庫房,乾淨,整潔,水泥地也用吸塵器吸過。有一天,突遇集團領導來檢查,饞娃打掃的庫房上了“名人榜”,公司獎勵老闆兩萬元。公司大劉總承諾,這種效果保持到年底,再獎勵兩萬。老闆高興壞了,當晚請宴請工人,吃了99元一位的海鮮自助火鍋。
饞娃在工地上立住了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