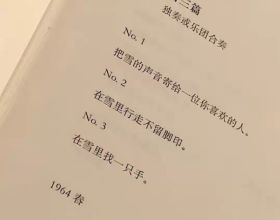直到今年,母親才結束自己從事六十多年的農耕事業。但她還是去跟村裡的承包大戶拋了兩天秧,既過了一把“雙搶”的癮,又賺到了100塊錢一天的工錢。在電話裡說起這些事,母親樂呵得很,頗有一種寶刀未老的豪情。這讓我恍然驚覺:每年夏天,湖湘地區轟轟烈烈的“雙搶”,早已跟過去不可同日而語了。傳統的肩扛手刨式“雙搶”正在遠去,現代的全機械化“雙搶”生機勃勃。生於農村經歷改革開放的我們,開始懷念親歷的“雙搶”,它是我們七零後成長的見證。
雙搶,顧名思義是把早稻收割回來,再把晚稻秧苗插播下去,搶的是播種的季節,搶是各家各戶做事的氣勢。我們湖區的雙季稻,風調雨順的年份,雙搶的開始時間一般是7月10號左右,有個別比較乾旱的年份,一些人家的早熟品種會在7月4號左右開始動鐮。為了趕時間,一般是田裡的稻穀接近八九分黃時開始收割。雙搶是盛夏季節的農事,太陽出來了就非常燥熱,鄉親們一般四五點鐘就起來去幹活,大清早做事效率要高很多,人也沒有那麼累。
大集體時代,雙搶要持續三十多天;同樣的田土,同樣的出工人數,承包到戶後,雙搶的時間迅速縮短,從最多的二十多天,到半個月,一個星期,到如今的三四天即可完成。農業機械化的逐步實現是主要原因,但人心齊泰山移也是決定因素。到季節了,只要“扮桶”了,誰家也不甘落後,一個生產隊裡,最先完成搶插任務上岸的那一兩家,表面上不說,言行舉止之間,卻無不透露出一種自豪感——一個種田的農民,無非就是拼那一畝三分地的長勢,拼家中糧倉裡的堆勢;當然,假以時日,還要拼孩子,拼房子。
“雙搶”第一年,有大我兩歲的姐姐在,父母是如何完成雙搶的,我的腦海裡幾乎一片空白。在1979年秋天,九歲的姐姐屁股上生個疔瘡,被村裡的赤腳醫生用錯藥而去世了;姐姐身上的擔當和期待,全部落到了我的頭上。我成了家中的老大,父母去田裡幹活的時候,照看兩個弟弟,掃地、煮飯就成了我的日常。當我十來歲的時候,就開始真正參與“雙搶”了。
當然,剛剛開始,我們小孩子能做的事不多,鋤草鋤不乾淨,插秧插不齊,踩打穀機個子不夠高,割稻常常傷到手指,甚至連一個放水的缺口都堵不住,我們完全能勝任的事情就是“摟禾把子”。而我恰恰最受不了的就是摟“禾把子”。剛剛割下來的禾杆,再大的太陽也曬不焉,它的鋒芒紮在手臂上,又癢又痛,這實在不是一個十多歲的孩子能一笑而過的事情。當然,這也是懶人挑重擔的弊端,如果不是為了偷懶,摟三四個“禾把子”到手上,而是一手一把,也不存在把雙臂弄得紅通通的。幸好父親做事心細,找到比別人省時省力的方法,他帶頭把一行行“禾把子”放成向中間聚攏的形式,一個扮桶拖過來,加上“遞與喂”兩者之間的距離,兩邊摟“禾把”的人不過走個三四步遠,就能把一桶禾靠邊的“禾把”摳到手中。
脫粒、曬穀,是每家每戶必做的事情。
最先幾年,當地稻穀脫粒的工具是人工扮桶,完全靠腳力的踩壓來帶動扮桶裡裝滿n字形齒輪的滾筒,大人緊扣“禾把”底部,讓稻穗部分在轉動的齒輪上摩擦,達到谷、穗分離的結果。這個工序,遞和喂的人最少要四個,最少一個“出谷(把扮桶裡的稻穀用撮箕裝到籮筐裡)”的人,還要一個人把一擔擔稻穀(俗稱“毛糠”)送回家。某個環節差人手時,其他人就要停下來幫忙或等待。這樣一套完整的班子,最少要六個人,大家一天的效率大抵是能收割完一畝七分地的稻穀。
因為很多農活單憑兩雙手是做不來的,第二年從開春起,父母就與一個兄弟家結伴,兩家四個大人聯手就可以盤活這場農事了。兩家的孩子差不多大小,真正幹農活還指望不上,兩家田土差不多,投入的種子農藥化肥等各自承擔,兩家只是在耕耘和收穫時合夥來做。今天收割你家的二畝二,明天收割他家的三畝六,收割回來後,利用空隙時間曬稻穀、捆草、打水,就是各自中午休息時間或者晚上的安排了。飯菜自然是到哪家做事就到那家吃飯,伙食什麼的並不講究,辣椒炒肉應該是一個祖宗菜了。抽得出時間的話,主人家會想方設法做些鯽魚、鱔魚、菱角、蓮藕等來改善伙食;在田間事做到中途,經常會有綠豆粥或西瓜、冰棒的補給,在我看來,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就是最好的美味了。
親戚之間結伴雙搶是常規操作。
最初幾年,家家戶戶都是用大水牛來耕田。那時水牛耕耘有四道工序必須要做:犁田、踏平、打滾、浪平。耕完之後,才能開始栽秧。對於這個“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耕牛,平常的照顧和餵養是必不可少的,因而,農閒時“放牛”便成了我做完作業之後的“主業”。由於平原地區到處都是莊稼,荒地極少,放牛可以去的地方並不多,最多的時候是把牛趕到田間排水渠,牛站在水溝裡,舔吃水溝兩邊的青草。放牛娃有時會騎到牛背上放鬆一下腳力,但眼睛一刻也不能放鬆,要防止大水牛突然伸長脖子,越過田埂去吃禾苗。
好在放牛不過三五年的事,然後,農村陸陸續續出現了半人工的“大鐵牛”——“動插頭”耕田。這個“動插頭”有點大鵬展翅的模樣,前面一個裝著許多鐵片的輪子,輪子上面是鐵架,鐵架上面用螺絲固定著一臺柴油機,緊挨著柴油機的位置有一個大“凹”形臂膀,臂膀連線的脖頸位置有一個鐵圈,可以橫穿一根手臂粗一兩米長的棍子。這個大鐵牛是可以直接開到田裡的,但是,人們為了節約柴油和減少鐵牛的損耗,一般是由兩個壯年勞力抬到田裡。雖然鐵牛代替了水牛,但是前面要有個人開動機器牽引,後面要有個人扶犁及浪耙等工具,才能完成耕耘的目的。經過幾年的改進,“動插頭”就變成了“坐耕機”。顧名思義,“坐耕機”就是前面做牽引的人不用再泥一腳水一腳地涉水,而是坐到“凹”形臂膀的後下方,一個屁股大小的托盤上,而後面拖拽的農具,也全部由木質變成了鐵質。重量的增加,動力的加大,坐耕機只需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稻田的全部耕耘程式;當然,任何事物有利也有弊,在我們當地,因操作不慎,一個年輕力壯的勞力被坐耕機軋斷腿的情況出現過幾起,甚至還有人因此喪命。
農業機械化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但每一點細微的進步,對於每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來說,都無異於一次如釋重負的解放。我清楚地記得:大鐵牛的橫空出世,得益於柴油機的發明和在農村的適用,所以,最先開始機械化的是柴油機與脫粒機搭配。
最先的稻穀脫粒是用扮桶,人們將稻穀收割後,把“禾把子”挑回家,擺在禾場上曬乾,再一把把抓緊,用力到扮桶的四周內壁去捶打,直至每一個禾把子上的稻穀全部掉完。萬山作協主席楊再樹老師寫過一篇《連蓋聲聲入夢來》,說的是貴州這邊最原始的打稻脫粒方式;二者一對比,我還是暗暗讚許“連蓋”所附帶的文化底蘊和執行力度。誠然,我對打稻的記憶並不是從完全意義上的“扮桶”開始,而是來自於經過民間的能工巧匠加工之後,自帶踩踏功能的滾芯扮桶。不說“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我能深深感受到腳踩的扮桶給大人帶來的勞累,他們要一邊腳踩踏板,一邊手喂禾把,手腳同時用力,才能把稻穀打下來,儘量減少浪費。古人的“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可以說是最能反映莊稼人的艱辛的經典詩句。
用上柴油機後,打稻穀還是要人工去喂,但是不用腳下發力了,至少省了多半的力氣,這對於一個卯足勁趕節氣搞雙搶的人來說,是一個極大的福音。我清楚地記得:父親在踩脫粒機時,表情是嚴肅的,是倔犟的,從側面看過去,他的嘴唇微張,上氣不接下氣,有點自顧不暇的感覺。而用上柴油機後,當我們把禾把遞上時,只見父親雙唇輕抿,滿眼慈愛地接過去,嘴裡還要叮囑幾句:帽子歪了,別跑,少摟點,別讓禾把扎到了……
我們家的這臺柴油機,用了三十多年,帶完脫粒機帶動插頭,後來別人家有了坐耕機給鄉親們包工,柴油機就被“待字閨中”,不再有到田頭耍威風的時候了。雖然被“雪藏”了,柴油機還是被父親當作寶貝一樣,隔三差五地加油 、擦拭,鬆動再擰緊那些螺絲。這時,只是偶爾需要柴油機帶動乾塘的水泵才會想到它的存在;而現在水泵被改為電泵,柴油機才退出了歷史舞臺。前幾年,父親才把這個完好無損的寶貝疙瘩當廢品賣了。
脫粒的時候,當預備的三五挑籮筐裝滿毛糠後,脫粒的班子就暫停了;父親們忙著把毛糠送回家並順便攤曬開來,母親們喝一口桶子裡放了鹽姜的井水,就拿起鐮刀“唰唰唰”地割稻去了。只有孩子畢竟還是孩子,轟鳴的柴油機剛一停下來就離開了勞動區域,花樣喝水、把稻草垛起來方便或者假寐、抓個蜻蜓或蚱蜢用野草綁起它的翅膀、處理一些表面上的小擦傷、到溼潤的稻田捅黃鱔、去滿滿的引水渠泡一下腳等等,搞得不亦樂乎。當我們覺得放鬆得差不多的時候,或者經過大人召喚,才回到大人的身邊,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小時候做不了插秧的活,現在倒是挺拿手的。
十來歲的孩子幹農活,只是帶出來認知這個勞動過程,不能指望湊到人數當天一定要完成指定的任務。當我十三四歲時,才開始體恤父母懂得競爭,只要出工就拼盡全力去做,一環接一環,再也沒有偷懶的意識了。當一丘稻田的稻穀全部收割回家後,父親的事情是把稻穀挑回家,撿草,再去電排排隊打水;母親的事情是回家去毛糠曬稻穀,還要見縫插針把飯菜弄好;我跟弟弟們的任務是把稻草捆起來,並拖到田埂上暫時避水,等父親晚上打水到田裡來了,就一邊看水,一邊用板車把稻草拖回家,晾曬在房前屋後的空地。
撿草,是一項比較輕鬆但講究技巧的工作,十多歲的孩子基本上能勝任,卻會因為不用心沒用力而散掉,導致要返工重做。稻草的軟硬程度跟稻穀的品種有關,最難撿的就是硬邦邦的雜交稻草,一些粳稻和糯谷的稻草,經過一兩個小時的暴曬後,變得十分柔軟。撿草的時候,只需抓起十來根稻草擰成一股繩,放到稻草尖上,取適量稻草,兩手合併把稻草立起,將草繩繞兩圈打個活結,用力往上一帶就扯緊了。這樣就把稻草捆成了一個個稻草人模樣,然後順勢把這個“稻草人”甩出去,讓其底部儘量散開,一個個像“兵馬俑”似的立在田中儘可能曬乾。
後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房子蓋起了水泥瓦,燒火煮飯用起了煤爐,液化氣等,田裡的稻草就不用撿了。我們拿根竹棍去把這些稻草挑開,由滿田的稻茬隔著曬,等六七分幹了,如果田裡要放水過來了,就一把火燒了漚肥,當然現在不再這麼做。再到後來有了收割機,稻草田裡留一半,被脫粒機自動截斷一半,無法打捆拉回家,也只能趁著月黑風高的夜晚去燒了。
稻草拉走後,我要做的事就是“薅路邊草”。稻穀收割了,四周田埂上的野草愈發顯得鬱鬱蔥蔥,在還沒有“草藥”問世的時候,“薅路邊”是雙搶途中沒有時間安排而又必不可少的事情,用華羅庚的“統籌學”解釋就是:這個工作是夾在“撿草”、放水、犁田或平田的時間做出來的。無需一個正勞力就可以做好的事情,當仁不讓就落到了我這個老大的身上。有一次我用力不當,鋤頭削到了自己左腳的當面骨上,差點點砍斷大動脈而釀成事故。這個事情既沒有成為“下不為例”的教訓,也沒有成為父母不讓我幹農活的理由。我自己也不曾覺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在以後的雙搶生涯中,反而再次出現了幾次“鞠躬盡瘁”的事情。
幹農活也需要用好技巧。
人們都說“六月天孩兒臉——說變就變”,這話一點沒錯。在我印象裡,當我們累得像狗一樣在田間勞作的時候,頭頂的烈日驕陽眨眼之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滿天的烏雲滾滾,風雨欲來。雙搶期間一般家裡禾場上都曬了稻穀,天氣驟變,田間的人就要立即跑回去搶收稻穀。這樣突如其來的天氣變化我們稱之為“風暴雨”,這個雨可能只有幾分鐘最多一二十分鐘,但是滿場即將曬乾的稻穀,一分鐘的暴雨也不能承受。我們的稻田都離家不遠,最多的一里多路,天氣一變,大家就以百米衝刺般的速度往家跑。我就在有一次跑回家後中暑了,突然暈倒在地,父母把我抬到涼板床上,掐人中、刮痧急救。儘管只昏迷了兩三分鐘就被弄醒來了,但是我這份回家搶稻的迫切之心父母是看在眼裡,疼在心裡。這樣的雙搶我做了十多年,直到我結婚成家後外出打工,就很少回孃家下過田了。令人欣慰的是:家鄉的雙搶日趨進步,捨不得放下土地的父母已不用那麼勞累了。
接下來,出現了培育秧苗的拋秧盤。拋秧盤鋪在秧田裡,把發芽的種子少少撒一遍,保證每一個孔裡有五六粒種子,然後再用掃把掃一遍,這樣,每一個秧孔裡都有泥水蓋住了,在起秧苗拋秧的時候,每一個孔裡起出來的秧苗根部都有一定的重量,像孩子們踢的毽子一樣,丟擲去大部分都能落到想象中的位置。以前靠人工彎腰插田的時候,手腳麻利點的五個人,一天最多能插兩畝田,現有了拋秧盤後,兩個人能幹出五個人的活,還不用那麼腰痠背痛的累。還有一種撒谷插田法,就是把發芽的種子直接撒到平整而少水的大田裡,省了母秧移栽的手續。
插秧也是一門手藝活。
2007年雙搶前,父親欣喜地告訴我:老家來了很多收割機。這些收割機都是從安徽、河南等省坐大型拖車過來的,到了鄉村公路後,這些收割機就自己開到機耕路,這些農戶就爭先恐後地去喊他們來給自己家裡收割。儘管要收50塊錢一畝的費用,很多家庭都願意出這個錢;因為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他們掐指一算就知道:是自己請假回去搞雙搶划得來,還是拿出一筆錢來支付這個費用,自己在工廠裡多加幾個班划得來?
而現在的農村耕種狀況大抵如此:只有極個別在家裡或附近有其他事情做的青壯勞力,就兼顧著種田的事業,沒有讓稻田荒蕪了,絕大部分人家都是把屬於自己名下的田土以兩百斤稻穀一年的報酬而承租給片區農業大戶。農業大戶承包的幾十甚至幾百畝良田,用機械的地方,一到三天就完成了雙搶,有些不得不用人工的地方,也是反請那些給田土的農戶家裡的老者,這樣雙方互惠互利,共同獲取這些田土產生的利益。
多年的農耕文明——雙搶,已經在這片“魚米之鄉”成為非主流之下的主流;儘管人們以各種方式打拼著自己的人生,但是,土地是基石是根本,糧食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命脈,二者缺一不可。我們將永遠引以為豪:勞動者是大地之子,勞動無上光榮。
我出生於七十年代初期,歷經了湖南長嶽益三角地帶“雙搶”從發展到興盛,從全人工到機械化的整個過程。現在的“雙搶”跟城裡人朝九晚五的上班模式差不多,已不爭不搶,短短几天就完成了,相比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進,而我歷經的“雙搶”貫穿整個八十年代,直到1993年高中畢業,開始外出打工。後來快30年時間,我下田搞雙搶幹農活的時間累計沒超過十天,身子骨早已不能承受當初那種彎腰駝背的農事,但那些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如今,我人生的第一個導師、引領和教養我怎樣做人做事的父親,已經離開我們兩年多了,我家的“雙搶”時代已落下帷幕。而“雙搶”的畫面依然像立體鏡頭一樣,時不時出現在腦海當中,提醒著我腳踏實地,不忘葉落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