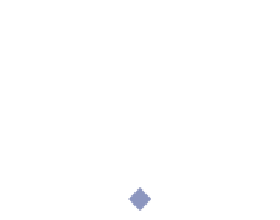三十年前的一個冬夜,一家人圍著火爐取暖,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閒話,突然,眼尖的妹妹發現伙房門口有一隻白貓在探頭探腦。
起先大家都沒理睬,但那隻貓一直在門口徘徊,沒有離去,卻也不敢接近我們。
母親猜它是餓了,就拿了點剩飯,用一隻破碗盛了放在門口。
那隻貓很警惕地慢慢走近,聞了聞那點剩飯,卻沒有立刻開吃,圍著那隻碗轉了好幾個來回,幾度離開又返回,最終還是忍不住低頭怯生生地吃起來。
不大一會兒,那點剩飯就風捲殘雲,掃蕩一空了。
吃完後它就消失在黑沉沉的暗處,我們都以為它走了,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們發現它還蜷縮在伙房後面的雜物間裡被煙燻得黑漆漆的大木櫃上。
母親依舊用那隻破碗盛了些稀飯,放在門邊,等它自己來取用。
我們以為它是附近壪子裡某家走失的,想到它的主人會尋找,並沒有指望長養它,但一直沒有什麼聲息。
這樣一連幾天,大概是看到我們沒有什麼惡意,那隻貓就在我家住了下來。
它也逐漸敢於走到我們身邊,豎起尾巴、昂起頭,與我們的腿挨挨擦擦,甚而接受我們手掌的愛撫。
不知不覺,它成了我家的新成員,隔一會兒沒見它的身影,都會有人查問它的下落。
我和妹妹放學回來,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它。
這隻貓來的時候邋里邋遢,刺毛刺球,也很消瘦,但過了一段時間,它毛色日見光亮,也顯得精神起來,常常和妹妹玩鬧。
它沒有名字,妹妹總愛喊它一個字“咪”,它也逐漸習慣了這一稱謂,我們說“咪”,它就知道是在說它,就立刻跑到我們面前或者抬頭目不轉睛地傾聽。
妹妹用毛線逗它,它也樂此不疲,玩累了就跳到她身上蜷臥,安靜地接受愛撫。
有時候它坐在火爐前打盹,發出輕微的呼嚕聲,我們覺得很有趣,禁不住發笑,聽到我們的動靜,它也把眼睛睜開一道縫,約略一瞧,又歸於夢鄉。
大約一兩個月以後,我們給它的殘羹冷炙,它也不大吃,我們都感到很迷惑,以為它生了病,但它依舊生龍活虎地,身體上看不出什麼異樣。
一直沒看到它捉老鼠,我們以為它是隻懶貓。
可是隨著春天到來,情況完全改變。
我們聽到房前屋後徹夜有貓兒“悽慘”的叫聲和廝打的聲音,看來我家的白貓戀愛了,它原來是一隻年輕的母貓。
有個把星期,我們很難再找到它的身影,喚也喚不回。
等房前屋後再次歸於靜寂,我們卻驚奇地發現我們的白貓常常拖一隻大老鼠回來,在灶背後津津有味地吃,還不要人靠近。
如果我們走近,它會趕緊一口咬住老鼠,張皇地鑽進碗櫃底下,似乎害怕我們與它爭食。
我們一時對這樣的變化感到很驚訝,但很快,隨著當年蠶種的到來,我們都歡喜不已。
因為有了這隻貓,不用再擔心老鼠偷蠶吃了。
養蠶是我家當時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所以這隻貓也順理成章成了我家的保護神。
我們逐漸對白貓捉老鼠見怪不怪,母親也逐漸忘記要給它剩飯了,那隻貓也逐漸敢於把老鼠拖到火爐邊來享用,夜裡我們再也聽不到窸窸窣窣的老鼠動靜了。
再後來,在廚房堆放柴火的角落裡,我們常常無意間會發現死老鼠,那是白貓吃不了藏在那裡的。
有一天中午,白貓得意洋洋地拖回一隻八哥,那隻倒黴的鳥兒還不住地撲騰,也不知道貓是如何捉住它的。
更令人驚訝的是,有一回白貓把一條尺多長的蛇拖進堂屋,那蛇滿身一圈圈黑白相間條紋,依舊蠕蠕而動,還沒有完全死去。
也有一回,白貓闖了禍,壪子裡有一家人辦喜事,有人發現白貓把一條一兩斤重的白鰱魚拖到了窗臺上,魚倒是被他們追搶了下來,我家人卻結實捱了頓罵。
後來我們才發現謎底。
那年開春之後,母親有一次上到伙房樓上存放紅薯種的穀倉中取紅薯,意外發現那裡臥著一窩出生不久的小貓,有三隻,她並沒有動它們。
但不知何故,白貓還是發現了異常和危險,它把那幾只小貓一一轉移到了別處。
直到很久之後的一天,它突然帶著活蹦亂跳的三隻小貓,驕傲地出現在我家的堂屋。
我家的堂屋登時熱鬧起來,壪子裡其他的孩子也都跑來看新奇,爭著去逗弄那幾只毛絨絨的小傢伙,白貓蹲在附近悠閒地看,等著它們玩累了來吃奶。
接下來的日子,白貓更加忙碌,小貓的叫聲日漸洪亮乾脆。
入夏,大貓開始拒絕為三隻小貓餵奶了,它常常捉一隻半大老鼠回來,還是活的,放在堂屋中間,讓小貓自己玩弄。
那老鼠總是拼命逃跑,卻一次次遭到大貓攔截,僅有一次,我們親眼見到一隻老鼠成功鑽入牆腳的縫隙。
小貓逐漸長大,一些親戚早早就約定抱養。它們一個個被人取走,白貓一時煩躁而失落。
其中有一隻被壪前半里路的一戶人家要去,白貓就天天去這一家轉悠,有時還領了小貓回來,大約經歷了個多月,它才漸漸淡漠。
以後每年,白貓都要生養一窩小貓,小貓總是送人,我們只留下它。
隨著我們長大,我家的房間明顯不足,父親買下了生產隊加工組的幾間房屋,把其中一間作為他和我的臥室。
這個地方離我家老屋三四百米選,中間隔著一個竹園。每天晚上,我們去睡覺,白貓都一路跟著,狗有跟腳的習慣,人所共知,但我家的白貓怎樣養成這個習慣的,我們卻莫名其妙。
起先,出門不久,我們就聽到路邊草叢中有動物快速跑動的聲響,父親用電筒一照,我們就看到那隻貓雙眼在草叢中明亮著幽藍的光,尾巴高高豎起,顯示著倔強和調皮。
我和父親把它轟了回去,但不一會兒,他又出現在我們前面的道路中間,一副顧盼自雄的樣子,我們無奈,默許了它的行為。
到我們的房間後,它就自顧自地忙碌,我們也不管它。等第二天早上起床,我們就會發現它縮成一團,安靜地睡在我們腳頭的床角。
有時候我們還未醒來,它跑到我們頭邊,在我們的臉上嗅來嗅去,鬍鬚撓得我們癢癢的,甚至我們把它推過去,它又躡手躡腳走到我們脖子邊來,拿頭蹭我們的下巴,讓我們給它抓癢,實際上它是要我們起床,帶它回家吃早飯。
它喜歡跟腳還不止此。每個週末,我外出放牛,它竟然也跟我到山上,滿山崗嶺地鑽,總在我懷疑它迷路走丟的時候,它又自己出現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它似乎非常熟悉我的行動規律,有時候我覺得它簡直有意和我捉迷藏。
這隻貓帶給我們的快樂集中在中間幾年。越到後來,我們因為貓捱罵的事越多。
捱罵最多的事是,全壪的人都說我家的貓扒瓦,弄得他們的屋頂下雨天漏水,白貓也因此吃了大虧。
有一戶鄰居特別恨這隻貓,他們逮著一次機會,就勢把一杯滾燙的茶水往這隻貓身上潑。可憐這隻貓差點燙死,跑回來淚眼婆娑,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貓也會哭。
我們趕緊用冷水給它沖洗,它非常抗拒,後來這隻貓背上還是有巴掌大一塊毛全部落盡,它也很長時間不敢接觸外人。
有一次,它大概是誤食吃了毒藥的老鼠而中毒,氣息奄奄地走回來,癱倒在堂屋的地上。
我母親大驚失色,趕緊把它抱起來,用筷子撬開它的嘴巴,給它灌青油。它不停地嘔吐,也拒絕進食,匍匐在柴角落裡一動不動。
餓了幾天之後,才有氣無力地喝了一點母親為它熬的米粥。
它好不容易挺過了那一次,保住了一條命。
雖然這一次逃脫了人的毒手,但它最終還是沒有幸免。在我們養了它八年之後,它再次中毒,這一次,我們無力迴天。
第一次中毒之後一年多,這隻貓都一蹶不振。它很少再捉老鼠了,常常跳到我們懷裡懶洋洋地睡覺,不願意起來;屋裡沒人的時候,它常常鑽進灶裡,臥在火滅之後的餘燼中。
有兩次,母親沒提防,點火還差點燒著了它,虧它及時竄出,只燒掉了部分鬍鬚和頭上一小塊毛。
妹妹不忍心看老貓這樣狼狽,就每天給它洗澡,把它抱到門口曬太陽。
直到有一天,她放學回來,母親哽咽著告訴她貓兒已經死去,她頓時大哭,憤怒地詛咒下老鼠藥的人,但終於毫無辦法。
母親按照習俗把那隻貓高高地掛在大路邊的楊樹杈上,這隻貓就這樣走完了它在我家生活的那八年時光,終結了與我家的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