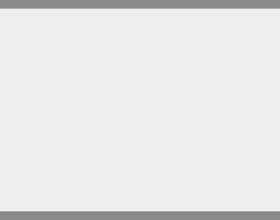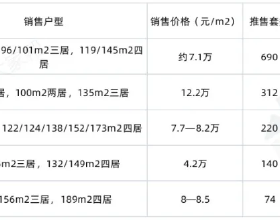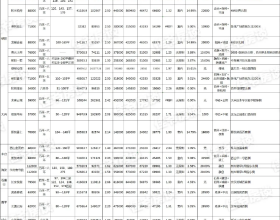蕭春雷
喜歡吃的蔬菜很多,但我最喜歡的,可能是蘿蔔。母親來廈住過一段時間,有次貪圖便宜,多買了幾斤蘿蔔,就切成蘿蔔條攤在砧板和鍋蓋上,拿去陽臺暴曬。沒想到這些蘿蔔乾鹽醃了兩天後,滋味極好,嚼起來生脆。我稱讚說:“做蘿蔔乾這麼簡單啊。蘿蔔真是天下最好的菜,清炒、燉湯、生醃,沒有不好吃的。”母親知道我的品位如此之低,十分欣慰,後來常醃蘿蔔乾給我。我呢,百吃不厭。
白蘿蔔不宜生吃。我網購過一箱山東濰縣綠蘿蔔,當成水果吃。綠蘿蔔有一層厚皮,辛辣;蘿蔔心也是綠的,脆而甜。我用水龍頭沖洗一下,連皮帶心咬進嘴裡,於是甘甜之中帶點熱辣。記起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句:“雪白蘆菔非蘆菔,吃來自是辣底玉;花葉蔓菁非蔓菁,吃來自是甜底冰。”蘆菔,即蘿蔔。蔓菁,即蕪菁。宋代的蔬菜,與我們今天的不同,當時恐怕還沒出現紅皮蘿蔔、綠皮蘿蔔呢。
我有點驚奇,蘿蔔如此美味,為什麼上古的文獻裡罕見提及?便去了解它的底細。原來,我國早就有蘿蔔了,只是早期記載較少,它又頻頻改名換姓。在《爾雅》註疏裡,蘿蔔的曾用名就有葖、雹葖、蘆萉、蘆菔、萊菔、溫菘、紫花菘等等,非專業人士,難免眼花繚亂。
農業考古學家說,我愛吃的這種大白蘿蔔名叫中國蘿蔔,雖然埃及、地中海沿岸更早出現蘿蔔,但是中國蘿蔔並非引進,而是起源於我國本土。《詩經》曰:“採葑採菲,無以下體。”其中“葑”指蕪菁(又稱蔓菁),“菲”就是蘿蔔。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稱:“蘆,蘆菔也。”清代學者段玉裁注:“今之蘿蔔也。”
漢唐時期,蘿蔔最常用的名字是蘆菔。很不幸,有史以來,蘆菔就籠罩在蕪菁的陰影下。蕪菁也是根類菜,有扁圓的肉質根,形態與口感都與蘿蔔相似,二者可以相互替代。既生瑜,何生亮?唐代以前,蕪菁無疑是最重要的根類菜,蘿蔔可有可無。北魏農書《齊民要術》在隆重介紹蔓菁(蕪菁)的栽培方法之後,簡單提了一句:“種菘、蘆菔法,與蔓菁同。”可見今日人們喜愛的白菜、蘿蔔,當年都是微不足道的配角。
宋代蘿蔔時來運轉,在我國南北地區廣泛種植,喜歡吃蘿蔔的名人很多。南宋晉江(今石獅市蚶江鎮)進士林洪寫過一本《山家清供》,介紹家常食品,就多處談到蘿蔔。他說永嘉學派大師葉適酷嗜蘿蔔,“每飲,適必索蘿菔,與皮生啖,乃快所欲”;詩人葉紹翁愛吃蘿蔔不亞於葉適,“然靖逸(葉紹翁)未老而發已皤,豈地黃之過歟?”他懷疑吃多了蘿蔔,讓葉紹翁未老白頭。
我們要知道,早期醫家對蘿蔔有一些誤解。唐孫思邈曾經告誡說:“(蘆菔)生不可與地黃同食,令人發白。”宋代筆記《國老談苑》記載,宋太宗想重用寇準,無奈寇準年紀太輕,難以服眾;寇準知道後,“遽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髭發皓白”。鬚髮皆白、貌似老成持重的寇準,如願以償,33歲就登上了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的寶座。這個故事強化了孫思邈的觀點,元代吳瑞《日用本草》還說:“白蘿蔔,久食之,發白。”
蘿蔔如此大的缺陷,為什麼還能取代蕪菁,成為首屈一指的根類菜?這是一個歷史之謎。我思考了很久,才恍然大悟,這可能與當時流行的另一個奇異觀念——蘿蔔能解面毒有關。蘇頌《本草圖經》明確指出:“萊菔,功同蕪菁……尤能制面毒。”該書還說了一個小故事:昔有婆羅門僧來到中土,看到人們吃麥面,大驚:“此大熱,何以食之?”接著他看到麵食中有蘿蔔,才放下心來,說全靠此物解毒,“自此相傳,食麵必啖蘆菔”。我們看到如今的蘭州拉麵裡,還要加點蘿蔔片,就是這種觀念的遺留。
麥面為什麼有毒?更早的時候人們吃麥面靠什麼解毒?這樣,我們就要簡單說說小麥的故事。小麥原產中東地區,約四千年前傳入我國北方,但中國人早期只知道粒食,做成麥飯,口感遠遜小米;漢代發明石磨後,才把小麥磨成麵粉,製作可口的饅頭、麵條,大約在唐代成為北方主食。麻煩的是,唐代醫藥學觀念比較落後,陳藏器等人還主張,小麥受四時之氣,兼有寒溫,“面熱麩冷”;粒食沒問題,一旦去除麩皮面食,就是傷身的大熱之物,稱為面毒。這成了小麥普及的最大問題。
面毒之說,其實是一個假問題;蘿蔔不妨充當一種偽解藥。因為《本草圖經》等宋代本草著作均宣稱找到了面毒的解方,小麥擺脫“毒”名,堂而皇之成為北方主要糧食作物,蘿蔔如影隨形,獲得了快速發展的機會。元代農學家王禎評論說:蕪菁與蘿蔔都是優秀的蔬菜作物,蕪菁多產於北方,蘿蔔則南北均獲其利,何況蘿蔔“尤宜生啖,能解面毒”。蕪菁與蘿蔔的兩千多年競爭史落幕,蘿蔔勝出,蕪菁黯然退場。
我在新疆吃過蕪菁,已經淪為一種地方食物,當地稱恰瑪古。細細比較,我還是更喜歡富含水分、鮮嫩生脆的蘿蔔。我想,蘿蔔取代蕪菁,當初可能是一種誤解,經過無數代農藝師的辛勤培育,最終被改良成完美的根菜,適合人類口味。歷史的奇妙在於,即使一個錯誤選擇,有時也能產生良好結果。
來源: 廈門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