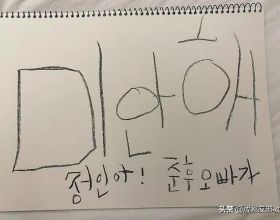1951年1月16日,志願軍第四十軍副軍長曾雍雅(1955年成為開國少將),正召集師團幹部研究下一階段作戰部署,突然接到志願軍總部打來的電話,要求曾雍雅立即前往志司所在地開會。
曾雍雅將軍明白這個會議可能非常重要,因此把手上的工作都放在一邊,只帶著一名警衛員和一名作戰參謀,連同一名司機,乘坐吉普車前往目的地。
雖然新年已過,但當時仍處在朝鮮最寒冷的時節。那一天的氣溫低至零下30攝氏度,到處覆蓋處厚厚的冰雪。
吉普車行駛在冰天雪地之地,根本開不了多快。雖然司機全神貫注、小心翼翼地駕駛,但車子面對這極度惡劣的路況仍很難駕馭,忽爾蹭到路旁的樹幹,忽爾險些滑下溝坎,讓司機緊張得渾身冒汗。
雖然作戰參謀和警衛員不時抱怨或提醒,但同坐在車中的曾雍雅似乎絲毫沒把路上發生的一切都放在心上,而是專注地思考著什麼問題,還不時拿出紙筆來寫上幾個字。
走到半路上,不遠處突然傳來一聲清脆的槍響,在空曠的山谷中迴盪。車上的人都明白,這槍聲是我軍防空哨發出的警報,說明空中出現了敵人的飛機。
果不其然,只過了一分多鐘,山谷中就突然鑽出兩架美軍的飛機。由於當時車子正行駛在一片開闊地,根本來不及隱蔽,很快就成為敵機追著掃射的目標。
成排成串的子彈掃了過來,把吉普車前後左右都打得塵土飛揚。
司機很有經驗,先是突然剎車吸引敵機,接著又突然加速往前衝,試圖鑽進前面的一片樹林。
這一招果然奏效了,敵機被耍得團團轉,投出的炸彈也偏離了位置。然而還是有一排子彈打中了車子頂棚,其中一顆正中警衛員的大腿,頓時血流不止。
另一架敵機氣瘋了,呼嘯著俯衝下來,司機只能加大油門繼續衝刺。
不巧的是,前面不遠處就是公路拐彎處,由於視線受阻,再加上車速過快、冰面溼滑,車子在轉彎時剎不住車了,竟一頭向山下栽去!
伴隨著警衛員和作戰參謀的驚呼聲,車子也在山坡上發起咣噹咣噹的碰撞聲,隨即翻滾著墜入200來米深的山谷裡!
車子動彈不了了,山谷裡一片寂靜,眾人半晌都沒有發起一點聲音。
過了十來分鐘,被磕暈過去的司機甦醒了過來,他顧不得血流滿面,急忙把副駕駛位的作戰參謀推醒。
還好兩人除了一些磕碰傷,身上並無大礙。他倆費勁地鑽進車子,發現警衛員從後座甩了出來,身旁一攤血跡。
幸運的是,警衛員只是昏迷了過去,很快被另外兩人救醒。
他睜開雙眼之後,顧不得傷口的疼痛,而是馬上環顧四周,當他發現找不到曾雍雅的身影,急得連連驚叫:“副軍長怎麼樣了?副軍長怎麼樣了?”
另外兩人也急切地呼喊著,到處尋找副軍長。
周圍視線可及處均沒有曾雍雅的身影,這讓三人無不心急如焚。他們都不敢想象,萬一副軍長有什麼三長兩短……
就在他們急得團團轉時,突然聽到一個洪亮的聲音從北面的山坡傳來:“我在這裡!”
毫無疑問,這正是曾雍雅那熟悉的聲音!司機和作戰參謀一邊高興地大喊著“副軍長、副軍長”,一邊向那邊奔去,就連受傷的警衛員也拼命想挪動自己的身子,確認一下副軍長是否安全。
司機和作戰參謀走到山坡前一看,眼前卻出現一幅頗為奇特的景象,只見曾雍雅正用雙手懸吊在一棵樹上,身子不停地晃動,看上去就像是在盪鞦韆!
二人也不知道副軍長在樹上蕩了多久的鞦韆。樹下面就是空蕩蕩的山谷,如果一不小心沒抓穩,曾雍雅就會滾到堆滿石塊的坡底去,就算不摔死也有可能受重傷。
兩名部下立即跑過去,幫助副軍長從樹上安全地回到地面上。
“你們都還好吧?警衛員怎麼樣?”曾雍雅急切地問。
“我們都好。警衛員受了點傷,但問題不大。”作戰參謀答道。
“副軍長,你怎麼爬到樹上去了?”司機問道。
“哈哈!”曾雍雅大笑道,“我呀,剛才變成了雜技演員!”
“雜技演員?”司機和作戰參謀一頭霧水。
“沒錯!車子把我甩出去的一剎那,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雙手竟然鬼使神差地一把摟住了山坡上那棵孤零零的樹,否則就要摔到山谷裡非死即傷了。”
作戰參謀仔細看了看那棵樹的位置,不禁感到後怕:“很神奇!副軍長真是福大命大,只要稍微有一點點偏差,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看來馬克思現在還不想見我,要讓我打敗美國佬再說!”
曾雍雅這番話,逗得眾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剛才遇險的不愉快情緒就這樣一掃而光。
多年以後,曾雍雅將軍寫文章回憶此事,曾感慨萬千:事後無論如何想不起來,自己在生死瞬間為什麼會做出那樣一個動作。幸虧這個無法解釋的自救動作,讓自己化險為夷,也造就了一段四人在朝鮮戰場同時遇險,卻全部安然無恙的奇特經歷。
只能說,當人處在非生即死的危急關頭,所迸發出來的能量之神奇是讓人不可思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