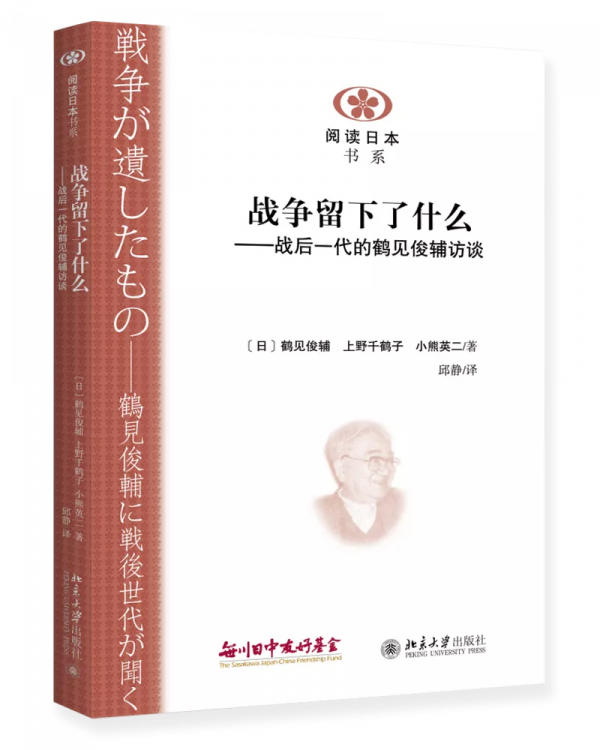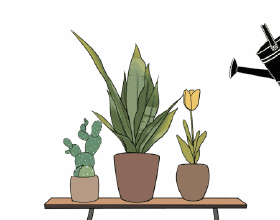《戰爭留下了什麼
——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
[日]鶴見俊輔
上野千鶴子 小熊英二著
邱靜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6月第一版
《戰爭留下了什麼——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是一本在漢語世界被低估的書。鶴見俊輔(Tsurumi Shunsuke,1922—2015)是把實用主義哲學介紹到日本的哲學家,系重要學術思想刊物《思想的科學》和“變節”(即日文“転向”)共同研究的核心成員。作為戰後進步知識人的代表、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鶴見提出的“十五年戰爭”說,早已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學術界共識;其主張的“超國家市民”和“加害的自覺”等理念,與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戰歿者追悼”及“被害的痛苦”等日本社會面對歷史問題的主流姿態並不矛盾,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發展形態”(小熊英二語)。
鶴見俊輔(1922年6月25日—2015年7月20日),日本哲學家、評論家、社會運動家、大眾文化研究者
耄耋之年,鶴見“空出了整整三天時間”(“對於我的餘生而言可是很長時間了”),與兩位戰後一代學者上野千鶴子和小熊英二對談,話題廣泛,且不乏深度。聯想到中文版出版僅一個月後,鶴見便駕鶴西去的事實,這本書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鶴見一生的回顧。
《思想·山水·人物》,[日]鶴見祐輔著,魯迅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鶴見作為自由主義學者,除了其思想主張之外,有兩點常被提及:一是家世,二是經歷,都堪稱獨特。1922年6月25日,鶴見俊輔出生於東京市麻布區,外祖父是明治期著名政治家,先後擔任臺灣總督、滿鐵總裁和東京市長的後藤新平。當時鶴見與父母和姐姐和子,都住在外祖父的大宅邸中,而那個老宅後來成了中國大使館。鶴見的父親鶴見祐輔,從舊制一高畢業,考入東大法學部,是公認的自由主義者和親美派,當過眾議院議員,戰前就是暢銷書作家。1928年,魯迅曾譯介過他的一本著作《思想·山水·人物》。可到了戰時,他轉而支援戰爭,擔任過大政翼贊會的總務。戰後,受到佔領軍的追究,遭公職追放。但後來又復歸政界,在鳩山一郎內閣中擔任厚生大臣。正是父親的這種反覆轉向的“變節”經歷,成了鶴見戰後“變節”研究的原點。
鶴見俊輔(左一)幼時的全家福。他的姐姐鶴見和子(右一)亦是日本著名社會學家
母親愛子是後藤新平的長女,從小在等級森嚴的大家庭中長大,也試圖以嚴苛的家規來管教兒子。但俊輔與生俱來的叛逆性格,卻每每令嚴母的苦肉計落空。俊輔回憶:
我媽媽在我十五歲去美國留學以前總是體罰我,從我兩三歲的時候就開始了。這對於小孩子來說是極其痛苦難當的。……媽媽發現我偷吃了華夫餅,就抓住我打我,說“你是個壞孩子,真是對不起先人。我把你殺掉自己也死了算了”。
所以到後來,俊輔徹底放飛自我、“愛誰誰”了:十二三歲,就開始泡酒吧,偷東西,跟女人發生關係,且有五次自殺未遂的體驗,“我當時的理想就是在酒吧喝下足以致命的安眠藥,撲通一下倒下死了,把屍體亮在我媽媽面前”。不過,雖然在課業上無可救藥,但俊輔從小酷愛讀書,上小學時,便讀過野村芳兵衛的文章,知道克魯泡特金和無政府主義。
1939年,鶴見俊輔進入哈佛時拍攝的入學紀念照
十五歲時,父親實在看不下去,就送他到美國去留學——那是1938年。一起赴美的,還有姐姐和子。“去了美國以後,就算喝了安眠藥撲通一下倒地也沒意義了。”於是,每天背五十個單詞,全憑苦學,以日本小學畢業的學歷考進了哈佛大學,學習語言學和哲學。同學中,有終生的摯友、前輩學人都留重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FBI關進移民局拘留所。在拘留所的馬桶上完成了畢業論文,獲得教授會的一致透過。後在被遣送回國的交換船上,同船的都留重人對他說:“今早的《紐約時報》上登出來了,你畢業了。”
雖然蹲拘留所,“我也沒有受到拷問”,而且“我覺得這裡是有民主主義的”,但當美日間開通交換船後,他還是選擇了回國。1942年6月11日,乘坐交換船“格里普斯霍爾姆”號,從紐約港起航回國,在海上迎來了二十歲生日。以鶴見的智慧,他當然知道日本必戰敗。但明知戰敗,還是要回去,其內心想法要多真實有多真實:
日本已經快要戰敗了。那在戰敗的時候,我要呆在戰敗的一方那裡……或者說,不想呆在戰勝的一方那裡。關於這場戰爭,不管有多麼覺得美國這方是對的,一想到自己跟著勝利者美國、說著英語回到日本的樣子,就覺得無法忍受。
竊以為,在解讀鶴見俊輔的生平及思想時,理解他這種決不迎合強勢,而永遠站在弱勢一方的反精英主義姿態,確是一把鑰匙。這不能不說與其自身幼少期的經歷,特別是其父的“鏡鑑”有關。這種“鏡鑑”,用俊輔的去學術化表述,叫做“第一病”:
我父親原本就是憑著學習上去的。他家境貧寒,拼命學習,一直拿到了一高的第一名。後來就跟後藤新平的女兒結了婚。因為是這樣靠學習去拿第一的人,所以除了當第一之外就沒有其它的追求了。就是這種有“第一病”的知識分子當了政治家、官僚,運作著日本。
在兒子的眼裡,老爹鶴見祐輔病得不輕。以一高第一的成績上東大。東大畢業,參加高文(高等文官)考試時屈居第二,痛失“銀懷錶”(只授予首席的獎品),這件事他始終不提。戰前,作為自由派文人,崇尚英美,屢屢赴美演講,相當拉風。戰時,國內空氣驟然收緊,遂搖身一變,甚至做起了翼贊會高官。戰後,被解除追放,實現政界復歸,鳩山一郎內閣成立後,祐輔出任厚生大臣,“當了大臣也算是一種滿足了吧,不過說實在的,我父親當了大臣就只做過一件事:他說大臣的房間太小了,給換了個大的……除此之外他什麼也沒做”。俊輔不禁“酷評”道:
日本的政治家大部分都是這樣,不是嗎?說想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但當了以後要做什麼呢,誰也說不出來。我看了就想起我父親(笑)。就只不過是想當第一嘛。
在鶴見看來,“麥克阿瑟很聰明,把天皇、文部省、東大這明治國家的三大根基原樣保留下來,沒有改變培養領導者的方法。這在統治和經濟方面是非常有效的”。但另一方面,社會精英“第一病”的病灶並未得到根治。而“一旦形成這種‘第一病’的學校制度,出現知識分子的集體‘變節’現象也就是當然的事了。因為都是意識不到自己變節的變節,就只是總想要當第一而已”。鶴見從自己的戰爭體驗中發現,“大學畢業的人輕易地變節,沒什麼學歷的人卻有獨立的思考。像渡邊清、加太浩二他們都只上過小學,卻發展出了自己的思想”。

鶴見俊輔視《共同研究 轉向》(三卷本,改訂增補版,平凡社1978年2月版)為畢生最重要的學術工作
鶴見平生最重要的學術貢獻之一,是對“變節”的研究。作為研究成果,煌煌三大卷(即《變節》上、中、下),總共賣出了十萬套。其目光之毒,診斷之準,在戰後社會之廣受歡迎,由此可見一斑。有一次,鶴見在週刊雜誌上看到對電影明星三國連太郎的專訪,發現他的書架上也放著《變節》三卷本。可以說,沒有對這種“第一病”的發現,便沒有“變節”研究。鶴見在自己的另一本訪談錄《期待與回憶》中坦言,“《變節》三卷,實際上是對我父親的感想”。
2007年8月4日,小田實的追悼會結束後,約500人舉著小田實的遺影,高唱著60年代的反戰歌曲在街上游行
正是出於對“第一病”的反動,他對諸如丸山真男、吉本隆明、小田實和韓國行動派知識人金芝河等“一根筋”式的思想者、活動家充滿敬意。當小熊英二以吉本隆明為例,指出鶴見對那種型別的人的肯定,其實“是把他們當作那些既能幹、又會做人的優等生的對立面”的時候,鶴見坦言:“是的。反正有‘第一病’的人不行。”
反正鶴見就是死活容不下首鼠兩端的“第一病”患。這種“執念”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他作為鐵桿的自由主義思想家、護憲論者,卻反而能見容於一些“黑社會式的傢伙”,而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他曾幫助過新左翼活動家中核派幹部北小路敏,儘管他並不贊同中核派的理論綱領。同樣的,他對三島由紀夫也抱有好感:
他以自殺證明了自己並不只是個想要出風頭的人。這就是我的感想。最後就是覺得那是個不錯的傢伙。切腹自殺可不是隻為了出風頭的人能夠做到的。我從少年時代起大概有五次自殺未遂,但沒有真正100%確定地自殺過。……但三島超出了這個範圍,從想死到死去,他表現實行了。這在只是自殺未遂的我看來,就會覺得“比我強,有始有終地做到了。了不起的傢伙。不錯的傢伙啊”(笑)。
說起來,三島在後期主動跟我接近。但我都沒有回應,也沒去過三島家。不過我覺得他的《春子》《喜悅之琴》,還有《近代能樂集》都非常好。
但我為什麼對三島有好感,日本的報紙雜誌是不會理解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關係好,一定不會有好事情。是會被利用的吧。所以我就覺得我們沒那麼密切挺好的。
身處劍拔弩張的“保(守)革(新)”對立意識形態磁力場的中心,鶴見當然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正確”的,所以他不吱聲。三島自戕時,學生從電視上看到訊息,立馬飛奔到鶴見家通知老師。鶴見知道媒體會打電話來採訪,於是馬上帶孩子出門,“我家附近有個北野神社,那天正好是緣日,有各種活動。我就跟孩子一起吃點心什麼的,過得很愉快。這樣在附近到處逛逛,就不會被記者逮住問‘您怎麼看’了不是嗎。就這麼過了一天,等日報的截稿日期過了,也就不會有人來採訪了”。
不過,儘管鶴見在內心對三島抱有好感,卻並沒有照單全收,拋卻政治立場的溫差不論,有一點是鶴見無論如何難以同調的,那就是“美化貴族”:
我從小就生活在被叫做貴族的人們中間,不管是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還是從統計上來看,日本的貴族當中有很多人都是很不堪的。只偶爾有些零零星星的例外。但三島卻不這麼認為。他這一點我覺得不咋地。
劉檸:作家,譯者。北京人。大學時代放浪東瀛,後服務日企有年。獨立後,碼字療飢,賣文買書。日本博物館、美術館、文豪故居,欄杆拍遍。先後在兩岸三地出版著譯十餘種。
編輯:陳蘊青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