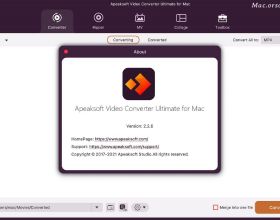文/盧明
鄆城博物館藏有明代書畫名家文徵明的一幅行書軸。文家與鄆城的關聯不僅在於這幅書軸,而且在於文徵明的叔叔文森曾是鄆城知縣。那麼,文徵明、書軸及文森,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文徵明,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大名鼎鼎。他是明代畫家、書法家、文學家。因官至翰林待詔,故稱“文待詔”,其文化造詣極為全面,詩、文、書、畫無一不精,人稱“四絕”全才。在畫史上,文徵明與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稱“明四家”(吳門四家)。在詩文上,文徵明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 並稱“吳中四才子。
鄆州博物館收藏的文徵明行書作品,是幅立軸,尺幅很大,系國家二級文物。據說,如果不是有個“每”字缺損,本可以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的。書軸的內容是文徵明本人的一首七律《內直有感》:
天上樓臺白玉堂,白頭來作秘書郎。
退朝每傍花枝入,儤直遙聞刻漏長。
鈴索蕭閒青瑣靜,詞頭爛漫紫泥香。
野人不識瀛洲樂,清夢依然在故鄉。
這首詩,文徵明在其他作品上也曾不止一次寫過,多與另外的詩一起寫在同一幅上。鄆城這一幅,卻是單獨寫的這一首詩。尾部只署“徵明”二字,是個窮款,並無年月背景之類的內容。
內行的專家,知道文徵明的這幅行書軸在鄆城。鄆城的文化人,更是以縣內藏有這幅名家的作品而深感自豪。一般人不一定知道的是,文徵明的親叔叔文森,曾是鄆城的知縣。
文森,熟悉鄆城歷史的學者一般會留意到,是鄆城明代著名的官員。最直接的資料來源,便是明崇禎《鄆城縣誌》和清光緒《鄆城縣誌》的記載。崇禎版《鄆城縣誌》載,“文森,直隸長洲縣人,由進士弘治五年任。”那麼,文森在鄆城幹了幾年知縣呢?在文森之後任職的是徐銳。縣誌載:“徐銳,直隸永年縣人,由進士弘治八年任。”也就是說,文森在鄆城任知的時間為弘治五年至弘治八年,大致三年的時間。
文森不是一般的縣官,而是個很有政聲的人。光緒《鄆城縣誌》把他列入《名宦》欄目,載:“文森,廉能兼著,威惠並行。擢御史,有聲。仕至南贛巡撫,邑人至今德之,主事龍霓有《去思碑記》。”龍霓的《邑侯文公去思碑記》全文收入崇禎、光緒兩版《鄆城縣誌》,文章記述了文森在鄆城的政績,表達了鄆城人民對這位知縣的充分肯定,“鄆人德之,刻石以示不忘”。看得出,他是個精明能幹的官員,抑強懲奸,減免賦稅,消除百姓不合理負擔,征剿盜寇,治理河患,成果顯著。他離開鄆城,是因為升職。《去思碑》記得清楚:“去此而為御史”。文森在鄆城的政績,不只鄆城的史乘有記,他的家鄉吳縣也有記述。民國《吳縣誌》載:文森“內艱歸,復補鄆城縣。縣有德府莊田,官校因而虐民。森曾於監司為徵取貯縣,俾官校自取,民得無憂。慶雲與鄆,皆多盜。森,所至置民兵,分曹巡捕而高其賞格,盜發境內,無脫者。”
文森關注民生,體恤民情,是一貫的。不只在鄆城,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來鄆城之前,他在慶雲任知縣。據民國《吳縣誌》記載,文森“成化定為進士,授慶雲知縣,歲大旱,上疏乞免田租。戶部以無撫按奏,不報。再疏,語加切,卒免其半。一切力役皆以民飢力爭於上官,得免。境故高低、無渠堰,民視雨澤以舊。遇旱則束手待槁。森,教民鑿塘蓄水以備旱。滄州每役縣民,民苦之。森曰:縣雖隸州,然各有分土,州安得懮(憂)縣。民白於監司,罷之。”
文森升職為御史以後的情況,《吳縣誌》也有記載,這裡引用過來,以便讀者對他有個較為全面的瞭解:“召拜御史。會吏部尚書缺,大臣有夤緣求進者,森疏論之,因舉劉大夏、周經,或以為非所宜言,下詔獄。上知其直,笞而不問。正德中,逆(劉)瑾用事例,致仕。瑾誅,起故官,升南京太僕寺少卿。十一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看來,文森還是一個勇於與宦官鬥爭的大臣。
最關鍵的環節,就是何以見得文森就是文徵明的叔父?這個問題不難解答,因為我們有足夠的資料加以證明。《明史·文徵明傳》說得清楚:“文徵明,長洲人……別號衡山。父林,溫州知府。叔父森,右僉都御史。”民國《吳縣誌·文林傳》載:“文林,字宗儒,其先出湖廣武昌,祖惠始家長洲,父洪字公大”。民國十八年出版的《蘇州文氏族譜續集》記載的蘇州世系表可知,文家一世為文惠,二世為文洪、文濟。文洪有三子:文林、文森、文彬為三世。文林有三子:文奎、文徵明、文室為四世。
講明文徵明與文森的親緣關係,並不是說文徵明的行書軸就是在鄆城創作的,或是文森帶來的。這幅字與鄆城結緣,應當另有途徑。但是,如果我們將思路再放寬些,將膽子再放大點,便可以這樣推測,或許文徵明就到鄆城來過,或許他也在鄆城創作過書畫作品。
有資料顯示,文森與文徵明雖是叔侄關係,但他們的年齡相差很小,相處相通的地方很多。兩個關係相近、性情相投的親人,叔叔在鄆城做主官,侄兒到鄆城來看望看望,住上幾天,這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不排除文徵明到鄆城來過的可能性。
雖然歷史遠去,但先賢們留下的身影,早已化作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對於鄆城來講,能存有數百年前文徵明的作品,能有文徵明的叔叔在鄆城當過知縣,這已經很值得一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