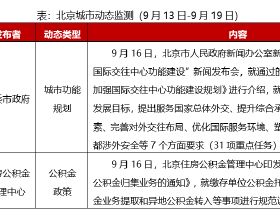齊白石 《牡丹》103.5×34cm 紙本設色 1955年 北京畫院藏
不似之似
對於“不似之似”,齊白石的說法是“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本質是中國畫物件形、形似的超越。現實中蝦的眼睛是圓點,而在齊白石的畫中,蝦的眼睛變成兩個“直道”。他不是在畫蝦的眼睛,而是在畫蝦遊動時眼睛在閃光的感覺,這樣顯得更生動更傳神。你說它不像,實際更像。山水畫也是,宋代畫家范寬的《溪山行旅圖》,是在山腳下描繪的,但山上的樹林卻描繪得非常清楚,在山下根本看不見,這需要提升視點才能看到。可見,范寬描繪這幅畫並沒有固定在一個立足點,而是不斷地移動視點,當然不是實際的移動,是想象中的移動。這幅畫中所描繪的景象在真實生活中不可能存在,跟實際景象拍攝出來的圖片絕對不一樣。似與不似之間,還可以表現為“語帶雙關”,清初畫家梅翀《松芝圖》中的松樹,既像松樹又像山,但又都不完全像。如果看作松樹,則松枝是一邊倒的;如果看作一座山,“松枝”則是山的脈絡紋理,畫家是用視覺的“語帶雙關”的形式,來表達壽比南山不老松的祝壽美意。這是一個特例,此類作品不太多,但對我們很有啟發意義。
舍形悅影
中國畫特點之一是舍形而悅影,就是從投影的啟示來把握物件。元代畫家顧安擅長畫竹,說是得自唐代畫家蕭悅觀牆上竹影而得畫竹的啟發。歷史上有很多記載都是在畫影子,而不是在畫形。比如陳淳《白陽集 墨牡丹詩序》中說:“甲午春日,戲作墨本數種。每種戲題絕句,以影索形,模糊到底耳。”他講的就是透過形來找影子,再透過影子來把握形,要模糊地把握物件。明代畫家徐渭在《徐文長集 畫竹》也說道:“萬物貴取影,寫竹更宜然。”清代鄭燮有一段《板橋題畫》非常生動:“餘家有茅屋兩間,南面種竹,夏日新篁初放,綠蔭照人,買一小榻其中,甚涼適也。秋冬之際,取圍屏骨子,斷去兩頭,橫安以為窗欞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風和日暖,涼蠅觸窗紙上咚咚作小鼓聲,於時一片竹影零亂,豈非天然圖畫乎?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於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20世紀以來,我們對古代傳統畫作的認識有些是片面的,中國傳統有時候被遮蔽,所以我們在力求建立傳承體系時,有時候還要挖掘傳承。
程式語彙
中國畫的另一個特點是程式化。中國畫的影象是程式化的,是對應物象的符號,不是如實描寫。聞一多先生曾講過,中國畫是提示性的,透過意會就能達到目的,比如畫竹從程式入手,程式用活了,修改程式變成自己的語彙,就有了自己的特點。中國畫程式的形成,一方面是對應物象的圖式,另一方面是按照一定的程式來操作。
奧理冥造
中國畫還有一個特點是奧理冥造——大膽的想象與幻化。奧理冥造為北宋沈括所言,就是說要大膽的想象與幻化。齊白石《自秤圖》中,一隻小老鼠跳到一杆秤的秤鉤上,似乎想稱稱自己的重量,奇怪的是,上面的秤繩不知由誰來提,秤砣不知由誰挪動使之平衡。畫中的影象其實是齊白石的想象,透過想象來調侃小老鼠:你這隻小老鼠偷油吃,偷糧食吃,不要自以為有什麼了不起的,你到底有多大分量,不妨自己來稱一稱。所畫內容在現實中並不存在。再說一個大膽想象幻化的例子。清代黃慎的《瓜月圖》中,瓜藤上的西瓜是切好的一牙西瓜,旁邊題詩:“剖開天上三秋月,飛作人間六月霜。”說的是,夏天天氣很熱,晚上如果剖開一個像月亮一樣的西瓜,吃到嘴裡一定會很涼快。再看八大山人的《魚鳥圖》,說是鳥,但有魚的尾巴;說是魚,又有鳥的翅膀。對此可以有兩種解讀。一是八大山人作為明宗室後代,明代滅亡對他來說可謂國破家亡,清初又實行極端民族政策,“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八大山人這樣的前朝王孫,只能出家做和尚,意為不留頭髮,並不是承認清代政權。從這個角度理解,他經歷了跌宕起伏的身世悲劇,內心非常悲涼,如果想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這句古詩,會感到海再闊,魚也沒法躍;天再高,鳥也沒法飛。再一種則從大的禪僧身份來索解,意在不執著一物:魚和鳥是可以轉化的,這件作品的題跋就是引用了莊子的《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裡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裡也。”這種大膽的想象,也並非憑空而來,而是有文獻典籍的依據。
彷彿有聲
中國畫還講究“彷彿有聲”,即視覺的轉化。齊白石的《蛙聲十里出山泉》,透過畫水裡游來的蝌蚪,表現遠處的蛙叫,用視覺形象表現聽覺的感受。這是一幅作家與畫家合作的作品,是作家老舍先生命題請齊白石所畫,老舍寫信說:“蛙聲十里出山泉,查初白句。蝌蚪四五,隨水搖曳,無蛙而蛙聲可想矣。”齊白石根據老舍的意思畫了這幅畫。中國畫不僅要表現畫外意、象外意,還要表現視覺以外的其他感覺。俞成《螢雪叢說》言,“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倫選幾許人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無以見得親切。一名畫者,恪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馬蹄香出也。”這位畫家透過視覺表現了嗅覺。錢鍾書在《通感》中說道:“在日常經驗裡,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口、鼻、身各個官能的領域可以不分界限。顏色似乎有溫度,聲音似乎會有形象,冷暖似乎會有感覺,氣味似乎會有體質。”近年來,有學者就指出中國詩歌講究通感,我覺得在現代藝術創作中也可以發揮通感的作用。這也是一個好的傳統。
比興如詩
中國畫追求詩歌一樣的比興手段,重視儒家的比德思想。五代荊浩就在《筆法記》中以儒家“比德”的思想賦予松樹人文精神。宋代《宣和畫譜花鳥敘論》主張,透過表現詩人一樣的感受(“寓興”)來寄託情懷,與觀者進行精神的交流,所謂:“所以繪事之妙,多寓興於此,與詩人相表裡焉。故花之於牡丹芍藥,禽之於鸞鳳孔翠,必使之富貴;而松竹梅菊,鷗鷺雁鶩,必見之幽閒;至於鶴之軒昂,鷹隼之擊搏,楊柳梧桐之扶疏風流,喬松古柏之歲寒磊落,展張於圖繪有以興起人意者,率能移精神遐想,如登臨覽物之有得也。”雖然混同了“象徵”和“寓興”,但揭示了兩種表現精神世界的途徑。南宋畫家陳居中的《四羊圖》中,嬉戲玩耍的兩隻小羊活潑可愛,母羊慈愛地欣賞著兩個孩子的玩耍,公羊則站在上面顯現出比較嚴肅的樣子。這幅畫充滿了親子之愛,是在畫感受,也是擬人化的。
以書入畫
以上的“寓興”主要是中國畫跟詩歌的密切關係,除此之外,傳統中國畫與中國書法的關係也很密切。南宋畫家馬遠的《水圖》中,黃河的奔騰澎湃、長江的煙波浩渺,都是靠線條表現出來的。靠線條輕重、虛實、剛柔、組合,再稍微著墨就會把物件惟妙惟肖地表現出來。這跟毛筆關係密切。元代趙孟頫《秀石疏林圖》是其非常著名的作品,畫後題詩:“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須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方知書畫本來同。”講的是筆跡形態與物象的結合,要畫石頭就用飛白來畫,表現石頭歷經千年風霜的滄桑;要表現樹木的生命力就用鐘鼎文,線條是很圓潤的;而畫竹枝竹葉“永字八法”都能用上。書法入畫,對線條、點畫形成了一種歷史積澱,積澱了質量上的要求,黃賓虹論筆墨講“平如錐畫沙”、“一波三折”、“屋漏痕”,都是對點畫質量的基本要求,更能體現“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天地之心”。再說墨,可以是潑墨,一氣呵成,也可以是破墨,先用淡墨再著濃墨,也可以先著墨再用水,形成不同的形態。黃賓虹《九子山》圖,就是用積墨,一層一層地著墨,線條是編織的、不重疊,黑中透亮。筆墨除狀物外,還可以寫心,讓點線形成一種節奏或韻律,跟人的性格及當時的感情狀態相對應。
詩書畫印結合
中國畫講究詩書畫印的結合,一幅畫其實已是一種綜合藝術,形成了相關藝術的綜合與互動。清代畫家鄭板橋的《衙齋圖》,就透過與書法題跋的結合體現了作者的仁心。他在衙門中聽到風吹竹子聲,以為是老百姓的啼飢號寒,就透過畫老竹子和小竹子的關係,將畫作跟題跋結合,表現了親民之官關心百姓疾苦的思想感情。清代畫家李方膺的《鍾馗圖》,創作於他做官丁憂回家期間,家鄉遇到天災,他很有感觸,便畫了這幅《鍾馗圖》,在詩畫結合中表達了憤世嫉俗的感情。題中文字是“節近端陽大雨風,登場二麥臥泥中。鍾馗尚有閒錢用,到底人窮鬼不窮!”畫的是鍾馗撐著破雨傘,看似很窮,可腰裡卻彆著一串銅錢。由此可見,作者並沒有按傳統將鍾馗畫作正義的正面形象,而是畫成了一個裝成清官的貪官。詩書畫印的結合除可以拓展意境,使畫外意和畫內表現密切結合起來,生髮延伸畫境之外,還影響了畫面構成,李方膺《游魚》中,如果沒有右側的柱式大字題字,畫作所表現的氣勢就會有所削弱。
來源:愛小說的小螃蟹
宣告:本文已註明轉載出處,如有侵權請聯絡我們刪除!聯絡郵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