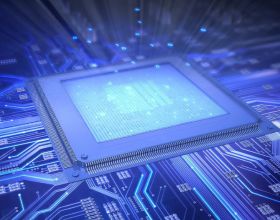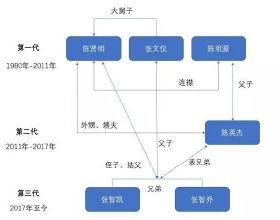記不清是六七還是六八年的事了。
星期一的晚上,娘把正在奶奶屋裡看《野火春風斗古城》的我叫回房間(奶奶是吃國家糧的長沙戶口,點燈的煤油票充足,她一個人睡有些害怕,故每晚燈是不熄的)附我耳旁悄悄說道:“喜伢,明天早些起來去砍柴,天氣好,下雨冒得柴火煮豬潲了哩!”
“嗯!”
我點了點頭,合上書放床頭到灶屋的熅壇臽了瓢熱水冼完臉、腳就趕緊睡下了,心裡一直凝惑:娘麼夾(湘鄉方言為什麼)要這般神秘呢……?一家八口的吃喝拉撒讓她原本靚麗的瓜子臉過早地刻上了格外顯眼的幾道皺紋,加上她心中只有丈夫兒女,惟獨沒有她自己,每逢家裡來客人做個葷菜,她怎是熱心地夾起來敬到客人飯碗裡,口裡不停地招呼客人:“ⅹⅹ,別客氣,吃菜咯!我廚藝不大好,可也煮熟了的。”自己卻從不伸筷子。想著想著就迷迷糊糊進了夢鄉……。
突然,耳朵好象被麼子東西掛住了一樣把我從沉睡中驚醒,揉揉朦朧的雙眼,娘站在床邊對我做著小心起床的手勢,我一骨碌爬起來輕手輕腳走出了廂房,廚房裡赫然看見娘早就預備好了的毛鐮(砍柴的7字形的刀)、箢箕,娘倆悄悄拿上就出了門。
農曆三月的凌晨,山凹裡的空氣中一層薄霧輕飄飄地裹住山裡的每戶人家,彷彿似慈愛的母親把自己的孩子攬在懷裡,生怕被傷害到,它是那麼地公平……。走到屋後的大文山腳下,晶瑩的露珠從雜草上蹦下來吻溼了我的布鞋,腳感覺有一絲絲涼意。
“六嬸,您來啦!還有喜伢呀?”
堂嫂常輝姐從草叢中站起來小聲招呼道。
睜著圓圓眼睛的滿月好奇地浮在偏西的湛藍湛藍的天幕下注視著我們仨,銀光穿過山嵐中飄蕩的薄霧瀉在山面的泥土上,能讓我們依稀看得清上山的窄道不至於讓蛇咬傷。
約摸半小時工夫,三人氣喘噓噓爬到了大文山倉頂,汗水從體內湧出來亳不留情浸溼了單衣。“喜伢,你座這兒等著,別亂跑啊!“
娘叮嚀道。轉身與常輝姐姐小心翼翼貓腰鑽進了山嶺另一邊屬於燕子衝的幽暗的柴叢深處。我找了塊平坦的青石板座著,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娘啊!原來您是怕走夜路叫兒子來打伴啊!生產隊分的那點柴火哪夠一家人做飯和煮豬潲燒呀!唉!您麼夾就生活在這麼貧瘠的小山村呢?真苦了您呀!一股愧疚、無奈、無助之情在體內湧動,想去幫忙又沒工具……。
天茫茫亮時娘和常輝姐從樹林中蠕動著瘦弱的身板揹負一大梱箭桿柴爬上了侖頂。
“喜伢!”
聲音是從娘低著頭的喉嚨裡擠出來的。
“哎!我在這哩!”
“快走,跟在我身後。”
我心中當然明白,這是“偷”了另外一個公社的柴能磨蹭?麻利躍起跟著娘下山。
俗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揹著百兒幾十斤重的凌亂溼柴下山更難!深一腳淺一腳下到大文山雞翅膀處時,我攥在手中的柴尖尖剎那間脫落,柴捆骨碌碌往下滾,我一驚,坡太陡,娘腳下一滑栽跟頭了,腚重重地頓在地上。
“娘……!”
我悲哭的喊聲瞬間從喉嚨迸出,躍步扶起她,仔細端詳著她瘦弱的身軀。祖宗庇佑,幸而冒摔傷。
”走,趕緊回家。”
娘倆用手往後撐著山地滑下坡找到滾到了不遠處的那捆箭桿柴,費了好大的勁才又把它弄到了娘那單瘦的瘠樑上扛起它繼續往家趕。
到家時天差不多亮了,娘卸下了柴,長長地圩了一口氣。
”快去吃飯好上學。”
娘用本就滴著水的衣袖抹了下臉上的熱汗,手指尖把留海上零亂的烏髮理了理,渾身通透的單薄衣裳貼緊身體,慢悠悠,輕渺渺的熱氣象蒸籠一樣從她的烏髮裡鑽出漸漸地與薄霧融合了在一起……。
”哦!”
我一邊應承一邊轉身進屋在爐膛裡打了盆溫水放冼臉架上給娘準備冼臉。
上學的路上暗暗發誓:一定要把書讀好跳出農門,讓娘不再這麼辛勞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