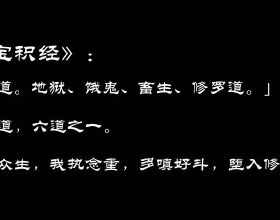《孟子·萬章》說:“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在孟夫子看來,伯夷、伊尹和柳下惠雖然都是聖人,但他們各居一偏、獨奏一音,只有孔子才集前聖之所成,透過編纂《六經》來“並奏八音”,既能“清”又能“任”還能“和”。與此同時,孔子又是儒學的開創者,是百家爭鳴的先驅。對於前代學術來說,孔子是“終條理者”;對於儒學來說,孔子又是“始條理者”,所以孟子用“金聲玉振”來讚譽他的學術地位——一首曲子總是以“金聲”為開頭,用“玉振”來收尾,作為總結者與開創者,孔子能夠“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所以獲得了“集大成者”的稱號。
究竟什麼樣的人才是“集大成者”?
後人不理解孟子的原意,而是把“集大成者”歪解成了總結者。例如有些人說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集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以及慎到的“勢”;又有人說朱熹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道學思想來自二程和張載、易學理論又兼取邵雍,在各家的基礎上編出了《四書章句集註》這樣的整合之物;還有人說王陽明是心學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陸九淵只是偶爾談到“宇宙即吾心”,楊簡也只是說“天地,我之天地”,只有陽明用“知行合一”與“致良知”來總結了心學的理論,使這種思想系統化。
然而,韓非、朱熹與王陽明都並未兼具開創者的身份。在韓非之後,法家就逐漸衰落了,朱熹也是理學由盛轉衰的轉折點,王陽明則是心學最後的輝煌。韓非子的核心思想不過是重新闡述申商之論,朱熹的“理氣二元論”也只是調和二程與張載的矛盾,至於王陽明,他的學說基本都建立在《大學》與《孟子》之上,不過是用另一種術語來重新闡述“正心誠意”和“萬物皆備於我”的道理而已。
真正的集大成者必然是這樣的人——他既是前代學術的總結者,又是後代學術的開創者;既是以往思想的清算者,又是新思想、新方法的建立者。比如西方的黑格爾與明末的王夫之就是這樣的人。
為什麼說王夫之是“集大成者”?
黑格爾是西方近代哲學的集大成者,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因為在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中,他將前人的思想原則化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概念,納入自己的體系裡。例如笛卡爾的“廣延與思想”在黑格爾那裡叫做“存在與思維”;康德的“二律背反”在《邏輯學》中被豐富成“矛盾”;“絕對精神”這個概念其實就是對斯賓諾莎的“實體”與費希特的“自我”進行統一和揚棄。
作為一名總結者,黑格爾的著作總結了當時各門學術所取得的成就。其中,《邏輯學》對應傳統的形而上學;《自然哲學》包含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精神哲學》相當於社會科學;此外他還有《歷史哲學》、《美學》、《宗教哲學》等各領域的專著,幾乎涉及所有的學科。
與此同時,黑格爾還是一名開創者,他用可知論來對抗當時廣為流行的休謨-康德不可知論;他批判了17世紀的形而上學和18世紀的機械論,提出辯證法的邏輯,將矛盾視為發展的動力,並且自覺在自然界中尋找例證。所以說,黑格爾既是理性主義的總結者又是辯證法思維的開創者。
明末三大家之中,黃宗羲是心學的總結者,他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都是總結性的著作;顧炎武則是樸學的開創者,他拋開宋明理學,“務當世之務”,開一代之學風;王夫之則類似於黑格爾,既是總結者又是開創者,他有句名言說:“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
三十三歲那年,王夫之抗清失敗,“遂決計歸隱”,當時他正值壯年,滿腹經史,卻因遭遇國變,立志不仕二姓,所以作為讀書人,他的人生目標已經不可能實現了。苦悶之下,王夫之只得埋首故紙堆,希望透過清算傳統哲學來找到新的出路,所以才自稱“六經責我開生面”——也就是說他要從“六經”中找出“生面”來,要發明新思想、做出新奉獻。而不是像朱熹和王陽明那樣,自稱得到了古本《大學》,延續了道統的正宗血脈,固執地守舊。
在這之後,王夫之隱姓埋名,潛心著書四十年,同樣寫出了卷帙浩瀚的著作;這些著作也都涉及各個領域,非常的廣博。按中國人傳統的經史子集來劃分,王夫之的代表作如下:
經類二十四種:包括《周易內外傳》、《讀四書大全說》、《尚書引義》等;
史學類五種:包括《讀通鑑論》、《宋論》、《永曆實錄》等;
子類十八種:包括《老子衍》、《張子正蒙注》、《思問錄》、《相宗絡索》等;
集類四十一種:包括《楚辭通釋》、《姜齋文集》、《船山經義》等。
從儒門道統到佛老異端、從正史實錄到詩文雜劇,王夫之的筆尖都有觸及,即使博學如朱熹,也無法像他這樣無所不包、無所不曉。所以王夫之不愧為一名總結者,同時,他又是一名開創者,例如《讀通鑑論》的哲學基礎其實就是“經世致用”的新思想,王夫之想要通過歷史來講時政,本意也是“務當世之務”。此外,《思問錄》這本書還體現了王夫之與前代哲學家兩大不同之處:其一、他用辯證法來抨擊機械論;其二、他有意將哲學建立在科學之上。
王夫之具有系統的辯證法思想
辯證法的思想普遍存在於古代哲學家的著作中,但多以箴言、斷言的形式存在,缺乏系統性,所以經常出現前後矛盾的表述。例如《老子》既說“有無相生”,卻又說“有生於無”,一會兒把“有”升到與“無”同等的矛盾地位,一會兒又將“有”貶低為派生者;在某些地方它斷言“天長地久。”,在另一些地方卻又說“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這些互相矛盾的地方鮮有人去追究,因這本書是由碎片式的句子組成的,所以各種膚淺之人都能各取所需,隨意解讀,進而隨意吹噓。
王夫之的著作卻並不如此,《思問錄》看似碎片化,但它是以系統的辯證法為基礎的,裡面鮮有前後不一的地方。在“內篇”中,王夫之著重討論了“無有”、“幽明”、“聚散”、“清濁”、“得失”等矛盾範疇,提出“兩端,其究一也”的對立統一辯證法;在“外篇”中,他的論述範圍更加擴大,並且批判了京房、邵雍、蔡沈等人的世界觀;這些人根據《周易》與《洪範》的思想,把世界描繪得整整齊齊、井然有序,認為透過卦象與六爻就可以準確預測未來——世界彷彿是一個已經編好程式碼的機器,保持著嚴格的秩序。王夫之則利用辯證法的偶然性理論來抨擊這種思想,他說:
“天地間無有如此整齊者,唯人所作則有然耳;圜而可視,方而可矩,皆人為之巧,自然生物,未有如此者也。”
地球不是正圓的、行星軌道也並非完全規則的橢圓;一年有365日,但並年年如此,而是有些年頭長些、有些年頭短些;所謂的嚴格規則只是人類思維的產物,人們把物體的形狀給抽象化,想象出半徑到處都完全相等的正圓、四邊完全一樣的方形等等,這種思想就是一種機械思維,必然要否認掉偶然性與不規則性。
王夫之對機械觀進行了出色的詰難,例如邵雍在研究自然時,喜歡將萬物“破作兩片”,比如他在《皇極經世》中將“太陽與太陰”、“日與月”、“水與火”、“氣與質”都破作兩片,並且認為兩片之間存在天差地別,各自獨立。王夫之則說:
“兩片四片之說,猜量比擬,非自然之理也。”
他認為對立的兩面是相互依存的,不能“破作兩片”,否則將變為“死形”和“遊氣”,進而不復存在。所以,機械思維的人所設想出來的世界並不是真實的世界,而是被他們給理想化了的。
王夫之自覺把哲學建立在科學之上
古代思想家們大多缺乏科學的精神,王陽明根本就不談科學。張載雖然是唯物主義者,但他存在“執理以限天”的唯心主義傾向,例如天文學家認為地球自轉,故而五星看上去執行速度不同,其中金水二星最快,木土兩星最遲,所以能夠推斷前者離大地近而後者遙遠,月球行一年經十二天,比眾星都快,應距地面最近,這是觀測到的結果。
張載、朱熹等人卻根據義理的思想,認為月球是極陰之物,要“伸日以抑月”,以便符合“陽動陰順”的義理,硬說月球執行得最慢,太陽執行得最快。對此,王夫之採用了當時流行的“遠鏡質測之法”,認可“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最居上”的科學結論,即使他很尊敬張載和朱熹,但仍然堅持唯物主義的原則,說:
“理自天出,在天者即為理,非可執人之理以強使天從之也。”
在《思問錄》中,王夫之還泛論各種自然科學觀點,提及祖沖之、郭守敬、方以智等科學家;可見他非常重視中國傳統的自然科學,並且有意利用自然科學來佐證自己的哲學觀點。在《張子正蒙注》中,王夫之經常引用自然科學的事例來說明辯證法,這點在張載的原書中是很罕見的。中國的大部分哲學家都喜歡引經據典,擅長獨斷;而在王夫之的哲學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傾向,他已經意識到要把哲學理論建立在牢固的科學基礎之上,而不是以幾部古老經典來作為立論基礎,這在中國哲學史上是繼往開來的創舉。當然,也會造成自己的侷限性,所以中國傳統科學的侷限就是王夫之哲學的侷限,這種侷限即使在西方也有,例如培根的《新工具》和黑格爾的《自然哲學》,都論述了許多錯誤的科學觀點,這不足以苛責古人。
此外,王夫之對於未知的問題始終保持謙遜,絕不肯牽強附會地編造答案。對於那些信口開河,聲稱“天開於子,子之前無天;地闢於醜,醜之前無地”等毫無科學依據的宇宙起源論,他答覆說:“吾無此邃古之傳聞,不能徵其然否;吾無無窮之耳目,不能徵其虛實。”對於那些喜歡在哲學中亂下斷言,亂編故事的人,無需去跟他們爭論什麼,因為他們的東西都是毫無根據的偽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