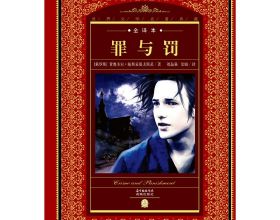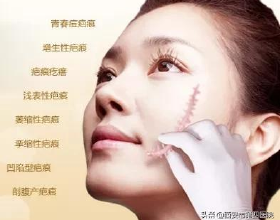每當我開始創作,我總會聽到其他人的聲音、看到其他人的眼睛。我不知道為何會有這樣的幻覺,儘管很多時候它會讓我迷失,但它也的確可以讓我成長。沒有人知道你的前路在何方,相信自己,除此以外沒有別的選擇。
——佐藤裕一郎(Yuichiro Sato)
- (請順時針旋轉螢幕90°以獲得最佳觀賞角度)
三棵年邁的樺樹,矗立在濃霧瀰漫的湖邊。霧氣凍結了偶爾闖入的陽光顆粒,彷彿沙漏裡滑落的沙瞬間停止了流淌。寧靜而刺骨的寒氣中,時間也在為即將到來的凝固而祈禱——雖然是一幅畫,但那裡一定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黎明時分的樺樹
“Koivumaisema”是這幅畫的標題,在芬蘭語中,它有著“黎明時分”與“樺樹風景”的意思。在長達780釐米、高約300釐米的幅面上,他僅僅使用自動鉛筆與石墨進行創作,每天持續繪製8至14個小時,共耗時6個月完成。這,是芬蘭的原始風景;他,是日本畫家佐藤裕一郎。
每當想畫些什麼的時候,佐藤拿起的第一件東西便是鉛筆。一個原點、一支0.5毫米的自動鉛筆、一段漫長而沉靜的時光。沒有束縛、沒有商業畫稿的壓力、沒有眼花繚亂的炫技。他只想畫得簡單一些,即使畫幅變得越來越龐大、即使每天只能完成20平方釐米的創作,但在落下每一筆之後,他仍想畫得再簡單一些。
無論是一棵樹,還是一片森林,佐藤總是喜歡對於細節的描述。所以我們會看到樹上長出的苔蘚、樹皮的龜裂與翹起。看過這些作品,芬蘭人說他們想起了記憶中熟悉的景觀與自然的魅力。而佐藤深知,樺樹與湖泊是芬蘭人的驕傲,就像日本的櫻花,都象徵著人們珍貴而超凡的生命之力,不同的是,前者在嚴寒中挺立,後者於凜風裡起舞。
“無論你走到哪裡,都可以畫出你想畫的畫”
1979年,佐藤裕一郎出生於日本的山形縣。高中時,喜歡畫畫的他放棄了參與了三年田徑俱樂部,隨後他考入東北藝術工科大學(Tohoku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並在那裡獲得了美術學士與日本畫碩士學位。
儘管入讀的是日本畫課程,但在求學階段,佐藤認為學習日本畫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包括顏料與紙張在內的各種畫材處理起來又非常的困難,且必須在各種嚴格的限制與規則內繪製。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原本模糊的念頭變得越發地清晰起來:日本畫不是他要畫的東西,日本或許也不是他可以追逐藝術夢想的地方。
研究生畢業之後,歷經了十年的蟄伏與摸索,2016年,佐藤申請了日本文化廳的藝術家海外實習專案,來到了北半球同樣有著豐富自然資源和深厚民族文化的芬蘭。在踏上這片簡約而冷峻的北歐土地之後,異國的時空重新梳理了他的心境與創念,彼時的佐藤感覺自己被重置了。涅槃之際,一句來自其大學老師木原正徳(Masanori Kihara)教授的話卻時時在耳邊迴響著:“無論你走到哪裡,都可以畫出你想畫的畫。”
樺樹之國·畫樹之人
湖中泛舟、樹林散步、種植漿果、採摘蘑菇……簡單而自由的生活總會讓人忘記了時間的流逝。直到看到了它——矗立在湖邊的一棵樺樹——長久以來他想要畫卻無法表述的一幕景緻,跨越整個歐亞大陸才映入視野的一幅畫卷。此時,原本計劃在芬蘭只停留一年的佐藤突然意識到,他或許永遠也無法離開這個國家了。
面對一棵老樹,我同時懷著敬畏與親和。在平凡的地方感受聖潔的一刻,我尊重這種感覺並試著去表達它。與芬蘭的邂逅、與一棵樹的邂逅,改變了我的工作與生活。
——佐藤裕一郎(Yuichiro Sato)
以白樺樹幹以及共生的苔蘚、蕨類植物為中心,以石墨和自動鉛筆繪製黑白,以礦物顏料和日本油墨表達明暗、乾溼。四季更迭,畫樹之人也跟隨季節輪轉的步伐感受著雕刻其中的文化與歷史,四季之後,又是另一個四季……儘管日本傳統繪畫藝術構成了佐藤的大部分創作思想和繪畫方法,但這個身在北歐的日本人卻在一年又一年的欣喜中,尋求著僅屬於他自己的表達方式,至今仍未停歇。
在芬蘭,很多人在看到我的作品之後都會感到有日本畫的影子,比如作品的張力、黑白的世界觀、空間的處理與留白等等。我從長澤蘆雪、葛飾北齋、伊藤若衝、長谷川等伯這些大師的身上吸收了精華,我想,也許這就是我心中對日本畫的認同感吧。
——佐藤裕一郎(Yuichiro Sato)
藝術本無藩籬,卻存根基。在芬蘭的中南部,赫爾辛基以北300公里處的于韋斯屈萊 (Jyvaskyla),在零下30至零下10攝氏度的冬季,有老樺樹立於湖邊,有畫樹人心念東方。
眼緣藝志 第835篇獻給生活的藝術禮物。
文字撰寫:眼緣藝志
如需轉載請先獲得授權,轉載後請標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