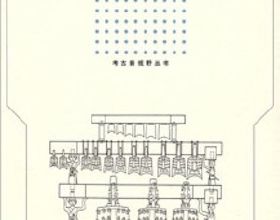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約翰·伯格(John Berger),戰後歐洲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被譽為“人文主義左派的精神領航星”、“良心的守護者”、“同代人中最具全球意義的聲音”。
伯格於1926年出生於一個倫敦中產階級家庭。他在年輕的時候曾立志成為一名藝術家,為此在16歲時違抗家庭意願輟學,前往中央藝術學院學習。二戰爆發後他參了軍,先後擔任過二等兵和準一等兵,在此期間他和工人階級有近距離接觸,這段經歷對他產生的思想影響是終身的。退伍後,伯格進入切爾西藝術學院學習,開始關注時事政治。雖然他終身都保持著繪畫的愛好,但他並沒有成為一名藝術家,而是成為了一名寫作者。伯格的著述非常多元,他寫過藝術評論、寫過小說(他的小說《G.》獲得了1972年布克獎)、寫過很多散文和詩歌,還參與過電視節目和影視作品的創作,可以說是一位20世紀下半葉非常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
但是終其一生伯格在英國也是一位爭議很大的公眾人物——2017年1月伯格去世時,許多訃告在悼念他的同時也不忘指出這一點。這些訃告將伯格描繪成一位因政治爭議激怒了策展人和教授們的藝術評論家;一位在布克獎獲獎感言中公然抨擊布克獎委員會並將一半獎金捐給了黑豹黨的小說家;一位用《觀看之道》猛烈抨擊另外一檔頗受歡迎的BBC藝術節目《文明》的電視節目主持人。
作為關於約翰·伯格生平與著述的首部傳記,《約翰·伯格的三重生命》(下稱《三重生命》)回顧了伯格一生的思想歷程,向讀者展現了他所經歷的各個重大歷史分水嶺以及他的思想變化,呈現所謂爭議下的一位具有非凡複雜性和韌性的人物。日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顧錚和馬凌分享了他們在閱讀約翰·伯格作品以及這部傳記的過程中,對這位非凡思想家的理解與感受。
這是一部“八卦愛好者勸退”的學術傳記,伯格有一種“可敬的滔滔不絕”
“據說接近約翰·伯格最好的方法應該是有意無意靠近他,而不是提前做了大量預備工作之後再去認真讀他。據他自己說,門外漢看他的作品應該是最棒的一條路徑。”馬凌開玩笑地說,伯格雖然教過書,也在電視上當過公共知識分子,但他厭惡學術氣息濃厚的言說,如果現在還活著,聽說有兩位新聞學院的教授在討論他的傳記,不知會作何感想。
中國讀者最早接觸約翰·伯格的作品是1994年由戴行鉞翻譯的《觀看之道》(當時的譯名為《視覺藝術鑑賞》)。馬凌在2009年時讀了2007年的譯本《觀看之道》,當時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通俗的讀本,淺顯地講了四個問題:藝術與政治的問題、性別的問題、油畫所謂自身矛盾的問題、廣告問題。今年為了備課重讀這本書,這位在豆瓣上非常活躍的書評人在短評中寫道:“依然覺得盛名難副,本書出版於1972年,有那個時代的激進色彩,太多政治,太少藝術。他說的都對,但是看多了無趣。”然而在讀完《三重生命》後,馬凌對《觀看之道》的感受出現了變化,“我突然意識到我們應該從歷史當中看待伯格的貢獻。之所以現在覺得它淺,因為他所有的思想我們都已經吸納了,我們都習以為常了,都是政治正確的一部分。但是我們要一路追隨回七十年代,才會意識到他的重要貢獻。”
顧錚表示,《觀看之道》最早的中譯本對書名做了某種無害化處理,可能是因為譯者不知道這部作品在英國——無論是作為電視節目還是配套書籍——所引起的震撼效應。但我們需要承認,不同時代的社會氛圍和學術環境會造成我們對伯格作品不同程度的理解,正如馬凌對伯格的認識也在不斷髮生變化。至於《三重生命》,顧錚覺得它不是一部生動的人物傳記,而是一部學術傳記,對於以某個特定人物為研究物件的博士論文寫作者來說,這本書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範例。
馬凌同意顧錚的觀點,稱這是一部“八卦愛好者勸退”的傳記,“八卦水平是不及格的,但是學術水平是相當高的”:人物傳記的部分只佔全書的1/6,和歷任妻子的每段婚姻三兩句話就介紹完畢,對伯格非常重要的童年生活也沒有交代很多。但作為一部伯格的精神傳記、思想傳記,《三重生命》具有很強的學術意義,作者喬舒亞·斯珀林不僅善於創造金句,而且善於從伯格的著作中挖掘金句,“每頁還有一兩點能夠一下子進入你眼睛裡。”
《三重生命》以伯格人生的三個階段為出發點展開敘述:第一階段是1950年代伯格作為新聞工作者和文化戰士的早期職業生涯;第二階段是伯格“活力的、感性的和高產的十五年”;第三階段則關於伯格如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紮根歐洲山村,將自己重塑為一位抵抗者和一位農民經驗的編年史家。馬凌認為,從作者花費諸多筆力描寫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卻寫得比較淺顯來看,可見作者本人最欣賞的也是伯格最高產活躍的歲月。
讀完《三重生命》,馬凌總結了伯格的三個特點:“伯格是咄咄逼人的,他經常挑戰對方,有時候是一對一的單挑,有時候是一對多的混戰,但是他一直堅持自己的立場不會動搖,這是挺可敬的事情;第二個特點是滔滔不絕,他確實是話比較密的那種人,熱情洋溢的,很跳躍的,總是要放思想焰火的;第三個特點,源源不斷,他的想象力、創造力非常豐沛。雖然我覺得他晚年的著作有點弱,但依然有他的貢獻,比如說動物的視覺和動物的視角,一旦提出後馬上被大家所模仿和欣賞。”
在顧錚看來,伯格的難能可貴之處是他不斷在《觀看之道》中提醒我們,觀眾在面對電視這樣一種影象媒介時是有主體性的,是可以並需要對自己接受的資訊保持警惕的。“這是他非常好的地方,他告訴觀眾和讀者,你們要跟我一起思考,你們也要對我保持一種警戒心,而不像有些知識分子天生就是說教,不允許質疑,就自己滔滔不絕。”顧錚說,“也許‘可敬的滔滔不絕’就是,在滔滔不絕的過程中不斷告訴你這個滔滔不絕是有問題的,你有權利表示質疑,有這樣一份警惕心的人,是不容易的。”
《觀看之道》的時代意義是其激進性,《第七人》才是伯格最好的作品
斯珀林在《三重生命》中指出,雖然伯格一生著述頗豐,但他最有名、最標誌性的作品還是《觀看之道》。要討論約翰·伯格,這確實是一部繞不開的作品。《觀看之道》是伯格與BBC藝術製片人麥克·迪柏一起製作的四集電視節目,首播於1972年,併成為接下來十年裡最有影響力的藝術節目。在每集30分鐘的節目裡,伯格討論了繪畫真跡與複製品之間的原真性問題、油畫在鞏固階級地位中發揮的作用、裸體人像如何反映男性觀者和女性被觀看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等、廣告如何煽動消費主義。斯珀林認為,《觀看之道》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它改變了人文學科的走向,這個節目以及改編自它的書籍一起奠定了後來興起的視覺研究、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方面的基礎。
馬凌表示,學者將階級、性別和種族這“神聖三位一體”的複合視角帶入文化研究領域已有半個世紀之久,因此現在回看伯格,她不免感到有些厭倦,反而覺得當時被伯格激烈反對的肯尼斯·克拉克(BBC藝術節目《文明》的主持人)的觀點也有道理。馬凌認為,《觀看之道》的主旨是為了“破”,這在那個時代是有其意義的,但對她而言,伯格走出了七十年代最激進的那一步後,時代的鐘擺就會往反方向走,“所以我是一個可以把伯格的《觀看之道》和克拉克的《裸體藝術論》放在一起看的學者。”而相容幷蓄——既能夠欣賞純粹的藝術之美,又能夠體察藝術背後的政治性——或許對當下人來說是一個更合適的立場。“就像一個時代的大船在向前航行,但是大多數人都在靠右的時候,可能需要少部分人向左邁一步,這樣船才不會翻。右翼為先的時候,需要左翼站出來;但是當大家都撲向左翼的時候,可能需要有人重新站到右邊來,這樣才能維持一種穩定。”馬凌說。
顧錚認為,《觀看之道》在七十年代的英國是一部石破天驚的作品,除了它在意識形態層面的突破性以外,它的拍攝手法(後來被稱為“電視隨筆”)和書籍的呈現方式(書中有一個章節沒有文字,完全由影象構成)也是開創性的。“這個當頭棒喝影響確實是深遠的,特別是對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初開始出現的英國新藝術史、視覺文化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注意到,伯格的工作具有某種重新確立研究正規化的創新性,甚至令之後的一些學者羞於承認學界在一定程度上被伯格引領了,比如美國藝術史學家溫尼·海德·米奈(Wernon Hyde Minor)在《藝術史的歷史》關於新藝術史和視覺文化的那一章就隻字不提伯格的影響。但在他看來,伯格確實為之做出了突破性的貢獻。
作為攝影批評家,顧錚也談到了伯格在攝影理論方面的建樹。伯格認為,攝影本身不能決定對社會事件、現實問題的態度,我們必須對每一張照片進行錨定,必須靠文字說明把影象的意義固定下來,他反覆強調不要過度理想化地看待一張照片。在《另一種講述方式》中,伯格曾做過一個實驗,請各行各業的人看一張毫無文字說明的照片,他們根據自己的理解給這張照片給出了許多不同的闡釋。對伯格來說,他一直對影象本身可能引發的歧義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另外,他對蒙太奇手法的興趣、與攝影家讓·摩爾的協同創作,也值得更深入的探討。
伯格與讓·摩爾共合作出版了三本書,分別是《幸運者》《第七人》和《另一種講述方式》,《三重生命》對這段合作關係做了認真的分析。這些作品關注的是鄉村醫生、歐洲移民勞工和山區農民,飽含伯格身為一名左翼知識分子的階級意識。馬凌贊同伯格自己的判斷,認為《第七人》是他最好的作品。在這本書中,伯格引入了一些此前被忽略的照片使用的方式。當時大量移民偷渡,他們會在離開家鄉前拍一張照片,撕成兩半,一半留給家人,另一半交給蛇頭,在偷渡成功後由蛇頭帶回作為證明,其家人才會支付費用。“這是我從他的作品中第一次意識到這麼深刻的人類學或社會學,或者說有溫度的方法,”馬凌說,“《第七人》使用的語言是詩人的語言,同時他運用了大量照片,這是一個綜合性的產品,也能代表七十年代的一種風格,在當時是很前衛的創作方式。”
在人生的後半階段,伯格隱居在日內瓦的一個山村中,發掘和書寫當地農民的生活經驗,因此他晚年的思想有很強的地域化傾向。馬凌注意到,伯格在晚年“變得柔軟了”,他寫了大量回憶式文章,用柔軟的、令人感動的筆觸記錄他的所思所想,“他最後能夠關注到動物和人的平等,跟他晚年慈悲為懷的心態也是相關的。”馬凌認為,有些遺憾的是伯格沒能在晚年像霍布斯鮑姆一樣認真地寫一本自傳,讓讀者看到整個20世紀歐洲左翼知識分子圈內的互動情況。“伯格是思維上的多動症,一生中不斷跳來跳去,都是很碎片化的記錄,沒有寫成很飽滿的長篇回憶錄,對我們也算是個遺憾。”
與許多對新媒介充滿警惕的學者不同,伯格意識到了電視技術的力量
伯格另外一個顯著特徵是他是一位非常樂意與公眾對話的知識分子,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是以媒體人的身份活躍在公共輿論場內。斯珀林是這樣描述其寫作上的公共性的:“身為作家,他趕上了用現代化通訊工具創作的年代,當時戰後的社會正在進行激進的民主化。在他餘下的長期職業生涯中,他繼續為儘可能廣泛的觀眾群體書寫,也經常出現在電視上。他的寫作風格平易近人,這種通俗易懂的表達方式,旨在更廣闊的說服力和可理解性。”
馬凌指出,電視自興起伊始就在知識分子圈裡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法國著名思想家布林迪厄就在《論電視》中提出質疑。但與之不同的是,伯格意識到了電視技術的力量,他可以運用這種力量去幫助弱勢群體,反對資本主義,利用這一媒介作為抗爭和發聲的手段。雖然電視的黃金時代是在八十年代,當時伯格已經退隱江湖,但他依然在不斷接觸電視媒介,比如在2016年參與拍攝了傳記片《昆西四季》。馬凌透過這部紀錄片認識到了伯格的魅力,“他對人是特別專注的,你跟他對話的時候,他的目光會看著你,一點不扭捏,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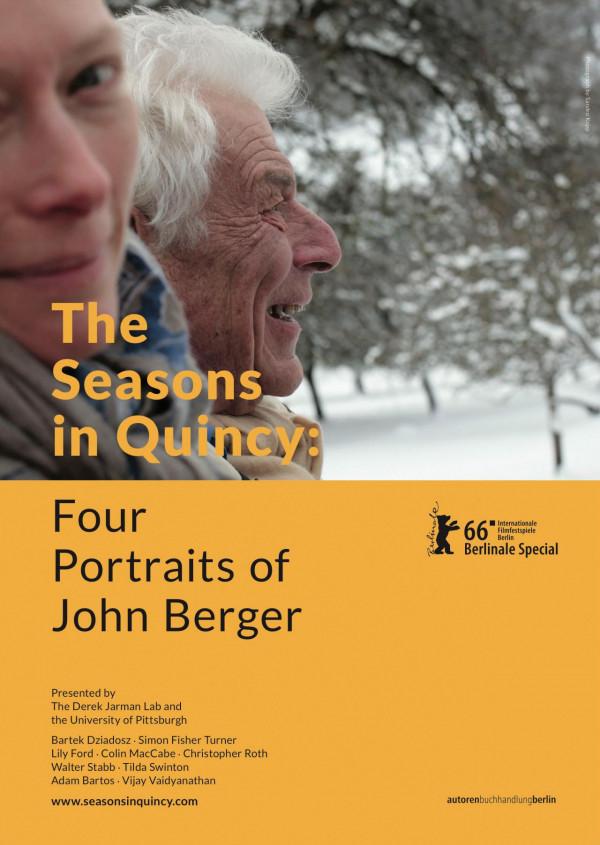
顧錚認為,電視如何在機械複製時代出現後把藝術作為傳播內容和實踐物件,並由此傳播文明,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而伯格在這當中確實起到了作用,“像扔了一顆手榴彈一樣給大家看。”多年來BBC已經形成了一種推出高質量藝術紀錄片的傳統,克拉克的《文明》(1969)、伯格的《觀看之道》(1972)和西蒙·沙瑪的新版《文明》(2018)屬於其中的佼佼者。但顧錚提醒我們注意BBC節目策劃者的“小人之心”,某種程度上來說,《觀看之道》的激進性亦是為了和此前大受歡迎的《文明》拉開反差,對其進行破壞性顛覆。而到了新千年之後,新版《文明》又需要在意識形態層面有所收斂,“就像剛才說的鐘擺來回擺盪。”
馬凌表示,作為一位活躍在前電視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伯格著作中存在一個盲點,就是他對技術沒有很多討論。如今電視也已式微,社交媒體和短影片開始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對人類心智可能造成的影響亦是我們時代的熱議話題。馬凌認為,每代人都在新媒介誕生時有過焦慮,但我們無需過度擔憂。在顧錚看來,知識分子遲早需要面對新媒介不斷出現、如何進行公共言說的現實問題。即使是布林迪爾本人,也在晚年的時候頻繁上法國電視臺。“新的媒介出現,也許會有一個從牴觸到逐漸接受的過程,布林迪厄也出現了這個變化,在薄薄的《論電視》中對它有相當的鄙視,再到後來自己積極地上電視,在不斷爭辯的過程中面對現實,尤其這個現實是全球資本主義到了勢不可擋的時候,有許多知識分子覺得應該要做點什麼,要努力一下。”
對於普通人來說,在短影片時代如何捍衛自己的資訊社群自主性或許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馬凌認為,從媒介平權的角度來說,短影片的意義重大,普通人都可以透過手機拍攝、分享自己的見聞;但如果不想被演算法推送裹挾,陷入被動接受單一資訊的漩渦,我們需要提高媒介素養,學會更好地利用新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