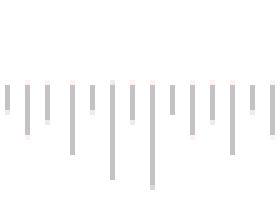澎湃新聞記者 錢雪兒 整理
“成為安迪·沃霍爾”正在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展出,展覽進行之際,一系列導覽直播向大眾分享了關於安迪·沃霍爾不同的解讀視角。其中,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以“叩訪當代藝術開啟的時刻”為題,講述了對於安迪·沃霍爾的理解。
安迪·沃霍爾(1928年-1987年)
無窮的複製:揭秘當代藝術
安迪·沃霍爾確實是當代藝術的一個時刻,而當代藝術的出現構成了文化史和藝術史的時刻,但是它並不是一個開啟時刻,因為早在安迪·沃霍爾震驚紐約,震動美國,震動全世界之前,當代藝術已然開啟。比如杜尚、畢加索、達利,他們開啟當代藝術的時刻,大都是在19、20世紀之交或者20世紀之初20世紀前半葉,如果說早在安迪·沃霍爾之前,現代藝術已然被開啟,那麼為什麼是安迪·沃霍爾成為了一個“地標性”的人物?
我想說,安迪·沃霍爾的時刻是一個揭秘的時刻,他把已然發生的當代藝術仍然小心翼翼地隱藏在藝術的光環之下的、儘可能去保護和撫慰社會公眾、關於藝術想象的那些偽裝全部撕碎了,炸碎了,燒光了。他把現代社會當中藝術的某一種真實和當代藝術的某一種特異性,赤裸裸地展現在了我們的面前。所以我說安迪·沃霍爾是這樣的一個時刻。
安迪·沃霍爾所開啟的時代的關鍵詞,毫無疑問是複製。複製這種事實和我們關於藝術的一個基本想象相悖逆,因為藝術的基本想象是原創、是原創力,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獨一無二。而複製不僅僅是對原創性的徹底否認和褻瀆,而且是充分地暴露了複製行為自身背後的一個現代社會、現代歷史的最重要的社會事實,就是工業化、機械、技術、資本、金錢、市場以及媚俗。安迪·沃霍爾最知名的作品,大概就是《瑪麗蓮·夢露》,在印刷的時候以不同的分色處理,由於印刷的時候出現套色錯版,而產生各種各樣不同的瑪麗蓮·夢露的照片,一個無窮無盡的複製、變奏。
《瑪麗蓮·夢露》
更具有代表性的一組作品是《坎貝爾罐頭》。有過美國生活經驗或者到美國旅遊的朋友,大概會知道坎貝爾罐頭在美國的日常生活、在美國的日常消費當中所佔的位置,進入任何一個大型超市,你很容易看到無數的坎貝爾罐頭,它就是一個現成即食的湯罐頭。當然同樣有名的、代表著安迪·沃霍爾複製行為的就是可口可樂。各種可口可樂形象的無窮複製。可口可樂和坎貝爾罐頭似乎比瑪麗蓮·夢露更容易讓我們理解到安迪·沃霍爾的作品的某一種特徵,就是充分地日常、充分地大眾、充分地非藝術。
安迪·沃霍爾只是把一個已然存在的事實透露出來。他是一個曝光和顯影者,這是一個曝光和顯影的時刻。為什麼這樣說?大家肯定知道,19世紀20世紀之交若干重要的技術發明之一是攝影術的發明,然後我們出現了照相機,我們出現了電影、攝放機器,我們誕生了攝影藝術和電影藝術,而攝影藝術、電影藝術長時間在傳統藝術觀念中無法自我證明,為什麼?因為他們難於透過作品的獨一無二性,與作品的原創和原出作品的原作的唯一性來印證自己的藝術品格。而安迪·沃霍爾把這個曾經潛藏在新技術發明,潛藏在攝影術和照相術當中歷史轉折的時刻,曝光在了藝術場域,曝光在了藝術現場,曝光在了美術館空間這樣一個場域之中。
《坎貝爾罐頭》
思想家本雅明在20世紀的前半葉撰寫了《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它已經向我們表明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機械複製時代。曾經在傳統藝術當中,藝術家原創,藝術家原作的獨一無二性已然被這樣的一個新的技術發明、技術改變所抹除。本雅明的作品當中也提出了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靈氛或者叫氛圍。原作本身是頂著光環的,但是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則使這個靈氛無限消散。我們講到安迪·沃霍爾的複製的時候,我們同時會意識到另外一個重要的理論事實:藝術作品非但不是原作,非但不是獨一無二的,非但不是不可替代的,它甚至成為了某一種擬象。法國理論家鮑德里亞曾經告訴我們,擬像是其當代文化的一個最主要的特質,是當代文化作品的一個基本的特質,這個特質是什麼?就是沒有原作的複製品,每一個都是複製品。安迪·沃霍爾不光無窮複製了坎貝爾罐頭,不光無窮複製了瑪麗蓮·夢露,他複製的那個東西本身不是原作,他複製的那個東西本身已經是工業製品。這個正是曾經隱藏在攝影術和電影藝術和當代藝術背後的謎底。
《神話》系列
流沙之中的堅固真實
我們行走在“成為安迪·沃霍爾”展覽大廳的時候,我多少能夠理解感到憤怒的朋友,是因為他一點都不崇高,他一點都不攜帶著我們似乎本能地體認的美感,我們很難遇到那種我們渴望沉浸在藝術當中獲得的美的啟示,是因為安迪·沃霍爾的作品,同時真實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20世紀的歷史時刻,這個時刻我們把它稱之為“媚俗”。
“成為安迪·沃霍爾”展覽現場
如果我們查查英文字典,媚俗就是Kitsch,它的原意就是批次生產機械複製。這才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安迪·沃霍爾的時刻。這個時刻來自於在現代歷史過程當中,資產階級透過暴力的非暴力的革命,透過經濟、政治革命,終於推翻了僧侶、貴族和皇權所聯合統治的這個世界,他們佔領了這個世界,成為了主宰者。但是在漫長的現代歷史當中,布林喬亞們始終沒有取得自己文化的自信,他們一直在貴族的趣味、生活,對現代革命之前的田園世界的無窮崇拜和嚮往之中。這樣的一個現代社會統治階級和統治文化,不能自我確認的事實,造就了一個非常扭曲的心理狀態。這個心理狀態,一方面表現在他們一直想模仿貴族趣味。其中包含張揚藝術的超越性:藝術是繆斯的召喚,藝術是詩神的迷狂,藝術是天才們的不可掌控的這樣的一種創造。而另外一方面,他們又必須小心翼翼地藏起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從確立那天起,就一直延續不斷推進的一個過程,即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形象、具象的藝術,色彩,線條,穩固的畫框,穩定的審美形態,在一個不斷地碎裂當中變成沙粒化,我們不斷地跟著文化的流沙在流逝。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就是一切都變為商品。金錢是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唯一度量,可是這兩個事實都被小心翼翼地隱藏起來。而安迪·沃霍爾作為一個揭秘者,足夠地赤裸和無恥,他不斷地聲稱我愛錢,我一生都致力於、都獻身於去賺錢。
展覽現場,銀色的地面和座椅,向遠處延伸的巨大的展陳空間。
《美元符號》也是安迪·沃霍爾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某種意義上說,二戰之後美國霸權的確立,非常真切地表現在世界上的一切都被美元化,尤其是在金本位被取消之後,我們所有的食物生產,所有的勞動,所有的血汗,最後都是以某種方式摺合為美元來確立它的價值。而安迪·沃霍爾赤裸地把這個美元的logo變成了一個他的作品。同時他毫不掩飾他愛錢,他要賺錢。安迪·沃霍爾所揭秘出來是一個當代藝術與市場、與資本、與工業、與技術的這種無間的連線。
從表面上看起來,安迪·沃霍爾是肆意妄為的,是桀驁不馴的,是極具挑戰性和冒犯性的。但是在我看起來,他並不是以他的冒犯挑釁、反抗,而標識他那個時刻的,為什麼這樣說?是因為他挑戰冒犯的物件,其實早已經是朽壞了的屍體,他根本不是藝術的真實。相反,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流沙之中堅固的真實,這個堅固的真實就是資本的主導,市場的主導,一切煙消雲散,堅固的東西都在煙消雲散,而一切東西都變成可賣的、可衡量的。
沃霍爾的自拍:顛覆與確認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安迪·沃霍爾著名的自拍。它不光是一個自拍,重要的是它的印製技術。你從某一個角度看,這幅自拍的照片是泛藍光的,你從另外一個角度說,它整個的形象是銀色的,泛著那種金屬的光澤和質感的。
安迪·沃霍爾自拍,截圖自UCCA×抖音直播導覽
傳統的藝術家也會有自己的自畫像,但是揭秘之後的當代藝術市場、當代藝術場域、當代藝術空間當中的藝術家,同時應該是自我形象的經營者。他們的形象成為了他們的品牌,成為引領人們去關注他們的作品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換句話說,安迪·沃霍爾一點不否認自己是藝術家,同時是個精明的商人。
正是從這個“自畫像”,我們可以進入到另外的討論當中,另外的層次,另外一個安迪·沃霍爾的時刻,是他以他的作品向我們強調了另外一個重要的文化變化的發生,就是媒介時代的到來。安迪·沃霍爾似乎對當下的追逐成功的人們,都很有啟示。就是你要充分地提供話題性、你要充分地引發爭議,你這樣說,有點想當然、有點誅心,就是你要去冒犯他們,以便引發話題和關注。
安迪·沃霍爾名人攝影
《瑪麗蓮·夢露》不僅在於那副著名的肖像被無窮複製,而且在於它讓我們親眼看到了批次生產,無窮複製,媚俗的過程本身是一個工業技術工藝過程。因為據說他最早的靈感就來自於印刷的時候的套色錯版,然後他就把套色錯版作為了他的一個基本的語言形態,他故意地製造套色錯版,和以不同的套色錯板形成他複製之中的變奏形態。同時安迪·沃霍爾的作品當中,他會故意地顯露出絲網印刷的絲網的痕跡,他會讓那個油墨的汙染留在這個作品上面,他會讓我們刻意地注意到當代藝術作品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的材質和物質性。
講到安迪·沃霍爾的時刻,也許熟悉美國文化史或者歐美文化史的朋友,同時會聯想到另外一個特殊的年代,就是全球60年代, 20年世紀60年代為什麼這麼重要?因為20世紀60年代開起了延續到我們今天的近乎一切,從技術,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的組織形態,然後個人的自我安置和個人自我安置時所面臨的問題。在政治性的位面上,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風雲激變的,激情噴湧的一個理想主義的鬥士,為改變世界而鬥爭的年代。但是經由安迪·沃霍爾,我們也許會看到另外一個位面:20世紀60年代的意味是一個政治上老帝國主義、老殖民主義節節敗退的年代,但是在文化層面上,現代主義開始炫耀他們的全球獲勝。為什麼這樣說?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的過程,也是曾經多姿多彩的,多元多義的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開始仿照西方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價值、知識體系來自我改造,而層出不窮的被壓迫人民,被壓迫人群,被壓迫的少數人,奮起反抗的過程,也可以多少有點令人沮喪的概括為一句話,就是I want to be human——我想當人,而這個時候女人要做人,有色人種要做人,土著要做人,奴隸要做人,性少數要做人,但是我們的模板是歐洲白人。換句話說,反抗的60年代,向我們揭示另外一個今天發人深省的事實,就是在現代主義內部,在現代主義內部的反抗當中,我們並沒有創造出一個現代主義邏輯之外的選擇、可能和出路。而今天我們面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困境危機,現代主義的問題,這個事實變得非常急迫。
安迪·沃霍爾名人攝影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回到安迪·沃霍爾。安迪·沃霍爾被視為一個頑童,一個挑釁者,一個冒犯者,一個主流文化的肇事者,他也是主流邏輯的這樣的一個實踐者和印證者。這裡面的反叛和挑釁,確立和建構,本身的矛盾議題正向我們揭示了,今天我們要思考世界,思考文化,思考藝術的時候,我們還有沒有一種想象、創造、建構其他的文化可能性,文化出路,一種其他的藝術,一種其他的文化實踐的可能性。
在安迪·沃霍爾的生平中,你會知道他因為出生在匹茲堡的貧民區,成長在大蕭條的年代,患有身心疾病,所以他極度敏感和自卑。但是看一看整個展廳當中的作品,你們會發現他如此的自戀而張狂。這個敏感、退縮和自戀、張狂,這樣的一個自卑與自戀的一個無限迴圈的組合體,似乎向我們昭示了某一種現代人或者現代人格的議題,向我們昭示了某一種現代個人的範本,也向我們昭示了某一種現代社會和現代文化當中,那個不斷試圖安置,但是難於安置的個人自我確認,使我所有的文化要求將我區隔於他人,但是所有的文化又不斷地在抹除我與他人的痕跡。所以獨一無二的安迪·沃霍爾是透過無窮複製的,難於辨識的這樣的一種作品形態,來自我標識的。無限自卑的安迪·沃霍爾,是透過張狂無比的侵犯性的、冒犯性的表達來自我確立的。安迪·沃霍爾是反文化運動的先驅,從某種意義上又是開啟了整個主流文化的一種路徑,模板,範例。
“成為安迪·沃霍爾”展覽現場
今天我們在北京,在尤倫斯這樣的一個空間當中來看安迪·沃霍爾。我們把美術館所在的空間稱為798。當798這樣的一個標識出來的時候,其實它再度召喚和聯絡起50—70年代的中國歷史,聯絡到我們中國工業化的程序,中國現代化的關鍵的歷史時刻。這樣的一個藝術性的,自帶著光環的空間,和它曾經舊有的工業空間連線對照。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它提醒我們,面對安迪·沃霍爾的時候同時要思考,經由不同的歷史路徑完成了自己現代化歷程、走到了今天的中國,是否應該去思考不同的路徑?是否應該在這個高度內化的,但畢竟是舶來的現代主義邏輯內部,與中國曾經有過的多元多意的邏輯碰撞當中,去思考我們的當代藝術,去思考我們的可能性,我們的想象是否還可以被激發?
(除特殊標註外,圖片均由澎湃新聞記者高丹攝於展覽現場。)
責任編輯:顧維華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