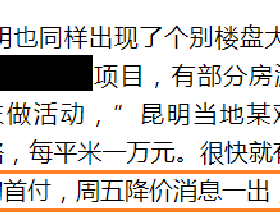我對“大火星”最初的印象,來源於高中時語文老師考試前的三令五申:“‘七月流火’的‘火’是大火星而不是火星,是說天氣逐漸變涼。”
從此,“大火星”就與“七月轉涼”聯絡在了一起,成為了掛在天上的“溫度計”。
實際上,《七月》所言也並非空穴來風,大火星在歷史上確實曾經一度擔任過衡量季節的重任。
按照天文學的說法,大火星的學名叫做“心宿二”,位於二十八星宿中的心宿,是一顆著名的紅超巨星,能放出火紅色的光亮,在附近其他的星星中間顯得異常奪目。
古人認為,它是唯一一顆能與同樣奪目的火星媲美的星星,因而將它叫作“大火星”。
大火星與火的淵源也並不只是這麼簡單。
先秦典籍《屍子》記載:“燧人上觀辰星,下察五木以為火。”辰星指的就是大火星,可見,古人認為,燧人氏鑽木取火的靈感,正是大火星給的。
當然,即便大火星再紅亮耀眼,它的光芒也不可能真的變成火,燧人氏這番“格物致知”的真正奧妙,在《中論》中得到了揭示:“燧人察時令而鑽火。”所以他觀察大火星的目的,是為了感知時令,確定取火和滅火的時節。《周禮·夏官》雲:“季春出火,民鹹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這裡說的“出火”,既是大火星自天邊而出,也是人間的火重新點燃的時候——而這,剛剛好也是“寒食節”的時間。
所以,早在燧人氏的時代,大火星的升落就已經與曆法密切地聯絡在了一起。《尚書·堯典》說:“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意思是說,在白天比較長的時候,大火星端正地出現在南方的天空,就意味著仲夏時節到了。星辰的執行比物候的變化更加準確,因此,古人學會了根據大火星為訊號,來決定何時播種,何時收穫。
專門記錄農事的歷書《夏小正》說:“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也就是說,五月看到黃昏時大火星位於南天中央,就是種黍米、大豆、糜子的時候了。
其實《夏小正》通篇的記載,都有著這種“一葉落知天下秋”的氣質,上至星象變化,下至鳥啼蟲鳴,最終都會和“莊稼事”聯絡在一起,像極了你在今天的鄉下依然能聽到的一段段閒談。
於是,回過頭來再讀《七月》,你就會發現,每一句都是那樣的順理成章、“師出有名”: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蠶月條桑,取彼斧斨,
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
八月剝棗,十月獲稻,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
九月叔苴,採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何時事蠶桑,何時採野菜,何時收蘆葦,何時備冬衣,何時築場圃,何時收稻荷……一年到頭的農事,都與時令物候緊密地聯絡在了一起,一副耕織圖就在詩句的娓娓道來中,緩緩在讀者面前展開了。
受到歲差效應的影響,大火星出沒的季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緩慢變化,如今“流火”的日子,已經推遲到了陽曆九月。
古人很快發現了這一點,因此,自漢代之後,人們逐漸拋棄了靠大火星定季節的歷法,但“流火”作為初秋的象徵,依然頻繁地出現在詩詞歌賦中。唐代劉言史有一首《立秋》這樣寫道:
茲晨戒流火,商飆早已驚。
雲天收夏色,木葉動秋聲。
從立秋這一天的清晨起,暑氣消去,秋風乍起。雲天疏朗,不復夏時模樣,樹葉的沙沙聲,在傳遞著秋的訊息。宋代周敦頤也有一首《贊蓮》提到了“流火”:
陸上百花競芬芳,碧水潭泮默默香。
不與桃李爭春風,七月流火送清涼。
按理說,到了唐宋時期,“流火”的時間應當早已過了立秋,但詩人仍然習慣性地按照《詩經》中的說法,把“流火”算作是七月的天象,只不過,此時的“火”,已經是既非火星,也非大火,而是“詩中之火”了。
細想來也有趣,也許對這些詩人來說,天上之“火”甚至遠不如書中之“火”來得熟悉,正如同今天的我們,還從未真正地在星空中見過火星和大火星,就已經在課本和典籍上熟悉它們了。
紙上談兵固然可悲,但換個角度想,在夜晚的星空逐漸暗淡的現代化城市裡,我們還能夠在詩歌裡尋覓到那些被定格的璀璨星辰,又何嘗不是一種幸運呢?
也許,比繁星更為永恆的,恰恰是人類的燦爛文明。
來源 | 我們的太空
作者 | 靳舒馨
編輯 | 羅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