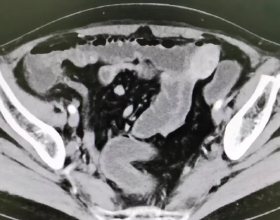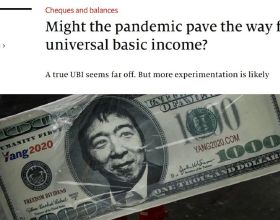孔維琴 陳波
“你們來自東方,你們來自西方,你們的存在向世界證明,在尋求使人類擺脫疾病的崇高使命中,沒有冷戰。”
——巴西爾·奧康納(Basil O’Connor)
在冷戰對抗的近半個世紀裡,與政治角力、軍備競賽不同的是,美蘇兩國在醫療衛生特別是對抗疾疫方面曾呈現一股奇特的趨勢:雙方在外交、軍事、意識形態、經濟制度等方面競爭激烈,但在醫療衛生方面卻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冷戰高峰期,美蘇兩國的科學家在沒有政府間協議的情況下,曾共同致力於脊髓灰質炎和天花疫苗的研發、生產和推廣,最終使人類戰勝了天花,並幾乎消滅了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痺症)。
美蘇合作研發薩賓型脊髓灰質炎疫苗
20世紀50年代,美國以喬納斯·索爾克(Jonas E. Salk)和阿爾伯特·薩賓(Albert B. Sabin)為代表的病毒學家研發出脊髓灰質炎病毒疫苗。1955年,在對全國近200萬學生進行了測試後,索爾克的滅活疫苗成為第一個獲得美國政府批准的疫苗並且得到廣泛應用。而薩賓認為,由減弱但仍具有活性的脊髓灰質炎病毒組成的疫苗將比滅活的病毒疫苗更有效,因為它可以產生終身免疫力。但是由於美國大都數人都已經接種了索爾克疫苗,就沒有足夠的受試者來證明他的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因此,薩賓的疫苗最初在美國並沒有獲得成功。
與此同時,脊髓灰質炎病毒也在蘇聯肆虐,發病率急劇上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派遣當時最傑出的病毒學家米哈伊爾·楚馬科夫(Михаил П. Чумаков)和阿納託利·斯莫羅廷採夫(Анатолий А.Смородинцев)以及楚馬科夫的妻子瑪麗亞·沃羅西洛娃(Марина К. Ворошилова)等人前往美國與薩爾克和薩賓等科學家交流(圖一),並且參觀了薩賓的實驗室。儘管當時美蘇兩國關係籠罩在冷戰的陰影之下,但是這次醫學交流還是比較成功的。雙方交換了一些醫療科學知識,最重要的是,這次訪問之後楚馬科夫和薩賓建立起了友誼,為以後的兩國疫苗合作打下了基礎。
圖一:從左到右:沃洛娃希洛娃、薩賓、楚馬科夫、斯莫羅廷採夫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565345/figure/ch6.fig1/?report=objectonly
1956年6月,薩賓受邀前往蘇聯,分別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與科學家們會談、舉行講座、推廣他的減毒疫苗。薩賓將他的三種“弱毒性”病毒株交給了楚馬科夫和瑪麗娜,用他的減毒疫苗技術幫助楚馬科夫等人推動蘇聯脊椎灰質炎疫苗的開發和使用。楚馬科夫為自己接種了薩賓疫苗,他的妻子給他們的三個兒子和幾個侄女和侄子也接種了該疫苗。
1959年,楚馬科夫決定組織第一次大規模臨床試驗,使用薩賓開發的弱化活毒株製成口服脊髓灰質炎病毒疫苗疫苗(OPV)。彼時,蘇聯已經開始使用索爾克的疫苗,蘇聯衛生部認為沒有理由再進行其他疫苗的臨床試驗。但是薩賓的疫苗更容易接種(通常將疫苗放在糖果裡面服用或者用藥水滴),生產成本更低,持續效果更長。楚馬科夫說服了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阿納斯塔斯·米高揚(Анастас И. Микоян)進行更廣泛的試驗。經過臨床試驗,薩賓和楚馬科夫證明,用弱病毒株生產的脊髓灰質炎疫苗既安全又有效。蘇聯及其他國家將近一億20歲以下的青少年接種了該疫苗。這也使得蘇聯成為第一個大規模使用薩賓活性疫苗的國家,幾年後蘇聯實際上根除了脊髓灰質炎的威脅。疫苗在蘇聯取得成功推動了美國進行OPV大規模臨床試驗。
蘇聯還向包括日本在內的脊髓灰質炎流行地區贈送了數百萬劑口服疫苗,並藉此獲得了人道主義讚譽。中國也是美蘇疫苗合作的受益者。“中國脊髓灰質炎疫苗之父”——顧方舟於1951年至1955年期間曾在蘇聯醫學科學院病毒研究所學習。1959年3月,中國衛生部決定派顧方舟等人到蘇聯考察脊灰疫苗的生產技術。回國後,衛生部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協作組”,由顧方舟擔任組長,進行脊髓灰質炎活疫苗的研究工作。2000年,中國衛生部門和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國內已徹底消滅脊髓灰質炎。
面對脊椎灰質炎給全球衛生健康帶來威脅,美蘇開啟了前所未有的醫療合作,成為冷戰政治中一個獨特的景象。正如1960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第五屆國際脊髓灰質炎會議上,美國國家嬰兒麻痺症基金會的主席巴西爾·奧康納(Basil O’Connor)所說:“……你們來自東方,來自西方,你們的存在向世界證明,在尋求使人類擺脫疾病的崇高使命中,沒有冷戰。”正是由於美蘇兩家合作推動的薩賓減毒活疫苗以及其他國家的共同努力,使全球脊髓灰質炎病例數量從1988年的35萬例減少到2011年的650例左右。
美蘇根除天花計劃的合作
天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短短十幾年間被完全消滅的人類傳染病。雖說天花疫苗在18世紀就已誕生,但該傳染病被完全消滅的關鍵不併在於醫療技術上的突破,而在於冷戰時期的大國合作。
195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上,蘇聯病毒學家、衛生部副部長維克多·日丹諾夫(Виктор Жданов)提交了一份關於根除天花病毒的長篇報告。他建議透過一項為期4—5年的疫苗接種運動來根除它。蘇聯已經在全國範圍內控制了天花,包括衛生服務落後的大片地區。當時蘇聯的亞洲鄰國頻繁出現天花,並在本已沒有天花的中亞加盟共和國爆發。第二年,蘇聯代表團繼續推動這一運動。日丹諾夫宣佈,蘇聯每年生產1億劑耐熱疫苗,如果必要的話可以增加三倍。蘇聯在1958年巴基斯坦疫情期間向其捐贈了疫苗,日丹諾夫再次承諾,蘇聯將以同樣的姿態支援全球根除天花運動。此外,蘇聯科學家開發了一種獨特的方法——冷凍乾燥技術,可以在惡劣的環境中儲存天花疫苗。以前的天花疫苗暴露於高溫後穩定性不高,效果降低。冷凍乾燥技術使得生產數億劑凍幹疫苗成為可能。這也是後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科學家唐納德·亨德森(Donald Henderson)領導的消滅天花運動的關鍵技術。
1966年,華盛頓將根除天花這項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交給了亨德森。1967年全球有多達200萬人死於天花,另有1500萬人受到感染。從一開始世衛組織就對疫苗接種運動缺乏信心。許多人,包括世衛組織總幹事都認為,要遏制天花,必須對43個受影響國家(包括那些國家的偏遠村莊)和地區所有約11億人口進行接種,這對後勤工作來說是無疑是噩夢。因此,世衛組織代表進行了數天的討論後,以史無前例的微薄優勢(需要58票透過,結果是60張贊成票),批准每年為這項工作提供微不足道的240萬美元,這些資金連疫苗資金缺口都填不上,更不用說為後勤提供支援了。
然而,亨德森和他的團隊突破了人們的預想。其中一個關鍵環節是亨德森意識到,蘇聯推動全球天花根除運動已有數年之久,並且保證每年捐贈2500萬劑疫苗。於是,他與蘇聯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迪米特里·韋尼迪克托夫(Дмитрий Венедиктов)取得了聯絡,美蘇雙方除了確保捐贈疫苗外(美國方面也已同意每年提供5000萬劑疫苗),還可以在戰略和後勤方面共同努力。上世紀60年代冷戰高峰期間,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和蘇聯病毒製劑研究所合作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天花疫苗——蘇聯提供4.5億劑疫苗,而美國則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支援世衛組織,並且提供專家小組以及專業知識。曾經參加根除天花運動的美國醫學家威廉·福格(William Foege)在接受STAT新聞採訪時回憶道:“這一切都是在冷戰期間完成的。蘇聯和美國合作……試圖說服世衛組織將此作為一個目標。”兩個看似最不可能的盟友最終領導了這場對抗天花的鬥爭。
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亨德森繼續高度重視並保持與蘇聯的良好與合作關係。在他擔任專案負責人期間,他一直細心地將專案的啟動歸功於蘇聯。他還與蘇聯官員密切合作,解決各種問題。例如蘇聯疫苗的質量提升。此前蘇聯出口的疫苗一部分因為沒有達到國際標準而被退回,亨德森親自前往莫斯科,與德米特里交流,後者表示保證對蘇聯疫苗生產質量的監控;雙方還一起對負責蘇聯專案的候選人進行考察。在每年的世界衛生大會之前,亨德森會與美國和蘇聯代表團會面,報告計劃的進展情況,並依靠他們將專案遇到的問題在議程上提出。亨德森還依靠派駐在疫病流行國家的美國和蘇聯外交官的幫助,對當地不配合的衛生官員施加壓力,無論是世衛組織區域辦事處還是駐在國的衛生當局官員。1974年,衣索比亞發生革命,美國和平隊志願者和美國外交官離開,大多數聯合國辦事處被關閉,兩名疫苗接種員被殺害。幾個月後,衣索比亞政府在蘇聯的壓力下,建立起了秩序,並將世界衛生組織的天花專案作為優先事項,天花根除計劃得以繼續。
美國軍方為世衛組織提供了無針注射器(圖二),可直接在皮下注射疫苗,每班次可以輕鬆接種一千人,大大提高了接種效率。威廉·福格擔任非洲疾病控制中心天花根除計劃負責人的同時,制定了監視和“環形疫苗接種”策略:他派人到30英里內的所有村莊檢查是否有更多的病例,然後只在出現病例的四個地方為人們接種疫苗。這在感染者周圍形成了一個疫苗接種的“環”,打破了感染鏈,最終遏制天花的傳播。這極大地減少了所需接種疫苗的數量。
圖二:七十年代的無針注射器(https://tjournal.ru/stories/155397-iskorenenie-ospy-kak-eto-bylo)
1980年,在全球共同努力之下,世界衛生組織宣佈世界正式消除了天花。因消滅天花的努力,福格與日丹諾夫兩位科學家共同獲得了2020年“生命未來獎”。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說:“我們都感謝福格和日丹諾夫在消滅天花方面的重要貢獻,這顯示出科學和國際合作對抗疾病的巨大價值。”福格說:“我們在天花中吸取了很多經驗教訓,其中之一是聯合的絕對必要性。”如果沒有美國的資金和蘇聯的疫苗,沒有兩個超級大國為該計劃提供的體制動力和政治支援,天花根除計劃不可能啟動,更不可能取得成功。天花根除計劃總共花費約9800萬美元,約有三分之一來自世衛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的支援,美國是該計劃資金的主要捐助國。而另一面,蘇聯貢獻了最大份額的疫苗:在全球根除天花運動中使用的大約20億劑疫苗中,共有近17億劑由蘇聯提供。
結語
雖說“疫苗外交”未曾緩和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緊張局勢,但它為大國聯合進行人道主義活動提供了範例。在美蘇合作對抗脊髓灰質炎和天花50年後,雖然這兩種疾病慢慢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但是兩個案例對當代全球醫療衛生合作仍然具有意義。儘管大國之間存在競爭關係,冷戰期間美蘇疫苗合作所取得的成就表明:面對人類共同的疾疫,醫療合作是必要且必需的。
新冠疫情之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要使世界重新開放、恢復常態,中美兩國應該攜起手來共同抗疫。只有中美兩國在疫苗援助領域進行分工、合作,全球疫苗的分配才能更加公平,抗擊新冠疫情的前景才會更加光明。冷戰期間美蘇合作給當前中美兩國樹立了一面鏡子,只有兩國加強在疫苗研發及生產、分配等領域的合作,才能建設人類健康共同體。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新冠病毒,雙方要眼於未來,就像美國和蘇聯在冷戰高峰期合作控制脊髓灰質炎、根除天花一樣,中美勠力同心必將鼓舞兩國和全世界人民戰勝新冠病毒的信心。
(作者:孔維琴,華東師範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兼職青年研究員;陳波,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