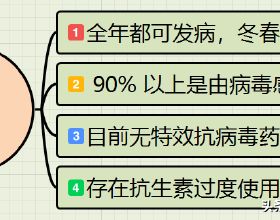作者: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統一大業,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專制主義王朝。秦王朝執政短暫,公元前207年被民眾武裝暴動推翻。秦短促而亡,其失敗,在後世長久的歷史記憶中更多地被賦予政治教訓的意義。然而人們回顧秦史時,往往也都會追溯到秦人從立國走向強盛的歷程,對秦文化的品質和特色有所思考。許多學者就此進行了長期的認真研究,得考古發掘收穫等多重證據之功,相關認識有所深入。
“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
秦人有早期以畜牧業作為主體經濟形式的歷史。《史記·秦本紀》說秦人先祖柏翳“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漢書》則作“育草木鳥獸”(《百官公卿表上》),“養育草木鳥獸”(《地理志下》),經營物件包括“草木”,反映農業和林業在秦早期經濟形式中曾經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秦作為政治實體,在兩週之際得到正式承認。秦人起先在汧渭之間開闢畜牧業基地,又聯絡草原部族,團結西戎力量,國力逐漸強大,後來向東發展,在雍(今陝西鳳翔)定都,成為西方諸侯,與東方列國發生外交和戰爭關係。秦國的經濟進步,有利用“周餘民”較成熟農耕經驗的因素。秦穆公時代“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史記·秦本紀》),是以關中西部地區作為根據地實現的崛起。
史書明確記載,商鞅推行變法,將秦都由雍遷到了咸陽。《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任大良造,“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定都咸陽,是秦史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因此形成了秦國興起歷史過程中的顯著轉折。遷都咸陽,有將都城從農耕區之邊緣轉移到農耕區之中心的用意。定都咸陽,是秦政治史上的輝煌亮點。商鞅頒佈的新法,有擴大農耕的規劃、獎勵農耕的法令、保護農耕的措施。於是使得秦國在秦孝公—商鞅時代實現了新的農業躍進。而指導這一歷史變化的策劃中心和指揮中心,就在咸陽。咸陽附近也自此成為關中經濟的重心地域。《史記·封禪書》說:“霸、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說明“近咸陽”地區水資源得到合理利用。關中於是“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漢書·地理志下》),被看作“天府之國”(《史記·留侯世家》)。
回顧春秋戰國時期列強競勝的歷史,歷史影響比較顯著的國家,多位於文明程度處於後起地位的中原外圍地區。其迅速崛起,對於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中國”即黃河中游地區,形成了強烈的衝擊。這一歷史文化現象,就是《荀子·王霸》中所說的:“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五霸”雖然都崛起在文明程序原本相對落後的“僻陋”之地,卻能夠以新興的文化強勢影響天下,震動中原。“五霸”所指,說法不一,如果按照《白虎通》有關“五伯”的說法,是包括秦穆公,即所謂“秦穆之霸”的。
在戰國晚期,七雄之中,以齊、楚、趙、秦為最強。到了公元前3世紀的後期,則秦國的軍威,已經勢不可當。在秦孝公與商鞅變法之後,秦惠文王兼併巴蜀,宣太后與秦昭襄王戰勝義渠,實現對上郡、北地的控制,使秦的疆域大大擴張,時人除“唯秦雄天下”(《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之說外,又稱“秦地半天下”(《史記·張儀列傳》)。秦國上層執政集團可以跨多緯度空間控制,實現了對遊牧區、農牧並作區、粟作區、麥作區以及稻作區兼行管理的條件。這是後來對統一王朝不同生態區和經濟區實施全面行政領導的前期演習。當時的東方六國,沒有一個國傢俱備從事這種政治實踐的條件。
秦兼併天下,“如暴風雷雨,閃擊中原”
關於秦統一的形勢,翦伯贊形容,“如暴風雷雨,閃擊中原”,證明“任何主觀的企圖,都不足以倒轉歷史的車輪”(翦伯贊:《秦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8頁)。秦的“統一”,有的學者更願意用“兼併”的說法。注意“歷史的車輪”之說,應當理解當時社會意識嚮往“天下”“定於一”(《孟子·梁惠王上》)的共同傾向。《公羊傳·隱公元年》首見“大一統”說。而儒學之外的其他學派,也有相近的文化表現。如《莊子·天道》:“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帝王天子之德也……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又說“一心定而王天下”。《墨子·尚同中》:“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荀子·不苟》也說“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一書中“天下”這一語彙出現頻度最高,達267次。如《解老》“進兼天下”,《飾邪》“強匡天下”,《制分》“令行禁止於天下”等。成書於秦地的《呂氏春秋》可見“天下”凡281次。
秦統一的實現,後人稱之為“六王畢,四海一”(杜牧:《阿房宮賦》)。其實,秦始皇完成統一的空間範圍,並不限於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原戰國七雄統治的地域,亦包括對嶺南珠江流域的征服以及“西北斥逐匈奴”(《史記·秦始皇本紀》)。據《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王翦)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從記述次序看,事在王賁、李信“破定燕、齊地”及“秦始皇二十六年,盡並天下”之前。遠征南越,是秦統一的戰略主題之一。而蒙恬經營北邊,又“卻匈奴七百餘里”(《史記·秦始皇本紀》)。南北兩個方向的進取,使得秦王朝的版圖遠遠超越了秦本土與“六王”故地的總和。
秦實現統一的原因
在對於秦文化的討論中,不可避免地會匯入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戰國七雄的歷史競爭中最終秦國取勝?為什麼是秦國而不是其他國家完成了統一這一歷史程序?
應當怎樣認識秦人實現統一的原因?按照秦始皇自己的宣傳,稱“德並諸侯”“烹滅強暴”,又說:“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鹹伏其辜,天下大定。”(《史記·秦始皇本紀》)自詡立足正義以“誅暴亂”,同時有賴“宗廟之靈”。而賈誼《過秦論》“續六世之餘烈”的說法,也肯定秦王政前代君主的歷史作用。李斯的總結,突出強調其政策和策略的合理:“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遊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鬥士,尊功臣,盛其爵祿”(《史記·李斯列傳》)。
司馬遷《史記》曾歸結為“天命”,又有“若天所助”的說法:“是善用兵,又有天命。”(《周本紀》)“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六國年表》)
對於秦所以能夠實現統一的原因,近世尤多有學者討論。有學者認為,秦改革徹底,社會制度先進,是主要原因。曾經負責《睡虎地秦墓竹簡》定稿、主持張家山漢簡整理並進行秦律和漢律對比研究的李學勤曾經指出:“睡虎地竹簡秦律的發現和研究,展示了相當典型的奴隸制關係的景象。”“有的著作認為秦的社會制度比六國先進,筆者不能同意這一看法,從秦人相當普遍地保留野蠻的奴隸制關係來看,事實毋寧說是相反。”(《東周與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0~291頁)
對於秦富國強兵、終於一統的具體條件,可以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秦國在水利經營、交通建設、機械發明、動力革命等方面體現的優勢,實現了國家綜合實力的上升,成為在軍事競爭中勢不可當的重要因素(王子今:《秦統一原因的技術層面考察》,《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9期)。而管理方式的進步與鐵質工具的普及,也表現出對東方六國的某種意義上的超越。秦的學術文化傾向特別注重實用之學的特點(王子今:《秦文化的實用之風》,《光明日報》2013年7月15日),與這一歷史現象有關。秦在技術層次的優勝,使得秦人在兼併戰爭中能夠“追亡逐北,伏屍百萬”,“宰割天下,分裂河山”,最終“振長策而御宇內”,“履至尊而制六合”(賈誼:《過秦論》)。當然,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秦國專制君權較早就發展出了相當之高的政治控制和社會動員能力”(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頁),能夠“有效地規範行政秩序和官員行為”,“保證行政機器的精密運轉”(閻步克:《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頁),也是重要的原因。從秦執政者自我宣傳的言辭看,若干措施“使秦國成為戰國七雄中政治最為清明的國家”(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0頁),而這正是能夠“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史記·秦始皇本紀》)的重要條件。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
秦的統一,是中國史的大事件,也是東方史乃至世界史的大事件。對於中華民族的形成,對於後來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的發展,對於統一政治格局的定型,秦的創制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秦王朝推行郡縣制,實現中央對地方的直接控制。皇帝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出現,也是推進政治史程序的重要發明。秦始皇時代實現了高度的集權。皇室、將相、後宮、富族,都無從侵犯或動搖皇帝的權威。執掌管理天下最高權力的,唯有皇帝。“夫其卓絕在上,不與士民等夷者,獨天子一人耳。”(章太炎:《秦政記》)與秦始皇“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樂觀設想不同,秦的統治未能長久,但是,秦王朝的若干重要制度特別是皇帝獨尊的制度,卻成為此後兩千多年政治史的正規化。後來歷代王朝的行政體制形式有所不同,但是皇權至上的專制主義性質並沒有改變。秦政風格延續長久,對後世中國有長久的規範作用,也對東方世界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影響,如毛澤東詩句所謂“百代都行秦政法”。而譚嗣同對自秦以來君權“橫暴”進行激烈批判,稱“故當以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譚嗣同:《仁學》)。
秦王朝在全新的歷史條件下帶有試驗性質的經濟管理形式,是值得重視的。貨幣的統一,度量衡的統一,創造了經濟進步的條件。其他經濟措施,在施行時有得有失。秦時由中央政府主持的長城工程、馳道與直道工程、阿房宮工程等規模宏大的土木工程的規劃和組織,表現出經濟管理水平的空前提高,也顯示了相當高的行政效率。秦王朝經濟管理的軍事化體制,以苛急的政策傾向為特徵。而以關中奴役關東的區域經濟方針顯現的弊病,也為後世提供了深刻的歷史教訓。秦多以軍人為吏,必然使各級行政機構都容易形成極權專制的特點,行政和經濟管理於是有軍事化的風格,統一後不久即應結束的軍事管制階段在實際上無限期延長,終於釀成暴政。
秦王朝的專制統治表現出高度集權的特色,其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具有與此相應的風格。秦王朝雖然統治時間不長,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卻在若干方面對後世有規定性的意義。“書同文”原本是孔子提出的文化理想。子思作《中庸》,引述了孔子的話:“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書同文”,成為文化統一的一種象徵。但是在孔子的時代,按照儒家的說法,有其位者無其德,有其德者無其位,“書同文”實際上只是一種空想。戰國時期,“書”不“同文”的情形更為嚴重。正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說,“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於是禮樂典籍受到破壞,天下分為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於是,秦統一之後,以“秦文”為基點,欲令天下文字“同之”。秦王朝的“書同文”雖然沒有取得全面的成功,但是當時能夠提出這樣的文化進步的規劃,並且開始實踐,應當說,已經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創舉。
秦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謀求統一,是透過強硬的專制手段推行有關政策的。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商鞅“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行為的繼續,即企圖以秦文化為主體實行強制性的文化統一。對於所謂“難施用”(《史記·封禪書》)“不中用”(《史記·秦始皇本紀》)的學說,不惜採用極端殘酷的手段。對於這種文化政策,東方列國的知識階層則以“吾為無用之學”,“秦非吾友”的態度予以抵制(《資治通鑑》卷七《秦紀二》)。
錢穆曾經發表的意見,我們未必完全贊同,但也許依然可以提供開拓思路的啟示:“中國版圖之恢廓,蓋自秦時已奠其規模。近世言秦政,率斥其專制。然按實而論,秦人初創中國統一之新局,其所努力,亦均為當時事勢所需,實未可一一深非也。”(錢穆:《秦漢史》,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20頁)
秦史的世界影響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將東周時代的中國劃分為中原、北方、齊魯、楚、吳越、巴蜀滇、秦7個文化圈。關於其中的“秦文化圈”,論者寫道:“關中的秦國雄長於廣大的西北地區,稱之為秦文化圈可能是適宜的。秦人在西周建都的故地興起,形成了有獨特風格的文化。雖與中原有所交往,而本身的特點仍甚明顯。”關於戰國晚期至於秦漢時期的文化趨勢,論者指出“秦文化的傳佈”這一時代特點,“秦的兼併列國,建立統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為後來輝煌的漢代文化的基礎”。秦的統一“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轉折點”,繼此之後,漢代創造了輝煌的文明,其影響,“範圍絕不限於亞洲東部,我們只有從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價它的意義和價值。”(《東周與秦代文明》,第10~11頁,第294頁)理解秦文化影響宏遠的意義,應當重視“從世界史的高度”進行考察。
秦人接受來自西北的文化影響,應當是沒有疑義的。周穆王西行,據說到達西王母之國,為他駕馭車馬的,就是以“善御”得“幸”的秦人先祖造父(《史記·秦本紀》)。秦早期養馬業的成功,應當借鑑了草原遊牧民族的技術。青銅器中被確定為秦器者,有的器形“和常見的中國青銅器有別,有學者以之與中亞的一些器物相比”。學界其實較早已經注意到這種器物,以為可能“模仿中亞的風格”。有學者正確地指出,應當重視秦與西北方向的文化聯絡,重視秦文化與中亞文化的關聯。但是以為郡縣制的實行可能來自外來文化影響的看法可能還有待於認真的論證。戰國時期,不僅秦國,不少其他諸侯也都實行了郡縣制。李學勤指出,“郡縣制在春秋時已有萌芽,特別是‘縣’,其原始形態可以追溯到西周。到戰國時期,郡縣制在各國都在推行”(《東周與秦代文明》,第146頁,第289~290頁)。
有人認為蒙恬抗擊匈奴,“斥逐北胡”,最終使得匈奴無法南下,只得西遷,影響了後來的世界民族分佈格局。陳序經在考察公元前3世紀中原民族與匈奴的關係時寫道:“歐洲有些學者曾經指出,中國的修築長城是羅馬帝國衰亡的一個主要原因。他們以為中國修築長城,使匈奴不能向南方發展,後來乃向西方發展。在公元四五世紀的時候,匈奴有一部分人到了歐洲,攻擊哥特人,攻擊羅馬帝國,使羅馬帝國趨於衰亡。”“長城不一定是羅馬帝國衰亡的一個主因,然長城之於羅馬帝國的衰亡,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陳序經:《匈奴史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185頁)匈奴向歐洲遷徙的歷史動向,有的學者認為自秦始皇令蒙恬經營“北邊”起始(比新:《長城、匈奴與羅馬帝國之覆滅》,《歷史大觀園》1985年3期)。有的學者更突出強調同樣為蒙恬經營的秦直道的作用(徐君峰:《秦直道道路走向與文化影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58~226頁)。相關認識的深化,可能還需要更充備的學術論證。
秦代徐巿東渡,“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所擇定的新的適宜的生存空間,《後漢書·東夷傳·倭》推定為與“倭”相關的“海外”之“洲”。這或許可以看作東洋航線初步開通的歷史蹟象。斯里蘭卡發現半兩錢(〔斯里蘭卡〕查迪瑪·博嘎哈瓦塔,柯莎莉·卡庫蘭達拉:《斯里蘭卡藏中國古代錢幣概況》,《百色學院學報》2017年6期),或許可以作為南洋航線早期開通的文物證明。理解並說明秦文化的世界影響,也是絲綢之路史研究應當關注的主題。
西漢時期匈奴人和西域人仍然稱中原人為“秦人”,《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匈奴傳上》及《漢書·西域傳下》均有記載。東漢西域人使用“秦人”稱謂,見於《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作關城誦》。肩水金關漢簡稱謂史料也可見“所將胡騎秦騎名籍”簡文(73EJT1:158),“秦騎”身份也值得關注。這些文化跡象,都說明秦文化對中土以外廣大區域的影響形成了深刻的歷史記憶。遠方“秦人”稱謂,是秦之輝煌歷史的文化紀念。
(本文系作者在為陝西省政府參事室組織編撰、西北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秦史與秦文化研究叢書”所撰總序基礎上改寫而成)
《光明日報》( 2021年08月02日14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