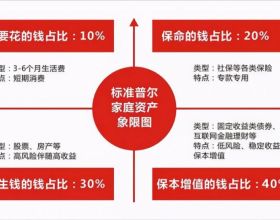流淌歲月
這個夢好像是看電影,不是故事片,而接近黑白記錄片。對面遙遠的群山,崗巒起伏,七坡八斜,灰濛濛。我覺得自己像是站在晴隆縣河塘鎮那個位置(因為攔光照電站水壩現在已經在百把米水下,三十多年前參加追逃或從農場回貴陽,後來多次深入北盤江腹地採訪經過)抬起頭看對面郎岱打鐵關。當真出現了電影鏡頭,而且還是古裝片,那隊馬客一溜煙衝上鄂爾泰古驛道,消失在霧鎖煙迷山埡口,他們是土匪,山貨商人,或者林則徐帶去雲南的隨從。也許是石達開正佈防西林渡。
我其實也清楚,從那個距離,當年汽車都得開三四個鐘頭,沒有望遠鏡,怎麼可能看得見那長隊飛奔的人和馬,夢裡彷彿還能聽見“啪嗒啪嗒”馬蹄聲音,約有十多個人,他們身後揚起煙塵。翻過了山岙。
我多半是從羅門口(小李子家,多年前在他家住了一夜,江對面是西嘎)古戰場乘船順流而下的,那個可以過汽車的鐵索橋仍在,沒拆也沒有沉在江底。如果沿江再繼續下行,我不知道去二十四道拐還需要多少時間。有一個男孩與我同行,在夢裡都不知道他名字,可能是臨時找的嚮導,撐船的另外有個小夥。船伕到哪去了呢?
嚮導大約二十五歲,身材不胖不瘦,比我高出個腦袋,修長胳膊肌肉脹鼓鼓的,手腕戴著個銀手鐲。好像近距離連血管都瞧得見,有點恐怖的是,他的血我覺得是綠色。他穿件淺黃略帶粉綠的無袖套頭衫和運動褲。厚嘴唇,牙齒雪白,臉頰英俊。他戴頂黑色旅行帽,帽沿前面有幾個英文字母。連續好幾天我倆在深山老林裡轉,我想找的那個人始終不肯露面,本想同他具體落實一下是不是在半坡寨過夜。
嚮導小夥告訴我,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肯定還留在(躲貓貓)山埡口翻山過去傳說是岳飛元帥後人居住的那個古老村寨,我怎麼覺得林則徐肯定守在半坡寨,現實中這兩人肯定是沒有碰過面的,在當年我經過那裡也只有三家獵戶,還是住的綠毛竹棚屋。我向其中三十歲左右獵人找水喝,他給了我一個火塘中扒出來的燒洋芋,我吃了,後來王司務長嚇唬我,他說來時警告過多次,不準隨便吃老鄉東西,小心他們放蠱。我說那個獵人是漢人,再說趙六斤是在老鷹巖(白沙鄉)烽火臺那邊中招的。小夥現在說跟當地寨老的談判也不可能少得了他,那是當然,話我都聽不懂。
我為此十分惱火,我車頭問小夥,他到底叫什麼名字,他說叫雅各布,我笑道,這不是那個傳教士伯格理在石門坎遇到的那個苗族人嗎?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小華的行蹤。我心頭正犯猜疑,魏x說不定找別的女人去了,他比較好色,人又長得帥氣,還是雜技表演者,派去南斯拉夫表演過。他老婆快要生孩子,不可能滿足他那方面的要求,而且接見(探監)的時候也沒有任何機會,大隊付叮囑我和丁開旗把他倆看緊點,結果我們上了那個女人的當,還是讓他逃走了。抓不住我責任可大了。
“儘管放心,老魏嘴上倔犟,人品還是不錯的。沒有船,估計他過不了北盤江。”
“難說,人心隔肚皮啊。他太坑我了。”
“相處多年,難道你不瞭解他為人。”
“瞭解個屁!”我對叫雅各布的小夥說著說著真動了氣。“他心事重,心裡邊藏著些事情才不會同我商量,生怕我吃他。”
我思忖,半坡寨的獵人會不會把他們藏在哪裡了,說不定是一個鄂爾泰修的烽火臺,早都廢棄了,我和小華扒開帶刺灌木找過,坍塌了,藏不住人。老魏可不是那種輕易會上女人當的,何況他和我在縣城國營“五一旅社”把那個風騷娘們支得團團轉,早都對他死心塌地。他心疼婆娘得要死那是另外一回事。魏x肯定是逃到D城去了,我和他在那裡都各自有相好的。
我車頭問雅各布知道石門坎鬧過傷寒那件事嗎,他告訴我傳教士伯格理帶去了藥,又幫助救人。如果半坡寨林則徐大人有眾兵把守,那三家獵戶又心甘情願替石達開當了內應,而翻山去那個寨子岳飛的後人都願意幫他經老王山抵達西嘎(我知道有一條小路),乘船到對面羅門口(暫時躲在小李子家),爬上山去就是長流鄉,小李子的姨父在小街上開了個旅社(有點像龍門客棧),或者他們直接走金鐘峽谷,一線天就可以到水城,那麼守在西林渡就徹底失去了意義。激戰西林渡還怎麼拍?
原來真的是劉旭他們在拍電影,這一次是由少煒導演,他怎麼長出鬍子來了,穿的不是黑色短袖衫,而是深灰色長袖帶條紋那種長袖衫和牛仔褲,剪的短髮。他和我可兒是中學同學。聽人講他拍了好幾部片子質量都上不去,什麼鏡頭處理得不好,打磨不精緻,可能是故事有漏洞。這就是我這個擔任編劇的人出問題了,不怪年輕導演。我才想起逃走的魏x原來是石達開受凌遲處死後轉世,雅各布是聽傳教士伯格理說的。他們怎麼可能相信轉世這種說法?不是搞笑又是什麼。或者半坡寨的獵人會信這種鬼話。有人前幾天看見他跟一箇中年獵人在“好再來”吃飯來著,我忍不住破口大罵:“老魏真他媽聰明!”
妻子對自己丈夫的性格最瞭解,對那方面(他會不會在縣城招妓)肯定敏感,但她壓根不想幫我們。我好像是站在新東門爬石梯子坎上去那條路,站路口東張西望,我兒子,孫子波時都是在那個郵電醫院生的,帥哥魏x也是在那裡出世的,當時接生醫生應該知道他是不是石達開將軍轉世。嚮導小夥說他不認識醫生,但我認識。順坡下去,拐個彎,是電臺街華之鴻家的“大覺精舍”和我讀書的貴陽二中。
他女兒是我的化學老師。我仍然站在小鎮街口等回貴陽的班車,老徐哥突然來了,他在農場摘不少八月豆,都已經是最後罷腳的了,看起來都是歪瓜裂棗,彎彎曲曲。但徐哥的車又不回貴陽,而是現在去農場。我覺得時間太晚了,魏x、小華和嚮導小夥雅各布都還在一個酒吧等著我。
我就是想問清楚老魏到底是不是石達開將軍轉世,林則徐大人在半坡寨設伏怎麼會落空,又是誰幫助他到的西嘎,誰划船送他去江對岸羅門口。那時候我其實住在長流街上小李子姨媽家,還有胡濤和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