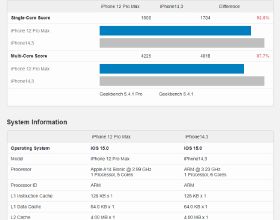我被黎明前的噩夢驚醒,在黑夜裡尋找尚未復歸原形的意識。身體裡翻湧著混濁之物,渴望掙脫皮囊之下的束縛,對一切肉身痛苦的侵襲無法抗拒。
面對黑夜與黎明,我的肉身將要分離;面對鏡子與自己,我將徹底逃離。毫無辦法,我依然受困於黎明前的黑夜,腦海裡殘存的意識聚了又散,逐漸支離破碎,彷彿要掉入深淵、掉入墓穴、掉入那雙壞掉的空洞無物的瞳孔。
我在床上平躺著,像具屍體,期望有光穿過窗戶,照亮我的臥室,照亮我的逃離之路。
每當醒來,我都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尋找消逝的記憶或者是遺失的肢體。我懼怕世界的失憶造成我的失憶,也懼怕世界的殘缺造成我的殘缺。
如果世界不復存在,我終將不復存在,而我與它僅僅是一張薄薄的皮囊的距離,但卻描述得如此遙遠。
醒醒吧!醒醒吧!
我的體內像是有一股灼熱的液體在湧流,既不是讓我血液噴張,也不是讓我精神振奮,而是要將我催眠,將我熔化,變成氣體,在日光之下熠熠生輝。
那是我喝到肚子裡的紅酒,經過一晚的翻騰,好像要將我折騰死。
我從床上爬起來,靜坐著回憶昨晚或者是更加遙遠的事情。
可是,我的右腿怎麼了?被壓得麻痺了,失去了知覺,我用右手去掐右腿的肉,還是沒有知覺。
我隱隱的擔憂即刻入侵腦海,像是拱起酒瓶拼命地往肚子裡灌酒那般迅猛,那般熾烈。我張嘴大喊,但是沒有聲音,我鼻子酸酸,但是沒有眼淚,我再用力掐右腿,但是沒有痛感。
“我真的殘廢了?”我想道。
我坐在床沿,上半身感覺在搖搖晃晃,下半身感覺酥軟無力。我想移動雙腳往前邁開一步,就一步,讓我證實我是杞人憂天。
我剛抬起腳,有種騰空的感覺,但瞬間掩面跌倒在床下。我的鼻子和兩顆門牙都磕碰到了硬梆梆的地板,“嘭”的一聲,磕出了鮮血。
我想要翻轉身體,可是無能為力,原來不僅是右腿,左腿也失去了知覺。毫無辦法,我雙手撐著地板,看到留在地板上的牙印與血跡。
我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出現在這間似曾相識的房間?
我無奈地抬起頭,面對著眼前那塊落地鏡。我看到一張消瘦不堪的面孔,一張不折不扣的滄桑的面孔。若不是看到那隻碰歪的鼻子和磕掉半截的門牙,我都不敢確認那是我的臉。
我掙扎著想要爬起來,可是下半身使不起勁,我只能雙手代替雙腳爬著走,像是一條被碾碎了半截身體的毛毛蟲在爬行。
這種爬行的姿勢在那塊鏡子裡面顯露無遺,一副醜態,如此難看,如此醜陋,可是我為什麼還擠出一張似笑非笑的臉。
我為什麼逃離那個家,為什麼逃離妻子,我怎麼會落到這副難堪的境地?我尋著這個意識,試圖找回遺失的記憶,還有那個殘缺的世界。
最挨近那張床的永遠是光,它是時間流逝的痕跡,是黑夜與黎明的橋樑,還有那令死人都無法逃離的陰影,都終將返回虛無之中。
我原來就躺在那張床上,身邊還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妻子。清晨的陽光從窗戶照射進來,照亮了我的臥室。妻子懶洋洋地伸著腰,鑽到被窩裡。
等到陽光爬到了床上,溫暖了被窩,我們才第二次醒來。
每天早晨,妻子要做的一件事是站在落地鏡前化妝,她的容貌已經令我迷戀不已,她的身體已經令我愛惜有加,可是我卻鮮有看到她令我痴迷的笑臉,甚至那是憂鬱的。她喜歡對著鏡子孤芳自賞,暗自誇耀自己的身材。
鏡子與女人是世間絕佳的搭配,不是無休止地獲得讚美就是共同毀滅。
我從妻子那裡獲得的唯一的讚美就是一張絕望的面孔,那像是一張掛在她額頭上的標籤,也像是一張對我出示的警告牌。
我看那張面孔如此熟悉,但又令我如此畏懼,不是畏懼她的面孔,而是面孔隱藏下的目光帶來的畏懼。
三年還是五年?
我忘記了具體的年數,我與妻子的感情就處在黑夜與黎明之間,生活陷入一潭死水般的窘境,沒有愛情,沒有激情,更沒有殘存的期望。
甜言蜜語成了嘲諷的詞語,取而代之是柴米油鹽的爭吵,相互挖苦、諷刺,誰都不給誰迴旋的餘地,只剩說話時的相互攻擊。
我問她:“這種生活存在什麼意義?”她不回答,拿起一張矮腳凳就砸碎了落地鏡。
她的幻影在我的眼前瞬間支離破碎,破碎的聲音是那樣蕩氣迴腸,那樣清脆響亮,掉落到地板上碎片藉著清晨的光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記憶連同碎片落滿地面。
徹底地破碎了,不僅是我與妻子的感情,還有這個家庭,甚至過去的、現在的和將來的生活都破碎了。
風雨飄搖了三五年,還沒有度過七年之癢,最終在一個平靜的清晨垮掉了,坍塌了。
我能說那是一瞬間的過程嗎?我能說那是三五年的醞釀嗎?
妻子回答說:“這就是生活,我們別無選擇。”
她的絕望的語氣像是毒汁對準我驚呆的嘴唇,還有睜大的瞳孔,噴射而出。我全然無法抵禦,奪門逃離。
清晨的臥室,陽光照射下的臥室,逃離之後的臥室——矮腳凳、摺疊椅、行李箱、木梳子、口紅、耳環、髮夾,還有菸灰缸、鋼筆、書籍、廢紙屑都在房間裡翻飛。
生活還存在什麼意義?我逃離出來的那一刻,這個疑問冒出我的腦海,答案已經是不言自明。可是為什麼逃離的人是我,一個大男人,而不是她。
我和妻子結婚這些年都沒有要孩子,我的父母頗有意見,責怪過她,誤以為是她生育功能出現障礙,因此父母與妻子曾有過爭吵。
事實上,是否要孩子的事,是我倆共同的決定。結婚的這幾年,我們組建了新家庭,過著兩個人的生活,家庭是新的,房屋是新的,可是生活卻再也沒有新過,不僅如此,還出現了家庭暴力。
過去的小資情調,儼然變得黯然失色,甚至蕩然無存。生活上唯一的意義只有熬日子。這是妻子親口告訴我的,就在我倆的冷戰開始的那些年。
熬,不僅成了生活的代言詞,而且成了一種生活常態。
光,漸漸地變淡了,從窗戶裡照射進來,照到我抬起的腦袋,照到我毫無知覺的下半身。
我回過頭又看到了落地鏡裡面的那張面孔,彷彿看到了妻子的面孔。
失望,悲傷,無趣,彷徨……我還留戀什麼光了?還思考什麼意義了?
一副殘肢廢體,棄之不惜,我再繼續下去也是徒勞無功。
記憶,又是記憶帶我重新整理殘存的意識。記憶裡有一條幽暗潮溼的小巷,它一直延伸,從我的腳下一直無限延伸。
那是一條陰森森的小巷,小巷裡沒有路燈,連月光也無法照射進來,腳下的道路像是要通往一處幽深的墓穴。
我看到小巷的盡頭有忽閃忽閃的燈光,不斷有人影出現,也不斷有人與我擦肩而過。
“兄弟,看著點,不要走路不長眼,趕著去投胎啊!”有個聲音在我的耳邊響起,那個人撞了我還理直氣壯,說話的聲音像是空谷傳響,迴盪在狹窄悠長的巷道里。
再往前走,接連幾個人撞了我,嘴裡重複著那句話。我以為那是同一個人,原來那是同一群人。我是在不知不覺中走向那處地方的,或者說是被人撞著進去的,終究是沒有人指引我,唯有自己模糊不清的記憶在牽引著……
我進入的是一家酒吧。我坐到吧檯前的椅子上,朝一個女服務員招手:“一瓶紅酒。”我的聲音也像是空谷傳響,除此還混雜著嘶嘶哀鳴。
旁邊的一位男人用奇怪的目光打量我,表情略顯誇張,像是看到了異物。
我看了看吧檯後面反射回來的映象:他穿著一身邋里邋遢的衣服,蓬頭垢面,鬍子拉碴,像一個可憐的乞丐,目光充滿憂鬱,臉頰是皺巴巴的,像是憋下去的氣球,每一條皺紋清晰可見,輪廓分明。
我看著“他”既陌生又恐懼。我尋找不到與“他”的共同點,但是他既是我,我既是他,這是不爭的事實。
一會之後,女服務員遞給我一瓶紅酒和兩隻杯子,她朝我抿嘴一笑,令我感到很驚詫,腦海裡冒出妻子那張絕望的臉。她以為我會請她喝酒,可是她錯了。
我說:“不要對著我笑。”
她就立馬扳過臉,從我的手中奪走一隻杯子,懟道:“還是這麼吝嗇。”
她奪盃子的動作如此連貫、嫻熟,像是早已彩排好的。
“又一個人喝悶酒啊?”坐在我旁邊的另外一個女人問道,她留著一頭金黃色的大波浪卷。
“走開,沒興趣請你喝酒。”我毫無憐香惜玉之心,甚至看她有種厭惡之感。
“你假裝成‘犀利哥’,還擺個臭架子。”女人說道,她用同情的目光看著我。
我不想搭理這個女人,她也沒有離開,她的眼神告訴我:我們曾經認識。
“今晚怎麼有時間過來喝酒了?”忽然有個人從背後拍著我的左肩膀問道。
我回頭看了一眼,他是個中年男人,顴骨凸起,兩頰凹陷,從他提的問題得知,他也認識我。但我認不出他的真實身份。
“你可不要招惹他,他今晚又是吃了火藥,估計是以前被老婆氣出來的。”女人接過中年男人的話,語氣中帶著嘲諷。
“又想起那事。都過去一年了,你還想念她。”中年男人說道。
“她畢竟是我最親的姐妹,她的離世讓我感到心痛。我怎麼會忘記。”女人嘆息道。
中年男人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也不全是你的錯。”
我被酒吧裡的燈光晃得眩暈,腦袋裡閃著斷斷續續的片段,加上灌了三杯紅酒,我的眼珠出現了灼熱感。即便如此,這裡還是給人營造出了一種夢幻般的氛圍,柔和的音樂,昏暗的燈光,還有我的映象,似真非真。可是我認識他們嗎?
他們為什麼跟我說些莫名其妙的話?我看到他們舉起酒杯相互碰了碰,露出似曾相識的笑臉。
“你又是誰?”我問道。我的嘴裡溢滿酒氣,說出的話也是帶著酒味。
“你不認得我,但我認得你。還是你喝醉了?你喝的酒也不夠勁啊!”中年男人說完這話就引起了一陣發笑,“你老婆以前懂你的幽默嗎?她估計不懂。她是因為看上你裝傻的樣子才喜歡你的吧。”
“你們怎麼認識我老婆?”我拍拍晃暈的腦袋問道。
“我們當然認識。”中年男人答道。
“你老婆是我的姐妹,她曾經是酒吧的‘鎮吧之寶’,這兒的人都認識她,她是大灣河右岸的名人。”
那個女人忍不住地說道,“那時你是個一事無成的男人,跟現在一樣模樣,一個落魄的默默無聞的作家,你經常來到酒吧裡喝悶酒、撒潑,是個十足逃離現實的人,看誰都不順眼,唯獨看我的姐妹——就是你以前的老婆——痴迷得要死。我真的不懂她看上你什麼了,居然放棄高薪工作嫁給你,嫁給一個一無所有的人。我真看不出來你有多大的能耐獲得她的芳心,真不懂。”
“也不能怪他,這兒的人也是一無所有,也是為了逃離現實。”中年男人說道,他像是在替我說情。
“你們男人就是喜歡逃離現實,還抱怨我們女人太過現實,把家庭擔子丟給女人就一走了之,真失望。”女人的情緒愈來愈不滿了。
“男人女人都有吧,無論逃離之路有多長,他們或多或少樂在其中。你現在逃離的就是你過去逃離的,你今天度過的就是你昨天度過的。他們想來這裡尋找逃離的道路,誰都沒有錯,可是這裡沒有道路,他們終將犯錯。”中年男人的話頗有意味,又像另有所指。
“你瞧瞧他那副頹敗的德性,當初我的姐妹怎麼就決心嫁給他了。要不是因為他,她就不會離家出走,就不會遭遇車禍,就不會離開我們。”女人說著就哽咽了。
“你們幹嘛詛咒我老婆?”我迷迷糊糊地問道,沒有悲傷與哀痛,只有疑惑。
“兄弟,我們理解你的處境。你老婆的確在一年前遭車禍去世了,因為你們夫妻爭吵,你動手搧她耳光,她一怒之下逃離了家。她本想回來找我們,卻在酒吧門口意外遭遇了車禍。事後,是我打電話告訴你這個噩耗,你很愧疚,卻不慎失足從樓梯上摔下來,暈倒了,最終造成了你的輕度的失認症。你經常來這家酒吧,但是都認不出我們。後來我們發現,你的記憶也出現了混亂,常常出現幻想。現在,你記不得你老婆去世那個事了。也許是上天對你的懲罰,也許是對你的同情吧……”
這會兒,我的身邊圍上來一群人,他們像是來聽中年男人講故事的,又像是來圍觀我、指責我的。我在女人那裡得知了自己的身份,得知了妻子已經離開世間,一切罪惡都因我而起,我是罪魁禍首。
在中年男人那裡,我卻迷失了自己,迷失了今天,原來逃離的人不是我,而是我的妻子。在他那裡,逃離現實無法獲得慰藉,始終是生命的徒然,現在也是生命的徒然,過去也不過是時間的徒然,而我沒有未來。那麼,逃離的意義又是什麼了?
我想要回避那個女人、那個中年男人還有他們。我對他們一無所知,他們說的話我將信將疑。
徒然,生命成了徒然,逃離成了徒然。
我在眼珠的絲絲灼痛之中返回到記憶的河流。那是更遠還是更近的記憶?、
時間像條河流在靜靜地流淌,流過過去與現在,但卻流不過未來。
我所行的路,在我的腳下成了虛空的映象,我知道也是徒然,通往一處更深的徒然。
映象裡,我走在一條街道上,路燈照射下來的光線是扭曲的,兩旁的樓房是搖晃的,街道是騰空斷裂的,這不像是我逃離遠方的路,也不像是引導我回家的路,而我固執地相信,我所行的路就是我心所願的。
我也不得不承認,只要一息尚存,我就永遠無法逃離。
我離開酒吧,搖搖晃晃地走出門口,我驚訝地看到了妻子,認出是她,她就站在街道中央向我招手。我朝她走去。耳邊響起了鐘錶的滴答聲,車輛的喇叭聲,忽然眼前閃過一束稍縱即逝的光芒。
記憶帶我走進一場噩夢,我在掙扎、逃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