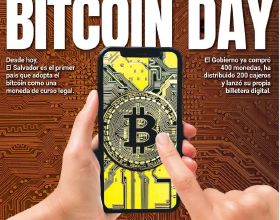我跟娘去賣豬仔
陳揚桂
早前和鄰居大媽聊天,問她餵了幾條豬,她說:“沒餵了,買不起豬仔。”我問:“豬仔多少錢一斤?”大媽搖搖頭說:“別提了,豬仔又貴又俏,買不起也買不到啊。”
而今的豬仔這麼好的行情,使我陡然想起當年娘帶我賣豬仔的苦處。
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農村經濟萎縮,農戶養雞養豬受到嚴格限制。我家人多勞少,因為生活所迫,我娘偷偷餵了一頭母豬,指望賣了豬仔打煤油、買鹽吃。
餵了母豬就意味著娘有做不完的苦活。母豬和剛生下的豬仔都是需要營養的,娘便趕早趕夜地烤燒酒和打豆腐賣,因為酒渣和豆腐渣都是豬們最好的營養品。相對來說,烤酒還要輕鬆一些,可打豆腐實在是太辛苦了。每天一早就要把幹黃豆碾碎,揚去豆皮,把豆肉泡在盆裡。傍晚,豆肉泡脹後,就開始磨豆漿。用石磨磨豆漿是十分勞累睏乏的活兒。印象中,我那在大隊漁場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不做家務的父親,從來沒有磨過豆漿,而我,從小就是幫娘推磨的主要幫手。
磨一盆豆漿需要個把小時,雙腳站在同一個地方,雙手輪流握著磨把轉來轉去,這種勞累而又單調的活兒,與其說是磨豆漿,不如說是磨人。我娘一般每晚打兩匣豆腐,多的也有三四匣,每天晚上,她總是要忙到半夜過後才能睡覺,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挑著豆腐擔子上街叫賣。
豬仔滿月後,賣豬仔的況味便是有喜有憂了。行情好的話,別人上門把仔豬捉走,有現錢給的,給你現錢,看到錢孃的眼裡會噙滿喜悅。沒現錢的也會說好等豬長大宰了後,給送肉送錢來,反正有無現錢到手,只要豬仔被人家捉走,希望便降臨到了我孃的心裡。然而,那些年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餵豬也是搞資本主義,沒有幾個人會像我娘一樣“傻”,累死累活地餵豬挨批鬥,所以仔豬賣不出去的時候居多。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十二三歲的時候,跟娘一起去賣豬仔的情形。
那年暑假裡,也正是開蒙早又跳級的我初中畢業,即將升入高中的一天早晨,天上的太陽像一隻燒紅了的炭火盆,早早地掛上東邊的天空。娘對我說:“桂毛幾,今天你跟娘去街上賣豬崽崽,賣到錢好給你交學費。”常常為學費受逼,看慣了老師和同學冷眼的我,為了那幾塊錢學費,吃了早飯就跟娘一道挑上豬仔去周旺鋪街上了。
從家裡到周旺鋪街上兩三里路遠,娘一擔籠子裡挑了七八隻豬仔,我只挑了三四隻,好在路不很遠,路上歇了幾回肩,也就不是太難地到了吉昌齋仔豬交易場。在這兒一整天,偶爾有人來問問價錢,娘開始說是賣五毛錢一斤,後來說到四毛五、四毛,可最終沒有誰買去一隻豬仔。到天黑時,孃兒倆懷著落寞的心情,又把餓得嗷嗷的仔豬挑回了家。
第二天早晨,娘又說要帶我去賣豬仔,可是這回她說話的底氣沒那麼足了,叫我的語調也和昨天明顯不同了,而且還用新的承諾來吊我的胃口,娘說:“桂毛,一開春你就打赤腳,今天我們去灘頭賣豬崽崽,那裡買的人多,賣了豬崽給你買雙草鞋。”我已沒了憧憬,但還是答應和娘一道去,一是為了那雙夢寐以求的草鞋,二是去看看灘頭也好,在這以前,我聽說灘頭比周旺鬧熱,那裡有吃居民糧的伢子妹子。
可是去灘頭的路程有二十來裡,同樣是那麼一擔豬仔,挑到那裡已經是用了吃奶的力氣了。可恨的是在灘頭同樣無人問津,到中午了,豬仔沒有賣了一隻,我卻喊起餓來。娘去買了兩個燒餅來給我吃,我問娘:“你吃什麼?”她說:“我去吃麵。”說著,交代我一邊吃,一邊照看著豬仔。我望著孃的單瘦的背影遠去、遠去,最後定格在豬市場可以看到的一座小石橋上。娘坐在那青石護欄上,望著橋下的流水發楞。一碗麵工夫後,娘起身回來了。我當時明明看到她沒有去哪兒吃一點東西,但不太懂事的我,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問。
到下午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我的肚子又一次咕咕叫了,豬仔還是一隻沒賣掉,娘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了聲“我們回去”,就領著我挑起豬仔回家去。二十里路,餓著肚子,挑著擔子,打著赤腳,走的是滾燙的沙石馬路,這一路是怎麼走回家的,對於一個個子矮小的少年來說,那份苦是沒法說得出來的。但是,我娘一整天一點東西也沒吃,作為她的兒子,我再不懂事,這個時候也不敢說苦叫累了。
豬仔這麼難賣,就連送人也沒人要了,再喂下去家裡是沒有糧食喂的,怎麼辦?娘把信發到她的孃家,外婆領著兩個舅媽和姨媽來了,她們一人捉了兩隻豬仔回去,剩下的請村裡的幾個嬸嬸一人捉去一隻,雖然大多沒有給現錢,但總算給我娘了了一樁難事。從不食言的娘,在我進入高中學習後,為了兌現承諾,硬是湊了一塊二毛錢,給我買了一雙廢輪胎割成的膠草鞋,讓我結束了光腳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