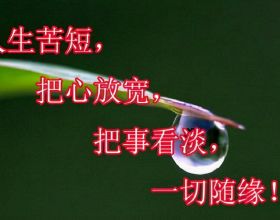南方故鄉
我從未見過一匹馬如此決絕,
畢竟我的南方故鄉終年不會落雪。
秋末,飛蓬從夷方歸來,
我總誤認為它們的潔白已經堅守多年,
飄轉過怒江終於落在北海湖的鳶尾叢中。
那時,我淚花盈眶,攜著竹籃,
站在馬的眼睛裡,像蒼老的榆木不再羨慕山林,
可當我低頭,馬兒兀然遠去,
你被淚水打溼一如雪地落下,失去了輕盈,
失去了南方終年的素樸,
然而那卻是另一種不可多得的絕色。
曲石記
你定然一生志在四方,朝碧海而暮蒼梧,
定然在青年時曾為誰不忍成行,
借道早春的江南抵達河湖同樣紛雜的邊陲。
可當群鳥飛落於柱狀節理,
一封三萬字的長信便佈滿龍川,
成為你餘生恆久的嗟嘆。
如若在含混的夢中南逾數里,
村廬、懸藤、古塢必現,
踞草而坐的醉酒者也必現,不再涉江去,
做高黎貢的隱客與齋僧,
忘記了人間賣漿的女子出生在怒江以西的江苴,
而不是東側的哀牢故地,先觸到霧的籠起。
//// 南齋公房
雨水在微茫的燈焰上還俗,
廟間打坐千年的瓦當,落滿人世的塵埃。
我崇敬地捧起一粒怒江的沙子,
揉進飲水的矮種馬胃腹裡,
某個月夜,它將孕育出天生帶疾的翡翠、鹽與鐵,
像星野一樣,這是邊疆的必須,也是奢侈。
當馬幫和走夷方的人群悄然翻越山巒,
古道就變得如此幽深莫測。
你看不見南齋公房,可它就依偎在岑雲旁,
給行人施捨著江水和齋飯,
像積蓄已久的雪,稠密而又清寒,
藏在一位年邁齋公的衣襟深處。
騰越帖
城中無市肆,城外有人焚棺煮酒,
而凡飲龍川江水者,臟腑必然透徹,
不似南關十里的宿霧,數百年,
籠罩著前朝皇帝拈過的花樹。
護珠寺佛腹內湧蕩的長歌從未泯塵,
像一座虛亭。過了舊巷,
直趨而南,都要遠走夷方。
從此,路亦漸湮,崖谷難料,
遇馬幫與流水,則從之,
逢虎獸,則避之,若不返,
世間的多情便化作紙蝶。
這邊陲的小江南,
偏安了白玉與諸佛,便多了野史和傳說,
除徐霞客與後來的過客,
再也沒人見過最為深情的烈女和她的牌坊。
//// 琥珀殤
酒徒,亡命之人,都曾在懸崖邊坐而論道,
空蕩的行囊裡慘白的月光。
一匹馬的身影走進松林,驚亂熟睡的蟻群,
唯有其中一隻安然無恙,其餘心悸而死。
多年以後,一個酒徒跌落山崖終於發現,
月光深藏著那隻螞蟻傳世的笑容。
走夷方
孤鴻與瘦馬,分別帶走我的命冊,
從南邊的舊城牆下。
還未取徑茶馬古道去過夷方,
可我知道異國的山川就橫陳在遠處的雲霞下。
若路沒有盡頭,
那就讓我們揹著花種一路行走,一直栽種。
而在我們的故鄉,母親為明月安上琴絃,
輕撥了幾次就被雨水衝釋。
父親醉了又醉,把我的名字放在神龕下,
欲言又止。他們只是單純地知道四面八方,
卻不清楚我漂泊至何處。
我撫摸過的皮影,永遠不是我的替身。
風裹挾著我的夢,穿梭于山歌和鄉愁間,
就此遠去,我向著初生的蔓草和墓堆作揖,
然後走進空寂的山嶺,叩問遠方。
路是沒有盡頭的。駝鈴從很遠的林中傳來,
漫在古道,一觸即破。
來源:NICE和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