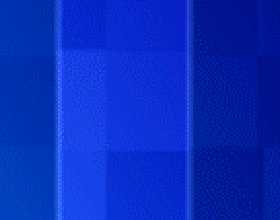《留守者:美國鄉村的衰落與憤怒》
[美]羅伯特·伍斯諾著
盧 屹譯
東方出版中心出版
是什麼引燃了美國鄉村人對聯邦政府的怒火?為什麼絕大多數美國鄉村人會把選票投給共和黨?是否能對日益加深的城鄉分裂給出某種較為具體的解釋?
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羅伯特·伍斯諾歷時十年,深入喧囂都市外的數百個鄉村,提煉上千次的定性訪談,帶我們走近美國鄉村的農場與社群。聆聽農民工人、鄉村主婦、返鄉青年、鄉企業家、鄉村官員的想法,直麵人才流失、企業撤離、外來威脅、種族紛爭、政府幹涉的困境。伍斯諾認為,為了真正地理解美國鄉村人的憤怒,有必要充分地瞭解他們的文化;美國鄉村人憤怒的根源更多的不是經濟上的顧慮,而是對華盛頓政府遠離鄉村社會結構卻對之橫加干涉。
《留守者》不侷限於對美國的核心——美國的鄉村進行簡單的描述,而是就美國鄉村人這個重要的群體對美國政治前途的影響提供了更為清晰的圖景。本書記錄美國鄉村生活、經濟、文化的同時,再現美國鄉村社會熟人社會秩序的瓦解過程,反映逆全球化的蝴蝶效應,為美國城鄉社會分裂與大選左右對立的局面提供了某種解釋。
引言(節選)
過去的十年裡,我一直都在研究美國鄉村的情況並撰寫著作。我在鄉村的世界裡長大,卻已經有好多年沒有生活在那裡了。那個世界裡的人們政治保守、宗教保守,他們生活在小鎮、農場以及遠離東西海岸、人口稀少的地區。他們認為自己的社群是美國的核心區域。我訪問了數百個這樣的社群,研究它們的歷史,從調查報告、選舉結果、出口民調、人口普查、商業資料以及市政檔案中收集它們的資訊。我和研究助手們一起開展了1000多次的深度定性訪談。我們與農民、工人、企業主、家庭主婦、神職人員、小鎮公務員、鎮長、社群志願者等人交談,我們聆聽他們的故事:他們對自己的社群哪裡喜歡、哪裡不喜歡,他們的困難與成就、在乎的問題、政治觀點,還有他們對子女的希望與期待。對於聽到不同意的事情,我們儘可能地擱置異議,並且試圖去傾聽、去理解。
我的主張是,要理解美國鄉村,必須看到由居民結成道德共同體(moral community)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指按照口頭意思所理解的“道德”,即善良、正直、高尚、剛正等,而是要因地制宜地看待道德:在某個地方,人們對彼此負有義務,覺得應該去維護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期望,維持他們獲得歸屬感、正確行事的本地生存法則。
道德共同體吸引我們注意到這樣一點:人們彼此互動時,會對彼此以及發生互動的地方產生忠誠感。這些持續的互動及由此帶來的責任感、身份認同感把這一共同體打造成了一個大家庭。這樣理解社群中的人,與把人看成獨立個體、完全按照自身經濟利益和精神需求而形成見解的觀點是不同的。這些人也許是頑固的利己主義者,但他們實質上未必如此。去美國鄉村待一陣子,你就會發現一個現象:那裡的人是以社群為導向的。
與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受到熱捧的觀點相反,美國鄉村不是鐵板一塊的人口普查集團,也不是步調一致的投票集合體,甚至不是偏向單一政黨的選區。美國鄉村是由小型社群構成的。美國鄉村人不是住在小鎮裡就是住在小鎮附近。從任一城市駕車向任一方向行駛,點綴在沿路地貌中的便是這些社群。在美國19000個統一建制區塊中,有18000個的人口少於25000人。而在這18000個區塊中,有14000個位於城市化區域之外。這才是美國鄉村。
小鎮是美國鄉村的核心。殖民者在佔據東海岸之時,便定居在了各個小鎮裡。隨著人口向著開放的西部擴充套件,他們建立了許多小鎮。定居者無論是住在小鎮上,還是在周邊務農,小鎮對他們的生存都是至關重要的,重要到哪怕全國人口都向城市及城郊遷移了,小鎮在美國鄉村人心目中的地位依然無法動搖。
託斯丹 · 凡勃侖(Thorstein Veblen,1857-1929)很多年前一語道出的小鎮的意義,至今仍能引起美國鄉村人的共鳴:“鄉村小鎮是美國的一種優秀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最優秀的制度,因為它已經並將繼續在塑造公眾情感、賦予美國文化特性等方面起到其他地方無可比擬的作用。”
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住在城市、城郊的人像凡勃侖這樣想的很少了,但住在鄉村小鎮的許多人依然會這樣想。美國鄉村人意識到,國家和文化已經翻開了新的篇章,但他們相信,美國的心臟依然在小型社群裡跳動。
跟美國鄉村人聊天,你馬上就會發現他們的身份認同感與他們所在小鎮的淵源之深。小鎮人口也許在減少,但他們依然關心它的存續。正是在這裡,他們與其他人相識——鄰居、鎮長、銀行女職員、農民合作社裡的夥計。也許他們在這裡長大,也許他們擁有土地。他們在意的是家鄉橄欖球隊在賽季中是否奪勝。他們為這裡的社群精神而感到自豪。
對你所在的小鎮,你不一定什麼都喜歡——也許還有很多不喜歡的地方,然而就是這個小鎮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你的為人。它是你生活的地方、你認識別人的地方以及別人認識你的地方。它的價值觀取決於你的行動,它的思維方式反映在你的談話中。它是你的生活方式,你珍視它並且盡力維護它。
美國鄉村人的內心憤慨是憂慮和憤怒的結合體。憂慮在於小鎮生活方式正在消失,憤怒在於它們已經深陷重圍。不瞭解美國鄉村人對於其社群的忠誠,就無法理解這種憤慨。這種憤慨源於一個事實:就他們習以為常並生活在其中的道德共同體而言,構造了這個共同體的社會期望、關係、責任正在年復一年地從根本上瓦解。
這種瓦解明顯表現在許多鄉村社群的人口正在減少。學校關停、企業撤離、工作機會消失。這些現象影響著諸多家庭,許多父母在撫養孩子之時就已明白他們成人後終有一日要離開家鄉,許多家庭為了工作、購物、做禮拜也不得不搬到更遠的地方。
儘管鄉村社群常常有驚人的復原能力,居民也敏銳地意識到了自己面臨的問題,但人口在很長時間內緩慢下行而他們幾乎意識不到,當學校停辦時,那就好比當頭一棒。鎮子上唯一的小製造廠因為母公司搬遷到墨西哥而關門,也讓他們意識到了相同的問題。還有其他問題:鎮上發現過製毒窩點、一場車禍導致全車的青少年喪生。居民們談論這些問題時就好像它們是新的問題或者比以往嚴重的問題,儘管實際上未必如此。他們擔心高科技裝置高昂的生產成本會逼得本地農民放棄務農。他們擔心社群中的老人、窮人增多,在本地更難得到幫助。他們還擔心來自其他國家、說外語的人們相繼到來,從而威脅到社群的根基。
面臨這些令人畏懼的挑戰,鄉村社群裡最先做出反應的是居民信任並且在需要幫忙時所指望的一群人。這些人希望鄉親們儘量自力更生,實在不行再尋求社群組織的幫助。他們的道德責任感有兩個方面:除非不得已,不要成為他人的負擔;有能力幫忙的話,就應該慷慨解囊。雖說有些是鄰里互助,但大多數還是透過正規渠道組織的。動員資助的組織通常是教會,其後是志願者消防公司、圖書館委員會、共濟會、為病殘者送餐上門的組織以及數量驚人的類似組織,他們都有參與。財力雄厚人士會被眾人期望扮演領導的角色,還有本地的民選官員。人們為這些傳統感到自豪,但也承認這些並不足以應付所有情況。跟其他人一樣,他們也期望政府幫助。
鄉村社群對於華府的看法通常顯現為兩種互相矛盾的敘述:一方面,政府不管我們,沒出任何力量為我們解決問題;另一方面,政府不理解我們,總是侵犯我們的生活,這樣更加添亂。他們表示自己“難過”“反感”“擔心”“憤怒”。他們說,困難之處不單在於華府失靈了,而且在於,為了解決問題,你必須瞭解當地的情況(道德秩序)。跟人打交道,你必須瞭解他們的需求和情況,而不是所有議程一刀切,他們覺得這種方式表明政府更關心的是城市利益而不是他們的利益。同時,他們覺得華府對待鄉村比以往更帶有侵犯性,如提高稅收,執行一些不太公道的規定。
除此之外,鄉村社群的道德秩序還包括用務實、符合常理的方式處理地方問題,而華府似乎不能理解這一點。地方社群自豪於務實、有效、踏實的辦事風格,儘管有時會失敗,要重複幾次才行得通。但社群領導者認識到,處理社群問題的規則已經變了。要辦成事情,就需要外部支援,而要獲得外部支援,就得籠絡人脈、申請撥款。這就必須用到他們可能不具備的專業技能,不然,地方事務就只能指望州、聯邦那些有所偏袒的政策。而華府只會誇誇其談而沒有實際行動,鋪張浪費、毫無人情味,是一個充斥著浮誇理念、高談闊論但不關心老百姓的地方,這種感覺加深了美國鄉村人的憤慨。居民們很氣憤,認為華府好像是被特殊利益驅動的,這些利益只是為了迎合政策說客和偏心的政客。他們憑直覺認為,華府變得如此不負責任,對草根的想法反應如此遲鈍,此時不清算更待何時。
傾聽談話者表達自己的觀點時,我們有時難免會想,他們所說的顯然不合理或者過於偏執。我的觀點是,研究者的角色不是爭論,而是懷著尊重去傾聽,以便能描述他們對自己的世界是如何解釋的。在鄉村美國人居住的社群裡,他們的觀念和想法大多數都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的看法通常表達了積極的價值觀和真實的關切,心懷公正的人都應該能理解。我認為,對於住在城市、城郊的人來說,理解的第一步是馬上走進這些社群,而不是表達反對意見,當然更不是指責數百萬同胞為無可救藥的瘋子。
(本文節選自《留守者:美國鄉村的衰落與憤怒》一書引言)
編輯: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