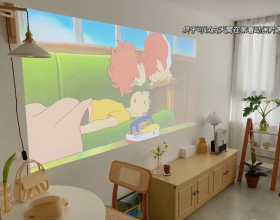新年的炮仗響了半宿,空中四處的五彩斑斕,明暗起伏,半點不見沉寂。
餃子湯氤氳著白茫茫的霧氣,鍾叔拿筷子夾了一下子蒜泥,抹到白生生的餃子皮上。
“明個兒,你去看看你三爺吧。”
山子突然頓住,腦海裡浮現出黑黢黢的小屋,裡面狹窄幽寂,什麼都蒙了一層灰,哪裡都擁擠,哪裡都壓抑。
他沒說話。
“村長的意思,輪換著來,總不能讓老人空著,一個人過年,多少年輪不了一輪,好不容易輪到咱家,你可不能臭著一張臉。”
“別忘了,你小時候……”
“我知道了爹。”山子點了點頭,低頭胡亂夾了兩個餃子,塞了一嘴。
夜裡,山子迷迷糊糊的,好像看見了寶子哥。
寶子哥大他兩歲,是村裡的孩子頭。
貪玩的年紀,又是一群半大小子,有個頭頭帶著,就覺得自己能稱霸,河裡的魚,山上的蘑菇山棗,冬天的結冰的河面,再有旁人家不小心長到牆外的果樹枝條,無一沒被他們光顧過。
大雪天打雪仗,撒歡蹦跳的像一群猴子,把來喊孩子回家吃飯的爹孃也混了進去,糊了人家一身的泥,一臉的雪。
告狀的人找上門,一群孩子齊刷刷地把賬賴給了寶子哥。
聽說那天晚上寶子哥捱打了,幾個小孩戰戰兢兢,聚在平時常去的地方,真像一堆虔誠的手下一般,等著寶子哥過來發火。
“我是你們的大哥,有好事得想著你們,有壞事我也給你們兜著。”
冬天風大,寶子哥的鼻涕甚至都沒擦乾淨,卻被一群小孩奉為了神祗。
那時候好像特別愛好稱大哥,講義氣,寶子哥家裡有一本挺厚的《壞蛋是怎樣煉成的》,山子沒事的時候拿來看了兩頁,看裡面捅人打架稱大哥,勾得他蠢蠢欲動,但到底沒這個膽量,也只能想想。
可寶子哥就不一樣了,他是真正的霸王,十四五歲就一米七多的個子,氣勢洶洶,有模有樣,帶著不知天高地厚的毛頭小子,收服了大半個學校。後來不知是不是玩膩了,寶子哥又和外面的老張老李混在一起,把自己混出了名堂,也混出了校門。
學校要不起那樣惹是生非的學生,山子記得寶子哥走的時候染了一頭黃毛,跟他說要去遠方闖蕩。
畫面定格在寶子哥走的時候那逐漸遠行的班車,突然眼前模糊起來,一轉眼,他也背上了行囊。
從逼仄的鄉間小路出去,他帶著少有的幸運,一路按部就班,抵達了他求學路上的終點。
忙碌,充實,新奇,五色斑斕,舊日的記憶在日益開闊的眼界與生活中被藏進歲月的一角,曾經的身影都被沖淡,面容也模糊,聲音也縹緲,只記得隱隱約約一個影子,帶著一段似有若無的友情。
他路過寶子哥家的時候偶爾會問問寶子哥的情況,寶子哥的父親,也就是三爺,通常寡言少語,只說:“挺好的”
挺好的是有多好,山子不知道,只覺得透著淡淡的敷衍,許久之後,這句話就像是嚼爛了的故事,毫無意義。
不知誰說了一句,寶子哥回來了,兒時的玩伴都湊在一起,竟全是小時候的模樣,他們拉了他衝進寶子哥的家裡,像小時候約好了去河邊一般喊了一聲。
“寶子哥!”
山子猛然醒了。
迎新的炮仗正響得熱鬧,他的心還在砰砰亂跳。
新年是個十分神奇的節點,它的意義並不單單代表萬家燈火,齊聚一堂,也並不單方面代表幸福。事實上它只是以一種轟轟烈烈的熱鬧形式,讓幸福的人察覺到自己的幸福,讓不幸的人察覺到自己的不幸。
而人通常都是趨利避害的,總想著貼近幸福,遠離不幸。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歡新年,對於同一個人來說,也不是所有的時候都喜歡新年。
山子一進屋就聞見一股熟悉的碳火味,這味道總讓他回憶起許多年前的那個大雪天。
屋子裡,頭髮花白的老人裹著棉衣,拿著火鉤子在爐裡捅火。
“三爺過年好啊!”山子揚起聲兒,抬手作了個揖。
“啊,來了?”三爺倒像是受了驚嚇一般,抬起頭,渾濁的眼中已經看不清楚神色。
答了話,三爺又有些懊悔地看了周圍一圈,“我這啥也沒有……”
山子往炕上一看,上面沒有鋪炕蓆,都是煙熏火燎的痕跡,被子堆到牆角,還有一隻髒兮兮的長毛貓在打哈欠。
“沒事,三爺,我就來看看。”山子隨意坐在炕上,感覺自己又回到了學前班時候,被老師盯著,怎麼都彆扭,這也不對,那也不對。
“三爺……寶子哥,還好吧?”
“好,好。”三爺像夢囈似的唸叨了兩聲,又重重嘆了口氣,“一直捎信說挺好的,就是不回來啊,外邊再好,哪能有家裡好啊……”
“是啊,三爺,沒準過兩年就回來了呢,寶子哥要強,肯定想多掙點錢。”
三爺點了一陣頭,沒說話,又繼續去捅那碳火。
山子最後也沒在三爺家待多久,出來的時候,冷風鑽進了衣領,寒意有些徹骨。
山脈一直綿延到遠方,在收斂了鋒芒的陽光下靜靜沉寂,也不知那埋葬了希望的土地,來年會孕育出怎樣的熱鬧,但他知道,入土的人是永遠不會回來了。
正是熱鬧的夏天,不知誰喊了一聲“寶子哥回來了”,而後他匆匆趕過去,親眼見證了年輕的生命如何魂歸故土,如何帶走了老父親的一段記憶。
在三爺的記憶中,寶子哥在遠方,在他的記憶中也應如是,只不過是更遠的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