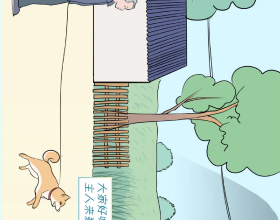故事發生在1951年9月一個寒冷的早晨,火車開到離西部邊境很近的地方,停在東德境內的最後一站。我走下火車,看到頭頂的陰雲,暗自慶幸。這是偷越國境逃回西德的好時機。
我走進一家昏暗的咖啡館坐下,慢慢啜飲一杯檸檬水,等待黑夜的到來。前幾天和父母兄弟在一起生活的情景一幕幕浮現在我眼前,這是我家七年來第一次團聚。
戰亂生活使父母離開家園,最後定居在東德的一個小鎮。再回到老家費希頓赫爾斯特已經不可能——它已隸屬於波蘭。
我從不列顛的戰俘營被釋放後曾一度住在西德。後來我終於打聽到父母的訊息。我父親,一個傷兵,現在已經殘廢,我決定帶他去西德治療,但我未被獲准進入東德。
1951年5月我曾試圖越境看我的父母,在邊境線上被捕並遣返西德,我的護照因此也打了“越境未遂”的標記。現在,4個月後,故伎重演,我成功了。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返回西德,第二次被抓住比蓋上“未遂”戳要糟糕得多,後果不堪設想。可是我覺得我有個很好的機會返回去。我的弟弟給我畫了張地圖,上面標有邊境衛兵的精確位置和一些崗哨無人把守的時間。
手錶指標指向11點鐘,我起身離開咖啡館。
在一條孤寂的鄉村小路上我走了兩個小時。當一個村莊出現在視野裡時,我立刻轉身走進右邊的森林。那片林子一直延伸到邊境。我擦亮一根火柴,最後看了一眼地圖,接著行進。每隔幾分鐘,我就靜靜地站住,聽聽周圍的沙沙聲是否僅僅是風聲和樹葉聲。很快,我接近那條分隔東西的小路。
突然——“站住!”有人用俄語向我大吼。
我立刻趴下,在地上滾了幾下,又爬起來飛跑。一隻手提機關槍“咔嗒嗒”地叫起來,兩團火光在我頭頂上方炸開。接著犬聲大作,什麼東西打在我背上,又把我撞進灌木叢,當我抬起頭,迎面看見一張血盆大口——一條德國牧羊犬正大口大口喘著粗氣。
兩個蘇聯士兵狠狠地扭住我,一個用槍口頂住我的下巴,另一個掏空了我的口袋。他們捆住了我的手,把我押出林子。突然我的血液凝固了——我想起了那張地圖!
那天夜裡我在陰冷的牢房裡走來走去,責怪自己沒有銷燬那張地圖。對蘇聯人來說它將成為我是間諜的最終證明。
第二天清早,衛兵把我帶進一個小辦公室。書桌後面坐著一個穿少校軍服的軍官。紅領章表示他是蘇聯安全警察。
“早晨好,小間諜!”他用德語講話,冷冷地開了個玩笑。
一個俄國軍官能講如此流利標準的德語著實令我吃驚。上校假定我已認罪並希望我立即自首。
“我不是間諜!”我抗議。
“我沒問你的職業,小間諜,只是你睡得如何?嗯——4個月前你曾經企圖越境,告訴我,這次你想偵察點兒什麼?”
“沒什麼,我只不過想去看我的父母。”
“那麼他們住哪兒?”
“無可奉告。”
“我們會弄清楚的。”上校說。
他看了一遍我的護照。“那麼說你生在費希頓赫爾斯特羅?”
他目光犀利地盯了我好一會兒,合上護照,又拿起我的地圖。
“畫得很好,不錯!道路,村莊,我們的哨位,甚至還有大工廠,這麼一張好圖,美國人付你多少錢?”
我沉默了,我知道我的解釋是多麼虛弱無力。
“好了,小間諜,”他喝道,“大概在西伯利亞你會說話!衛兵,帶下去!”
一種寒冷的感覺攫住了我,西伯利亞,不過在牢房裡,飢餓和勞累一襲來我就開始打瞌睡。我沉沉睡去直到衛兵喊醒我,又把我帶到那個上校面前。他點燃了一支菸,從噴出的煙霧後面審視著我。
“我們檢查了你的護照,都是偽造的。現在我們知道了你的確是個間諜,你最好說實話。”
“我沒有理由對你說謊。”我抗議道。
“我們會看到的。你在費希頓赫爾斯特待了多久,小間諜?”
“13歲以前。”
“好極了,給我們講講費希頓赫爾斯特,正好我們也瞭解一下那個村莊。”他身子往後一靠,閉上眼睛。
我開始講述我們的村莊,酸橙樹中古老的教堂;講述我們精力旺盛的男孩子們如何在傍晚的河邊刷洗馬匹。我提到了鄉村牧師、學校老師和我的外祖母。人人都愛她,因為她品德高尚。
我講述的過程中,上校始終表情漠然。當我停下後,他睜開眼睛問道:“那麼你該知道瑪格達·弗爾斯特和娃爾苔爾·考布,比方說?”
我不明白他究竟玩什麼把戲,村子裡根本沒有這兩個人。
“或者莊園主斯多佩爾——伊格那爾·斯多佩爾?”他接著說。
“是的,是的,這個我知道。你認識他,上校?”
“住嘴!”他咆吼道,“我在問你問題,告訴我有關伊格那爾·斯多佩爾的事!”
“好的,他莊園裡的土地是費希頓赫爾斯特最貧瘠的。他幹活那樣拼命,所有的人都同情他。斯多佩爾太太每天都在地裡幹活,他們的兒子約瑟夫也一樣。父親驅使兒子就像驅使他自己一樣沒日沒夜。約瑟夫16歲那年離家出走了。人傳他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但是沒有人敢肯定。”我頓了頓,回憶著我們對斯多佩爾的所有同情。
“講下去。”上校命令。
“兒子失蹤後,伊格那爾像變了個人。他敵視村莊,不去教堂甚至不讓他太太去。”
“為什麼不讓她去?”上校問。
“他們說她袒護那孩子,他為此痛苦,他不願她和別人交談。兒子出走後兩年,斯多佩爾太太就死了,她的丈夫變得比從前更沉默更痛苦了。”
我又停止了一下,“還要我講下去嗎,上校?”
“是的。”
“一天,斯多佩爾受傷住進醫院,他的農場被賣掉付了醫藥費。”
“春天的時候,他回來了,”我接著說,“我的祖母見他在他的老莊園上徘徊,就把他帶到我們家裡,祖母給他一間房,我們一起用餐。他很少講話,連‘謝謝’也不說。但是他儘可能地做所有他能做的事,掙取他的飯食。
“對我來說他似乎非常老,全白頭髮,步履蹣跚。開始我有點怕他。有一天,我想做一個魚竿,笨手笨腳地搗鼓半天。他拿過魚竿,非常嫻熟地做好交給我,從始至終沒有一個字,可那份親切驅走了我的恐懼。從此我們之間充滿了無言的友誼。
“他去世後,祖母在他床墊下找到他太太的祈禱書,書裡夾了一張紙條:父親,我走了,再也不回來了,因為你不愛我。請向媽媽問好,下面簽名:約瑟夫。”
“現在,你相信我是費希頓赫爾斯特的人了吧?!”最後我說。閒聊一個老人和他的不幸使我有點惱羞成怒。
上校沒有回答。“帶下去!”他聲音乾澀地命令。當我轉身離開的時候,他又拿起了地圖。我知道,他不會給我機會解釋了。有人曾因犯罪證據較少而被判服10年苦役。事實上他根本沒對我提起這張圖,一切早策劃好了,我失望而麻木。
早晨,衛兵叫醒了我:“收拾一下!”
是了,西伯利亞,寒冷的西伯利亞!
可是衛兵說,我們帶你去西邊。
往邊界線走的路上,兩個士兵把我夾在中,走了大約一個小時。一路上我時刻準備著被帶回去,這是陰險的詭計,我確信。直到他們給我一些紙並提醒我到西德去要經過的界線時,我相信了一半。
“你真走運。”其中一個不無好意地說。
當我看我的護照時我明白他講的多麼正確。一個新的戳記赫然醒目:“二次潛逃未遂。”簽名:“約瑟夫·斯多佩爾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