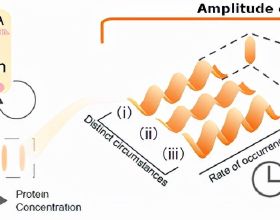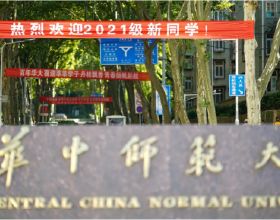1960年,是新中國歷史上極其複雜艱難的一年。
此前發生的天災人禍,在這一年帶來了全國性的大饑荒。
中蘇兩國傷了和氣,最親密的兄弟終於翻臉。蘇聯政府一紙命令,在中國的所有蘇聯專家於當年9月全部撤退回國,給中國眾多重大專案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此乃中蘇兩國交惡的一個標誌性的事件。

圖為1960年9月國防部五院某考研單位歡送蘇聯專家謝苗諾夫及家人回國時留影。
在中央領導層,隨著彭德懷在此前的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說真話的“萬言書”,而被打成反黨集團頭子,撤銷其國防部長職務,兵權被解除,軍隊系統也自然發生了大規模的人事變動。
林彪接替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後,一大批他所信任和熟悉的將領受到重用,被派往各個部門執掌要津。林在四野時期的參謀長——空軍司令劉亞樓上將,於這一年3月18日被任命兼任國防部五院院長;空軍副司令王秉章中將被任命兼任五院副院長,王是劉亞樓的老部下,曾任林彪四野司令部的作戰處長。
4月14日,劉亞樓對五院領導班子說:”五院領導的分工,經過軍委廣州會議前後的醞釀,已經定下來了。聶總也於本月4日找我們黨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還是放在空軍,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時,由他拿總。”
王秉璋當然也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高階將領,但他那時在空軍的工作相當繁重,而且對導彈一點也不熟悉。他本人一開始不理解,上面為什麼要讓他主管這個國防部五院。王秉璋就去找周恩來,周恩來在懷仁堂北門西邊的小屋裡接見了他。王秉璋向周恩來報告說,我沒有技術,搞導彈,搞不了。周恩來停了一會兒說,你說你搞不了導彈,那麼誰能搞?請你在我們這些老同志中找一找,在這些將領中找一找,看看誰能搞!王秉璋提不出來。周恩來說,還是你去搞吧!導彈是帶翅膀的,飛機也是帶翅膀的。你是空軍的,你們總還算是帶翅膀的嘛!相近嘛!
4月27日,五院向總政治部並國防科委呈報正式備案:“五院黨委一致同意:劉亞樓同志為第一書記,王秉璋、劉有光、王諍三同志為書記,劉亞樓同志不在五院時,由王秉璋同志執行第一書記職責,掌管全盤工作。”
這樣,來自空軍的將領全面接管了五院,來自防空軍的劉秉彥,由前幾年主持全院行政工作,改為分管導彈生產協作,從此成為王秉章院長的最得力的助手。而五院首任院長錢學森,則改任專管技術的副院長,此項任命也正符合這位大科學家本人的意願。
1960年儘管整個國家的經濟形勢極為嚴峻,史上最嚴重的饑荒導致民不聊生,許多農村餓殍遍野。但是中央在開發研製導彈這類“殺手鐧”武器方面,仍是克服一切困難,從人員到物資在各個方面,千方百計予以充實和支援。
——這一年,鄧小平、彭真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後視察五院及下屬單位;林彪、賀龍、陳毅、聶榮臻等四位元帥也接踵而至,力挺五院度過難關。
——這一年,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提出了“發憤圖強,突破尖端,兩彈為主,導彈第一,積極發展噴氣技術及無線電電子學,建立現代化的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的方針。
——這一年,中央軍委和國防部從全軍各部隊調來300名軍、師、團、營幹部,充實到五院各單位。國家還從全國各高校一次性向國防部五院分配了4000名大學生。”——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大學生在中國老百姓眼裡屬於鳳毛麟角,遠不像現在這般四處氾濫,滿大街都是。那時一個縣,一年能分配到幾個、十幾個大學生就如獲至寶了。
——這一年,五院的在編人數由17000人增加到30000人,技術幹部由3500人增加到10000人,工人由9000人增加到11000人,導彈研製開始了從仿製到自行設計的轉變。
——這一年,由於生活用品供應不足,五院幹部體質下降,全院查出因營養不良患浮腫病者994人。五院黨委派出以劉秉彥為首的工作組去京郊聯絡,並得到大興縣的支援,先在高碑店開辦農場,後又在河北寶坻縣大中莊、黑龍江北安、甘肅甘南等地建了3個農場。聶榮臻號召各有關單位以副食品支援五院,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北京軍區,東北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瀋陽軍區等單位在物資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立即支援了大批生豬、鮮魚、大豆送到五院。
——這一年,由五院仿製的中國第一枚 “ 1059”導彈,又名“東風一號”在酒泉發射基地發射成功。11月5日,這枚全長17.7米,最大直徑1.65米,起飛重量20.5噸,射程590公里的近程地地導彈,發射後飛行550公里,彈頭準確命中目標區。
當晚,在基地舉行的慶祝酒會上,聶榮臻激動地向參加試驗的科技人員和官兵祝酒:“今天,在祖國的地平線上,飛起了我國自己製造的第一枚導彈,這是我國軍事裝備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以後,我們有了自己的導彈。”
在此前後,劉秉彥作為分管導彈仿製生產的院領導,為了編織一個較為完整,又便於管理的火箭及導彈生產體系,他奔波穿梭于軍內外各有關生產單位,在整合與協調方面耗費了大量精力。
所謂導彈,如果簡單說來,就是在一枚火箭前面加上一個能夠爆炸的有威力的彈頭,並能制導方向。可是不瞭解它的人恐怕不知道,導彈的研發生產其實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系統工程。導彈技術,乃是現代科學技術和基礎工業成就的高度結合,它所需要的材料、工藝、技術幾乎涉及國民經濟的所有生產部門,大到發動機、彈體合金鋼,小到一個橡皮墊圈、一個針頭、一卷鋼絲。
冬春老人曾任二一一導彈總裝廠副廠長。他記得:“仿製“1059”的時候,就有3800多項零部件材料需要落實、解決。別說是我們這些扛槍桿子出身的門外漢,就是讀了大學的專家看了也全傻了眼。工人師傅連同技術員也恐怕有一半叫不出名。”
所以,當1957年12月,蘇聯提供的“P-2”教學導彈還未開始拆卸時,國防部五院和一機部就共同制定了仿製計劃,並簽發了任務分配表。將地面機械裝置分別安排給了航空、電子、兵器等工業部門仿製,原材料則由冶金、化工、建材、輕工、紡織、商業等部門去試製生產。主要承製的廠有60多個,二次協作的廠家有100多個,實際上,到臨近成功時,協作廠將近1400個,簡直就是全國範圍的大動員、大協作!
不難想象,要把這麼多分佈在全國各地及各個行業的廠家,組織起來,為仿製導彈協同會戰,需要劉秉彥付出多少心血!
當年在五院工作的前輩這樣概括說:
首先應當承認,早期中國導彈、火箭的研製,當然不是一個研究院、一個總裝廠就能幹得下來的。它的成功發射,首先是國家集體的力量,是千千萬萬群眾的智慧,它承載著千千萬萬人民群眾的心血和汗水。但就具體實施這一專案的領軍人物而言,錢學森、王諍、劉秉彥這三個人勞苦功高,最具代表性。當年,他們三個人分別負責的研發設計、材料供應和生產工藝這三大環節,可以說是“三駕馬車”並駕齊驅,並由此打下了堅實基礎,形成了基本框架,中國航天在研發和生產方面,才得以一步一步走向輝煌,發展到今天這樣國際領先的一流水平。
面對各種紛繁複雜的人事及利益關係,劉秉彥必須要在這座前所未有的舞臺上,扮演一個折衝樽俎於臺前幕後的吃重角色。雖然他殫精竭慮,勞苦功高,卻未必為觀眾所知。
先講一個涉外交往的故事。
在最後幾名蘇聯專家即將回國之前,劉秉彥就在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市長彭真的親自“導演”下,和彭真一起與幾位部下共同演出過一場“杯酒見真情,讓蘇聯專家把智慧留在中國”的精彩好戲。
1958年底至1960年初國防五院一分院領導與蘇聯專家的合影。左1一分院副院長:林爽,左5五院副院長兼一分院副院長:劉秉彥,左6蘇聯首席顧問什那金,左7劉秉彥兒子劉若楓。
《天歌——走近中國火箭的搖籃》一書中這樣寫道:
1960年9月,就在“1059”導彈的仿製進入了最後階段。在一分院工作的最後三名蘇聯專家已接到命令奉召回國。就在他們接到撤離命令的前兩天,他們依然固執地堅持我國製造的酒精不合格,不能作為導彈的推進劑。儘管國產酒精經過國家檢驗是合格的,但蘇聯專家說必須向蘇聯購買,否則出了問題他們概不負責。
這天,彭真同志正巧來到總裝廠視察。負責生產的副廠長冬春將酒精的事作了詳盡的彙報。彭真笑了笑說:" 我給你們調解調解。你午飯時把杜得柯夫等三個專家請到副院長劉秉彥那兒去,就說我和劉院長請他們喝酒,提前給他們餞個行。"
之後,彭真又走到"1059" 導彈前,與工人、技術員一一握手問候,談了一陣話,才在政委張鈞陪同下,被湧來的科技人員和工人們簇擁著走出總裝廠。
午飯時,冬春領著杜得柯夫等3位蘇聯專家走進院部的小食堂。彭真、張鈞、劉秉彥已在門口恭候迎接。彭真同志特地將杜得柯夫和另一專家拉在他身邊坐下。高高大大、灑脫儒雅的劉秉彥儼然是今天酒宴的主人。鋪著潔白桌布的桌上,分別擺著一排茅臺、五糧液。酒瓶蓋剛掀開,陣陣酒香就把小食堂燻得搖搖欲墜。蘇聯專家們的臉都笑歪了,不等主人把盞敬酒,他們就自己動起手來。62度的中國佳釀,在蘇聯那是隻有總書記宴請各國政要的宴會上才有的,今天中國領導人用如此的瓊漿玉液招待他們,他們自豪、高興又百般感激。賓主間一連三杯下來,那還真應了民間諺語:“一口悶,感情深。”
蘇聯專家高興地唱起了《三套車》,藍眼睛裡充盈了淚水。他們說在中國工作生活每天都像過聖誕節,中國朋友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還說他們的國家對不起中國人,他們感到很慚愧,現在要走了不知今生是否還能來中國,看望一起工作、生活的老朋友。
“感謝就不用說,杜得柯夫同志,你說說今天的酒怎麼樣?”冬春說。
“比起你們的酒呢?”張鈞好像很隨意地問道。
“那不能比,你們的酒在天上,我們的酒在地下,不能比呀!”
“不,杜得柯夫同志,我們的酒不行,酒精也不行,不能加註成導彈推進劑。”劉秉彥略顯醉意,故意大大咧咧地說。
“你們的酒精好,行,完全符合要求,比我想得好,完全可以用在導彈上做推進劑用。”
“可是,杜得柯夫同志,我聽說你不同意使用我們中國的酒精,要用蘇聯的,有這回事嗎?”彭真笑著問道。
“沒有,我怎麼會說這種話呢,你們說過嗎?”杜得柯夫盯著另兩名蘇聯專家問。兩名蘇聯專家一起擺手爭著說:“我沒有”、“我不知道”、“我不會說這樣的蠢話”。
“既然專家們都沒有說過,冬春,那就按原定計劃使用中國的酒精加註,進行試驗。”彭真肯定地說。
“冬春廠長,就按首長的話執行,我現在就簽字。”杜得柯夫邊說邊掏出鋼筆,冬春早就作了準備,立刻將報告簽單遞了過去,杜得柯夫上校揮筆簽上了他的名字。
散席時,劉秉彥副院長把備好的禮物,一瓶茅臺、一瓶五糧液送給他們,蘇聯專家高興地捧著禮物向彭真、劉秉彥、張鈞深深鞠了一躬離去。
晚上11點時,杜得柯夫上校敲開了冬春的門,把一個16開的蘇式筆記本按在冬春手裡神秘地說:“冬春廠長,明天我們就要回國了,我把這個本子留在中國,對將來你們研製新的導彈或許會有幫助,再次謝謝你們對我們在中國的照顧,我們永遠是好—朋—友。”
冬春一把擁抱著他,淚水流了出來:“好朋友,你再等會兒,咱們再幹幾杯。”
中蘇友好的那幾年,劉秉彥曾兩次率五院科學家去蘇聯考察,也經常請蘇聯專家喝酒。老人們說:“劉院長平時不喝酒,但是有酒量。請蘇聯人喝酒,既是友誼,也是工作,都是一人一瓶茅臺,幹完為止。”
經常和蘇聯專家打交道,劉秉彥也喜歡上了喝咖啡,吃黃油麵包。他晚年的生活秘書張亞斌說:“老領導平時吃的很簡單,但有時候一高興,就會吩咐:來,給我沏杯咖啡!我吃一塊麵包。”
相比較與蘇聯專家喝茅臺,談工作,推杯換盞之間,就能推心置腹把問題解決了,更多時候在國內和自己人打交道,反而沒那麼簡單,由此所需足夠的意志力、耐心和原則性,缺一不可。
在他的精心組織協調下,經過各方面人士的刻苦努力,上述工廠的工程技術人員在裝置短缺、無成型技術的困難條件下,仿製前蘇聯B-750型戰術導彈自行研製出彈體、液體火箭發動機和自動駕駛儀,於1964年4月7日在瀋陽成功製造出新中國第一枚地空導彈,並將其命名為“紅旗一號”,代號為HQ-1。同年12月即被批准定型,批次生產出100枚地空導彈裝備了部隊。
同一個時期,國防五院開始仿製“543”地空導彈,與三機部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了以劉秉彥為首的模型彈試驗領導小組,全面領導試射工作。在此之後,科研人員又在該型導彈仿製成功的基礎上改進設計,研製出“紅旗二號”地空導彈,於1967年7月設計定型。同年9月8日,我國防空導彈部隊用新裝備的“紅旗二號”導彈擊落竄入我國華東地區上空的美製u-2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