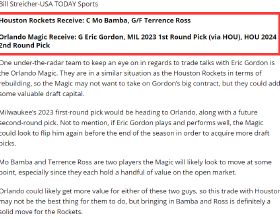六年後我見到初戀,他剛換下芭蕾舞服,光著白花花的大屁股,場面十分驚人。
我慌得從包裡掉出了今早剛到手的離婚證。
他看了上面的日期卻笑了:“我在你心裡就這麼重要,連看一場演出,都要特地先離個婚?”
1、
三十天前,我和戀愛五年的男友申請離婚了。
我和孟放是隱婚,我們高中畢業在一起,大學畢業領了證。
離婚的原因是我發現他出軌。
孟放平時是個很細心的人,微信資訊欄點贊、餓了麼外賣記錄、淘寶購物車這些錯誤他是知道怎麼避免的。
我是在某眾點評裡發現的端倪。
那天我借他的手機搜上門維修,結果在他收藏欄裡,我看見一家叫豆豆糖的網咖。
這個網咖在離杭市足足有30公里的縣城裡。看裝修起碼開了十年,一條點評都沒有的那種。
孟放去年剛買的膝上型電腦,他讀研的學校裡也有很好的學生網咖。不論什麼理由,孟放根本沒有必要去那裡。
那個縣城的名字,我聽著有點熟悉。
直到我找人打聽了一圈,我才知道,那家豆豆糖網咖,是許煬煬爸爸開的。
2.
有什麼橫亙在我們中間微妙的平衡剎那間被打破了。
許煬煬是他的初戀,這麼多年,我一直知道孟放心裡有個放不下的初戀。
所以他沒有給我婚禮,甚至沒有求婚,因為這一切,他都是給許煬煬準備的。
一個月前,我提離婚,孟放沉默了幾秒,然後說了一個字:好。
申請離婚的時候,孟放甚至都沒問我為什麼,結婚是我提的,離婚也是我提的,他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孟放高一的時候母親得癌症,他爸怕麻煩,出軌把他媽甩了。
沒過多久他媽離世,那會他才15歲。
許煬煬在他最灰暗的歲月裡出現,同樣十五歲的她挑染著頭髮,玩世不恭,熱情又放肆,有點像那種電視劇裡的“小太妹”。
但是她家裡很窮,後來高二就輟學了,和孟放的感情也不了了之。
這些年,我忍著孟放,我以為結婚了以後會改變,可事實證明,人是最不可能改變的。
三十天後,我拿到這本離婚證,站在民政局的門口等車,平靜地把離婚證放回包裡。
就在這時,我看到兩張票。
俄國芭蕾舞團的《天鵝湖》。
3.
票是公司獎勵給我的。
我跟孟放大學期間學的戲劇藝術,那時窮歸窮,卻養出了個財閥愛好——喜歡看歌舞劇。
一張票最便宜也要五六百。
年少時我們曾經吹牛逼說等以後賺了錢要買最好的位置,坐在第一排好好數黑天鵝那段“32揮鞭轉”到底轉了幾個圈。再看看哪家芭蕾舞團實力最強。
我看著手裡的票,第一排,最中間,價位兩千以上。
現在我們買得起票了,可演出日期就是我們拿到離婚證的這天。
天意弄人。
最後我拉了大晴來陪我看。
她不知道我跟孟放隱婚,更不知道我今天離婚。
到了現場,她一直在逼逼說ppt還沒做完,這種高雅藝術她欣賞不來。
事實證明,哪怕是價值兩三千的票,也阻止不了大晴坐在第一排打瞌睡。
直到男主演出場了,王子齊格弗裡德從幕後跑出來,她才忽然瞪圓雙眼!
“我靠!這男主角!發育得也太好了吧!”
我看著大晴一臉色相,瞬間知道她在想什麼了。
《天鵝湖》的王子出現的第一幕是舞會,
舞會上有幾組王子單獨連續的“鞭轉”,還有“大跳”的動作。
芭蕾舞裡男演員的“連體褲”原本就很緊身,在動作大得時候,就被拉得更貼、更透。
坐在第一排看得就尤其清楚,懂得都懂。
其實經常看芭蕾舞的人不會特別關注這些,但是大晴忽然這麼“吼”出來,我也被帶“歪”了。
差不多兩個小時,我坐那光聽大晴在那大呼小叫。連傳世的那段黑天鵝的“32揮鞭轉”我都看得心不在焉,更忘了數到底有幾圈。
謝幕之後,大晴說要去後臺找演員合影。
人多雜亂,我不小心走丟了。
一般後臺不讓觀眾隨便進來。我趕緊找個沒人的房間避一避,誰知門一開,渾身血都要飆到天靈蓋上!
對方正站著對著鏡子卸妝,連體服薄,光看背影我不確定他這是脫了還是沒脫。
但是我還是看到了,特別立體的、特別白的、特別有視覺衝擊力的——
一個腚!
“不、不好意思……”
我嚇得扭頭就走,
誰知就在我們開門要出去的時候,那人慢條斯理地吐出兩個字。
“站住。”
我拉門的手中邪一樣停了。
這個聲音有點熟悉。
“剛才演出的時候就跟你閨蜜一直在我身上亂瞟,現在直接闖男演員更衣室,”
“陳嬌,六年沒見,你出息了啊?”
聽著聲音,我腦袋裡好像有什麼東西要炸開了。
“李,李之賁?真的是你?”
剛才看身型聽聲音我就覺得熟悉,同樣的人高馬大、深邃五官,我這輩子也沒見過幾個。
只是舞臺妝的作用下,哪怕第一排我也沒確認。
我本能地回過身去,結果看到眼前畫面嚇出雞叫:“你你你……你怎麼轉過來了!”
他剛好在穿褲子,其實沒讓我看到什麼。
但剛才那一眼讓我確認了,他就是什麼都沒穿!!
李之賁一臉平靜:“你不就想看到這樣嗎?”
“我哪有?我是來看芭蕾舞的!”
“不信你看我有票!”
我說著趕緊從包裡拿票作證,誰知手忙腳亂之中一個紫紅色的本本掉在了地上。
離婚證。
啪,快樂沒了。
我的大腦一片空白,能夠感覺到,他也有一瞬間的靜默。
我呆在原地,手腳都不知道往哪放。
就在這時,他邁著修長的腿走了過來。
李之賁還沒來得及穿上半身的衣服,長腿走過來,彎腰,纖細的手指把那本東西從地上撿起來開啟看了一眼。
“10月21號,今天,”
他合上那個小本子,眼底有促狹的笑意,聲音卻很溫和,“看我一場演出,還要特地先離個婚?”
“看來我在你心裡還是很有分量的嘛。”
4.
李之賁很紳士。
他沒多問一個字,我卻尷尬得要死。
為了證明自己不是那麼侷促,我說有機會請他吃飯。
誰知道他有社交牛逼症:“好啊,剛好你欠我一頓飯,擇日不如撞日,就今天請吧。”
我乾笑著說行啊。
六年前,高三的那個寒假,他說要出國讀書,約我出來玩。
那天他請客,這頓飯我一直沒請回去。到今天他還記著,簡直耗子鑽油壺,只進不出。
我帶他到大劇院附近酒店裡的一家餐廳。
只有這裡門臉很簡陋。木屋子加一塊掛布,一看就很簡樸。
我以為人均100撐死最多了,誰知進去坐下,翻開價目單我心都在抖。
我算了一把,要是李之賁食量跟我差不多的話,想吃個六成飽,人均基本3000起。
我坐在李之賁旁邊強作鎮定:“剛才你在臺上跳了兩個小時餓壞了吧,喜歡吃什麼呀,呵呵。”
“都行,你定。”
他沒拿選單,只是託著側臉一直看著我。
我想大完蛋,他連選單都不看,這是真打算讓我付錢。
我抱著視死如歸的心叫來服務員。
“那個,要河豚白子三吃,白子春捲,還要四串這個雞提燈,燒鳥五拼……”
我水深火熱地點完一堆看不懂的菜之後,扭頭髮現李之賁居然在笑!
“你笑什麼啊?”
“沒什麼,就覺得你挺重的。”
“重?”
我看看自己的小胳膊腿,“我不重啊,我才88斤!”
我轉念一想不對啊,我這剛點完菜呢:“你是說我口味重嗎?”
其實我壓根不知道剛才點了什麼,好多“雅稱”我壓根看不懂。
照這主謂賓結合來看,海鮮有了,主食也有了,我以為算是有裡也有面。
誰知這時李之賁吐出三個字:“我說欲。”
我血剛唰地衝上頭。
他又笑嘻嘻地拿筷子:“口腹之慾的欲,四捨五入,還是重口。”
我當時沒明白他話裡有話,只顧著裝逼:“一看你就沒見過世面吧,日本飲食都很清淡的。”
他沒拆穿我,笑著點頭說是。
直到後來我回家,在網上搜日料裡的“白子”“提燈”都是些什麼東西,尬得我用腳趾都能在地上摳出新西湖十景!
知識告訴我——白子是魚類的精巢。
而提燈,是雞的卵巢。
5.
就在我和李之賁吃完飯的第二天,前夫打電話說他找新女朋友了。
其實我一直是挺慫一個人,從某評上看到訊息到離婚,我甚至都沒發飆過。
可他這次說要帶來給我見見,真的有點惹我生氣了。
我幾乎是下意識給李之賁打電話:“哥,今晚能幫我一把嗎?”
“說。”李之賁那邊好像在開party有點吵。
我扯著嗓子說:“那個,我前夫,今晚要跟小三兒一起約我吃飯。”
“我不想一打二,你跟我演場戲,幫我撐撐場子唄?行不行,球球了。”
我沒想到我會打電話給李之賁。
其實現在網上租一個一日男友也挺便宜的,但憑藉這麼多年孟放對我的瞭解,租一個男友,一來是太容易被識破,二來,今晚陪我出席的這個人,不管換成誰,都不如李之賁具有殺傷力。
因為,曾經我和李之賁也是“夫妻”。
只不過是遊戲裡那種。
我和李之賁最開始是在14歲的時候因為一款網遊認識的。
為了做任務,我倆在遊戲月老NPC面前結為“夫妻”。
後來差不多2012年的時候有一款頁遊火了。每次電腦課我們全班幾乎都揹著老師在偷摸地玩這款遊戲。
李之賁有天也叫我陪他玩,還說給我準備好了賬號。
我當時傻乎乎的,沒想那麼多。誰知電腦課的時候我一上號,全校都炸了。
李之賁雖然不是我們初中的,但在我們學校一直挺出名的。
他在這款遊戲裡是全伺服器第一名,叫一隻小蠍子,
他給我準備的那個賬號,跟他剛好是情侶名,叫一隻小笨魚。
於是所有人都在傳初一三班有一個叫陳嬌的女同學是隔壁私立中學“芭蕾王子”李某同學的女朋友。
更勁爆的是,有人說他給我這個號砸了五十萬!
那會兒我們才讀初中呀,十年前,五十萬,什麼概念?
我根本不敢相信,只覺得是有人要校園霸凌我,故意搞這樣的謊。
而且就一個頁遊小破號,誰會給它充五十萬啊?
他們伺服器有這麼大額充值的埠嗎?
因為害怕被惡搞,我後來也就沒敢上那個號。
我還記得那會我說不玩了,李之賁生氣了好幾天。
他在遊戲裡噼裡啪啦打字罵我:“老子特麼廢大心思給你收來的號,你說不玩就不玩了,你當老子錢大風颳來的?”
我默默回覆:“大不了我幫你掛網賣了啊。”
李之賁:“賣多少?”
我:“五……五十塊?我全轉給你。”
李之賁:“………………”
過了幾分鐘,他給我回了三個字:操你媽!
6.
這號最後我沒賣。
不過接下來忙中考,我也沒再玩過遊戲了。
高中李之賁準備出國了,專攻他從小就擅長的芭蕾舞。
後來我認識了孟放,再後來孟放和許煬煬在一起。
然後就是到了今天。
我和孟放在一起的五年裡,每次提李之賁他就氣一次。
他老說:“李之賁,不就仗著家裡有點小錢嗎?”
“這點小錢有什麼用,他那種不學無術的學無術的小少爺,遲早都會被社會淘汰。”
他嘴上看不起李之賁,心裡其實羨慕嫉妒恨得緊。
所以,現在我們四個人見面是這個局面,我一點也不意外。
氛圍高雅的高階餐廳裡,孟放和許煬煬坐在我對面。
地方是他們選的,本市最高階的一家西餐廳。
在本地,一直有傳言說這家餐廳是我們省的首富家裡開的。
所以這裡座位特別少,價格也特別貴。
當初孟放報出地名時我就知道他們要裝逼。
見到許煬煬本人,更是印證了我心裡這個猜想。
幾年不見,許煬煬一身大牌。什麼四葉草五花,卡地亞釘子全齊,而我坐在她對面,全身上下最值錢的就是優衣庫。首飾就是個200塊錢的小米手環。
不過孟放也好不到哪兒去,他連工作都還沒有。優衣庫都穿不起。
但讓我意外的是,李之賁今天什麼都沒戴。
他一身牛仔褲白體恤,來了之後,耷拉著兩條大長腿大馬金刀地坐在位子上:“怎麼還不上菜啊?”
我拼命給他使眼色,讓他別給我丟人。
他這才收斂了一點,沒繼續左顧右盼。自顧自地開始喝檸檬水。
從他進來開始,孟放的眼睛灼灼地盯著他:“李同學,好巧,今天沒想到你也來,陳嬌可沒跟我說。”
孟放這話說的陰陽怪氣。李之賁這才正眼看他一眼:“哦?是嗎,大概因為最近我們都在一起吧。”
“你說什麼?”孟放笑容有點掛不住。
我鼓起勇氣,拉著李之賁的手火上澆油:“對啊,我們昨晚就在一起了。”
昨晚我們在一起吃晚飯,這麼說也沒錯。我故意大放厥詞,成功地看到孟放現在的臉色就像喋了屎。
他皮笑肉不笑,準備祭出他傲人的學習成績開始diss人:“李同學現在在哪裡高就?我直博XX師範大學,以後興許能有個照應。”
李之賁漫不經心地理了理餐巾:“照應就免了,”
“我平時就跳跳舞。應該照應不了你,孟老師。”
李之賁說孟老師這三個字的時候特別賤,一本正經地諷刺人。
結果孟放這呆比還真信了,甚至笑出來:“跳舞挺好的啊,跳舞鍛鍊身體。”
“你看你,身材比我好多了,光靠臉都能吃到飯呢,哪像我們這種人,只能靠才華,呵呵呵。”
我白眼簡直要翻到天上去。
更要死的是這時許煬煬也開口了:“李同學,我也喜歡跳舞,你平時去哪家店?也許我們以後能碰到呢。”
噗……
我快要笑噴水了。
許煬煬說的“店”應該就是夜店。當年就有人傳許煬煬輟學之後“下海”去了,現在看她這身奶都快掉出來的裝束,還真有這個可能性!
許煬煬還在說:“以後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可以找我和孟老師啊,”
“孟老師在本地人脈很廣的,各大論壇會議如果需要表演的話都可以照顧到你。出場費五百呢!”
許煬煬說得可真誠了,假睫毛一顫一顫的。
這時我忍不住看向我們皇家芭蕾舞團的男主角李之賁同學。
孟放和許煬煬對李之賁的瞭解很少,都是從學校裡的傳聞聽說的。
只有唯一跟李之賁切實有交集的我知道,他不是什麼不學無術的富二代。
就憑他這一場《天鵝湖》的男主角來說吧,亞洲人想要坐到這個位置,天賦功力機遇條件缺一不可。
他的一場演出,一張票就要上千元,上萬元,觀眾上千個。
出場費五百塊?要笑死誰呢?
面對對方這麼奇絕的言辭,李之賁居然還能忍,甚至還做出一臉憧憬的表情:“好啊。”
我都快急死了。
兩頓飯加起來請他吃了一個iphone13了,他居然還在這裡玩龜息大法。
這錢花到哪裡去了?專門花給他長腱子肉了嗎?
到後面,我簡直絕望。
前菜主菜甜品一道道上完,他淨顧著吃,連屁都不帶放一個!
就在我後悔今天為什麼拉這個水貨來撐場子,如喪考妣地叫服務員來買單時,他忽然開口了。
“今天這頓飯算我請了,”
“大家有什麼意見或者建議的話,可以反映給我們的主廚。”
“我們主廚很敬業的,每次客戶的意見他都會悉心聽取。”
我在這時好像聽到了空氣裡一根針掉下的聲音。
良久,許煬煬表情有些愕然:“這裡……是你的餐廳?”
“對啊。”李之賁淡淡道,“李xx是我爸。”
!!!
此時。
我、孟放、許煬煬三個人齊齊都驚了!
請客……餐廳……首富!!
李之賁居然真的是首富的娃!
7.
我整個人都是懵的。
不僅是我,孟放和許煬煬也一樣的懵。
離開餐廳時,我看到了許煬煬精心準備的賓士e300,可在李之賁暴發戶般的幻影面前也黯然失色。
“嘿,想什麼呢。鞋帶散了。”李之賁的司機這時剛把那輛勞斯萊斯開過來。
突然他當著孟放和許煬煬的在我面前蹲下。我下意識一躲,結果腳踝被他穩穩地捏住。
我不敢再動了。呆呆地看著他伸出手,白皙修長的手指給我的帆布鞋繫了一個蝴蝶結。
末了,他還站起來對我笑笑:“老子這輩子還是第一次給女人繫鞋帶。”
“走,上車。”
那一瞬我感覺許煬煬叫上的jimmychoo在流淚。
那可是一雙芭蕾王子的手啊!
誰不想被這雙手摸……呸!哪雙鞋不想被這雙手摸一把!!
安迪·沃霍爾曾說,每個人未來都有15分鐘的成名機會。
我是個十八線的劇作家,一年好不容易接幾個本子都沒有署名權。
連名都不配有,更別提出名。
我不知道這輩子以後我還會不會出名。可自從我再遇到李之賁之後,他讓我的人生就像坐上了雲霄飛車。
原來渺小如我,也能在這幾個小時內成為我小小世界舞臺的唯一主角。
我坐李之賁的勞斯萊斯上,看著他車裡的“星空頂”發呆。
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你當年給我的那個號,到底值多少錢?”
“你猜。”李之賁語氣聽不出情緒。
我只知道為那事他後來好幾年都沒理我。
“我怎麼猜的出來,這麼多年過去了,你就算告訴我又……”
“五十。”他說。
呼,我鬆了一口氣。
還好還好。
他看我如釋重負的模樣,笑嘻嘻地補了一個字:“萬。”
我:“真假的?真值五十萬?”
他漫不經心地開啟車窗,攏著火點了一根菸:“不值。”
“啊?”
“我買來五十萬,你賣五十塊,你說值不值?”
我莫名有點臉紅:“那是因為我歲數小不識貨啊……”
李之賁若有所思地嗤笑一聲:“現在也是。”
他是說我現在還是不識貨嗎?
我水深火熱地想要為自己辯解,他忽然說了一句:“我要走了。”
“啊?去哪啊?”
“舞團下禮拜要去別的地方演出,接下來都有安排,”他說著,吸了一口煙,很紳士地故意吐向窗外,然後回頭眯眸笑著看我,“一兩年都不會回來了。”
嘩啦——
我的星空頂剎那之間好像都不亮了。
就在我發呆的時候,車子到了我家樓下。
我茫然地開啟車門。
關門前,李之賁忽然叫住我:“陳嬌。”
我還是有點悶:“啊?”
“那天你最後一次上線,為什麼不理我?”
我知道他是在說N年前那款網頁遊戲的事情。
在我決定徹底不玩那款遊戲之前,我曾想過在遊戲裡找李之賁去道別。
可就在我上線的時候,偏偏看到他在周圍頻道里在跟我們班班花蘇瑤聊天。
李之賁曾在我面前說過無數次要追蘇瑤。
我一直以為他是口嗨,可那天看到他對蘇瑤的態度,既親暱又熱烈,當時的我特別生氣。
那天李之賁遊戲好友私信裡給我發了一句話,我看都沒看直接下線。
後來,我也沒再重新登陸去看過那條私信了。
我怕看見他說蘇瑤跟他在一起了。
再後來,那個遊戲也倒閉了,所有聊天記錄都不復存在。我至今都不知道李之賁給我發了什麼。
我站在車外,想起彼時年少的我因為他跟蘇瑤熱聊還傷心了好幾個月,一口氣沒提上來,故作冷漠地說:“我幹嘛非要理你啊?我又不是你的小狗。”
丟下這句,我轉身頭也不回出溜竄進黑暗的小巷子。
好像……
一條落荒而逃的小狗。
淦。
8.
回家後我做了一個夢。
夢裡是14歲那年第一次在遊戲裡見到李之賁。
那時的我在遊戲裡是個100級的大佬,他才一級,穿著最昂貴又裝逼的新款時裝,站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原上。
14歲那年,現實中的我父母離婚,我被判給了我爸。
我爸是做銷售的,平時工作壓力大,每次喝醉了回家會一邊罵我一邊砸東西。
我嚇得不知所措,到了晚上經常一個人躲在被窩裡哭。
可是想找人傾訴,所有同學也都睡了。
只有李之賁。
他到深夜都線上,家裡也不管,也沒人沒收他手機。自由得飛起。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次他透過我的動態猜到了什麼。
總之那幾年,一到晚上他都會給我轉發一些笑話。
到後來,沒有他的笑話我都睡不著了。
這種互動一直到他出國後某天深夜我在朋友圈裡發了我和孟放在一起的圖片才結束。
在那段艱澀的歲月裡,我對李之賁的心意,沒有人知道。
我還是挺慫一個人,只敢等李之賁一個青春期,不敢等李之賁一輩子。
9.
最近有高中同學小規模聚會,閨蜜說大家在傳我被大款包了。
不用想都知道是孟放和許煬煬那兩個賤貨。
閨蜜還說他們在同學聚會上很高調,就差把我扒個底朝天。
我嗤之以鼻,一心一意地坐在電腦前肝劇本。
那句話怎麼說來著?
要做那個不聲不響得到整個月亮的人!
努力肝劇本能不能得到月亮不知道,但那天請李之賁吃日料信用卡刷了六千,再不衝點業績月亮直接把我開出族譜哈——月光族淪為月欠族。
就在這時手機響了。
“喂!陳嬌,快點過來。”電話是李之賁打的。
我一臉問號:“快十二點了,我要去哪?”
“來T撈老子,給你獎勵。”
聽到獎勵我眼睛都要綠了。
李之賁窮的只剩下錢,他說獎勵難道是要給我打錢?
只是這地名聽著像酒吧,我訕訕地:“要我幫你滴滴代喝啊?”
“不用你喝,趕緊過來!”
這是我第一次來夜店。之前聽劇組裡有小姐妹說過,杭市夜店裡最貴的就是“A區”那幾個座位。
其中“A區”裡的戰鬥機就是“A88”,“A66”這種卡座號,一晚上消費動輒十萬幾十萬!
小姐妹之前還去了一趟帝都的組,說那邊更誇張,到了節假日最中間的卡座都是要拍賣的,消費幾百萬的都有!
我聽了渾身寒毛都豎起來。有錢人的世界粗暴又瘋狂,喝的假酒都比別人的真酒貴!
李少爺今天的座位號就是A88。
服務員帶著我穿過九曲十八彎。
全夜店最囂張的就是他們這塊。
一堆發光的洋酒瓶子在桌上擺著,一堆身材火辣的洋妞舉著LZB李之賁名字縮寫首字母之類的字母在卡座前站成一排在隨著音樂跳舞。
我看見李之賁坐在最中間,那雙練芭蕾的大長腿四仰八叉地疊著,十分惹眼。
“李……”我剛要叫他,他就對身邊幾個已經喝得醉醺醺的人開口道。
“看見沒,老子的女朋友來接我回家了,都趕緊死開。”(未完待續)
再次宣告:本文轉自知乎,如有侵權,聯絡後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