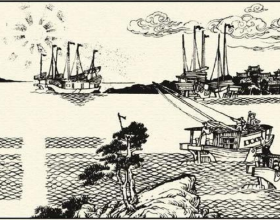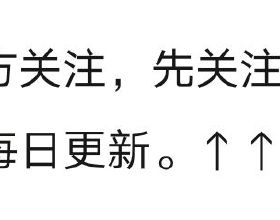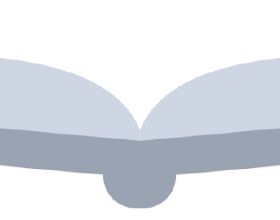我銅陵的房子裡收藏著一套《林氏家譜》,五本厚的,還有一本薄如雜誌。我翻得最多的是其中堪比磚頭般厚實的一本,開啟如木板的封面,裡面有我,有父母,再往上是爺爺奶奶的名字。翻來翻去,我的目光就定格在爺爺身上。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讓我有種沉沉的敬畏,也有一團團的疑惑待解。或許是永存的謎。
有關爺爺的記錄少得可憐:“學詩,生於一九一四年七月初八,卒於一九四三年,葬無為。”就這麼一行,且“卒於一九四三年,”後面沒有月,日,用的是逗號,冥冥之中似乎在暗示他的下人去求證,去澄清這個日子。而“葬無為”這三個字常讓我潸然淚下。十多年了,每到清明冬至祭祖,我們兄弟幾個都沒上過爺爺的墳,為他送一碗飯,一杯酒,一沓紙錢,更不知道我們悲愴的呼喚聲他能否聽到。
爺爺來到這個世界只有二十九年,經歷短暫卻是傳奇,悲壯的人生。去年,我以在老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章彪為原型,寫了一部中篇小說《荒野》,裡面的章彪是真名真人真事,林先生也同樣真實,他就是我爺爺。
聽父親和叔叔聊過,爺爺很早參加了革命,抗日戰爭時期,仼新四軍桐東稅務局的幹部(有人說是局長),在一次稅收回家,屁股還未落坐,家裡便進來了幾個便衣,亮出的身份是新四軍,並且所說的情況都和爺爺所掌握的相符。但爺爺是個有原則的人,他的稅款上繳也必須得到收款憑證。他果斷決定告別家人,和來人一道將稅款送到新四軍隊部,再取回憑證。
這一去就沒再回家。
在寫《荒野》以前,我走訪過村裡的兩位年長者。聊到爺爺,他們解釋是,來的確實是新四軍的人,但是是桐東新四軍游擊隊的兄弟部隊,即,無為的游擊隊。他們掌握了情報,並且先下手為強,等於擄走了這批稅款,因為怕桐東遊擊隊追究,便來了個死無對證。這個解釋有些合理。家譜上的祖祖輩輩都葬在本土,唯有爺爺客死他鄉。這在交通靠雙腳的年代,爺爺又不做生意的背景下,不可能葬到一個陌生的異鄉。
聽父親說,爺爺遇害後奶奶帶他去過爺爺的墳墓,只記待叫牛埠鎮,具體叫什麼地方,他也不清楚。但我能想象,一個小腳女人領著一個才幾歲的孩子,靠自己的腿丈量完幾十公里的泥路,去面對一堆溼漉漉的黃土,這不是毅力,是撕心裂肺的畫畫。
二O一七年,父親重病住院期間,我在《樅陽線上》上看到一篇通訊。作者我認識,我們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一起去樅陽參加過業餘通訊員會議。他去蕪湖幹休所採訪了一位年近百歲的老幹部,巧的是,那位老同志年輕時對桐東新四軍及沿江圩區一帶非常熟悉,並且提到了烈士章彪。其時我還不知道章彪被追授為烈士的。
心中燃起的希望之火,卻被父親淡淡的語氣澆滅了。父親說,事情都過去幾十年了,再查也沒什麼意思,即便查清又能得到什麼?父親是有六月多年黨齡的共產黨員,一直受組織活動的薰陶,境界比我高吧!
不知道父親的內心深處是怎麼想的,但我知道,父親和叔叔曾為爺爺的事奔波了三十年之久。叔叔還沒去世時我曾問過他,你們跑得這麼辛苦,又沒有結果,是為了什麼呢?叔叔說為了一塊牌子。我不知道什麼牌子。上初中時我才明白父親和叔叔不僅僅是爭這塊“烈士家屬”牌匾,更是想洗清爺爺身上蒙著的一層泥垢。他們都確信爺爺是為革命獻身的,死的那年,我一歲不到的小姑也夭折了,太太失望中,獨自一人出家到湯溝後面的“望瑞庵裡。家裡過的日子可想而知,所以我確信,父親和叔叔想得到的應該是精神和物質上的需求。
忽然想起在我開始有了記憶的小學時光裡,每次他們之間的一人去樅陽縣城或安慶市裡歸來,總要聚在門前的稻場上,談論這次跑路的結果,聽到最往往都是“沒人證明”這幾個冷漠的字眼蹦出。夜晚納涼的時候,有了思維能力的我便問,如果爺爺在世,該是多大的幹部?叔叔是個有文化的人,他說該有省裡那麼大吧。我便產生幻覺,彷彿自己就躺在一個機關大院子裡,四周都是樓下樓下,電燈電話的房子,天空中閃爍的星星在朝我眨著眼睛,像是在對我招手。待我醒來,叔叔和父親早已回家睡覺去了。
如今父親和叔叔永遠不再醒來,爺爺的故事早已戛然而止。我們的門頭上沒掛上閃光的金匾,但我們仍沿著他們走過的路在努力前行,奮力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