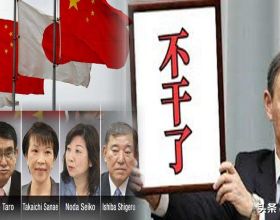攝影:ANAND VARMA
人們聽到“寄生蟲”仨字就反感不適,而寄生蟲的英語“parasite”便來自希臘語“parasitos”,意為“坐在別人旁邊吃飯的;吃剩飯的”。但美國進化生物學家Jimmy Bernot表示,作為“一種非常成功的生命形式”,寄生狀態應得到更多尊重。
一塊有9900萬年曆史的琥珀,一隻抓著恐龍羽毛的蜱蟲,它們以恐龍血液為食
供圖:E. PEÑALVER VIA NATURE COMMUNICATIONS
5.15億年前寄生生物已經出現,人類祖先的出現時間連它們的零頭都趕不上。數億年的演化時間,讓它們掌握了奇巧豐富的生存策略;而且有些“寄生”並不令人作嘔,比如,鮟鱇魚的寄生就是一個悲傷且畸形的愛情故事——
圖中右下角,一條雄性鮟鱇魚(又名琵琶魚)正“小鳥依人”般依附在巨大的雌性體側,它們將透過體外受精來繁殖後代。嬌小的雄魚溶解雌魚腹部的面板組織,然後鑽進去;兩條魚的面板和血管就此合二為一,終身相附至死。最終雄魚除了精巢什麼也不剩,隨時準備在雌性排卵時讓卵受精——“為了愛你,我把自己徹底變成了你。”
攝影:DARLYNE A. MURAWSKI, NATIONAL GEOGRAPHIC CREATIVE
這種鮟鱇魚名為獨樹須魚(Haplophryne mollis),如圖所示,不止一條雄魚寄生在雌魚身上,已知最高紀錄是8條。
攝影:PETER DAVID, GETTY IMAGES
寄生生物從宿主身上獲取營養有多種方式:有一些是體內寄生,在宿主體內安家,比如絛蟲和膚蠅;另一些是體外寄生,直接吸食血液或吃宿主的面板,如蚊子和吸血蝙蝠。
憑藉鋒利牙齒、靈活的舌頭和唾液中的抗凝血劑,吸血蝙蝠的攻擊有時甚至不會被宿主發覺
奧里亞羅非魚尾部的寄生扁蟲
攝影:JOEL SARTORE, NATIONAL GEOGRAPHIC PHOTO ARK
寄生生物已經鑽進了“生命之樹”的每個縫隙,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寄生蟲學家Mackenzie Kwak說:“如果說有什麼把龐大的生態系統粘和在一起,那就是寄生生物。在食物網或生態網中,寄生生物維繫著物種之間超半數的聯絡。”;但至今,我們仍然無法確知寄生生物的所有種類和數量。華盛頓大學寄生蟲生態學家Chelsea Wood得出了一個大概資料——
地球近半數已知生物——
全是寄生生物。
化石記錄中,最早的寄生生物是一條蠕蟲,5.15億年前,它從類似蛤蜊的腕足類動物那裡偷取食物;現代世界的水蛭也是一種蠕蟲,也是最著名的寄生蟲之一。全世界有多達700種水蛭,吸血水蛭的只佔其中一半。
馬來西亞婆羅洲丹濃谷保護區,一個人正在清除水蛭
攝影:MATTIAS KLUM, NAT GEO IMAGE COLLECTION
少數寄生生物還能巧妙地取代宿主的某些器官,比如縮頭魚蝨(Cymothoa exigua)。它們在幼蟲時進入魚類口腔,透過魚的舌頭吸食其血液,直到魚舌頭萎縮,便將自己的尾部與已經萎縮的魚舌連線起來,代替魚舌工作。
供圖:UNIVERSITY OF SALFORD
寄生生物還能使控制宿主行為。例如,一些蟲草屬真菌會把比如螞蟻等昆蟲變成“殭屍”,迫使它們爬到更高的地方,再殺死它們,因為高處是散播真菌孢子的完美地點;孢子充分散播,感染更多螞蟻......
偏側蛇蟲草菌(Ophiocordyceps unilateralis)吞噬了宿主螞蟻,並從螞蟻屍體上長出來。
供圖:ALEX WILD
還有寄生生物會間接竊取資源。比如杜鵑,它會把蛋生在其它鳥巢裡,以騙取別的鳥幫它們撫養後代。
大杜鵑(Cuculus canorus)將卵產在紅尾鴝(Phoenicurus)巢中,寄生卵除了稍大一些之外,顏色與紅尾鴝(qú)卵非常相似;相比之下,左下方,褐頭牛鸝的(Molothrus ater)的寄生卵佈滿斑點,與宿主純白的卵具有明顯差異。
圖源:Nature Education Courtesy of T. Grim & M. Hauber.
東方大葦鶯(左)正在飼餵一隻杜鵑雛鳥,杜鵑是東方大葦鶯體重8倍左右,小鶯鳥辛勤養育著一隻巨嬰(鶯)
攝影:FRANKA SLOTHOUBER
還有看似奇特實則常見的“重寄生”現象,即一種寄生生物又被其他寄生生物寄生。比如寄生蜂Hyposoter horticola會被另一種寄生蜂Mesochorus cf. stigmaticus寄生,後者在前者的幼蟲體內產卵。
一種寄生蜂蟲繭化石,約3500萬年前,數百隻寄生蜂幼蟲飽餐完宿主之後結繭,準備變為成蟲。
攝影:GEORG OLESCHINSKI
生成:THOMAS VAN DE KAMP
還有更甚者,比如寄生真菌的真菌的真菌——在紐西蘭,真菌Rhinotrichella globulifera以真菌Hypomyces c.f. aurantius的死亡部分為食;而後者生前,則吃寄生在山毛櫸樹上的另一種真菌:半灰層孔菌(Fomes hemitephrus)。學名太長、關係太繞,一言以蔽之:你生前吃別人,你死後我吃你。
半灰層孔菌(Fomes hemitephrus)
圖源:jjharrison.com.au
還有一些寄生生物,雖然不起眼,卻在生態系統中起到巨大作用。比如小鼻花(Rhinanthus minor),一種原產於歐洲的寄生植物,會把根部插入草中,吸取它們的汁液,削弱野草那瘋狂的生長力。比方說,一片野地如果沒有小鼻花,這裡就會變成被野草吞沒的草原;反之,野草的生長受限,花朵得以開遍田野,為傳粉昆蟲提供生存空間;昆蟲又會吸引鳥類和兩棲動物前來。於是小鼻花成了一片野花草地的奠基者。
小鼻花(Rhinanthus minor)
圖源:plantsoftheworldonline.org
匹茲堡大學的助理教授Jessica Stephenson認為:“儘管寄生生物很重要,卻奇怪地被忽視了。”;寄生生物生來不討喜,常遭“冷落”,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的生態學家Skylar Hopkins帶頭,曾在《生物保護》雜誌的特刊上發表首個拯救寄生蟲全球計劃,也提出類似看法:“幾百萬種寄生蟲受到威脅,很多可能已滅絕;但奇怪的是,我們幾乎沒有記錄過它們的滅絕。”
此外,許多寄生蟲因為宿主極危,自身也已岌岌可危。
極危物種加州神鷲
攝影:JOEL SARTORE
比如極危物種加州神鷲,20世紀70年代,科學家不顧一切想拯救它們,於是開始圈養這種鳥,但加州神鷲鳥身上特有的蝨子被認為對鳥有害(未確認),為了“保護”鳥,科學家大肆運用殺蟲劑消殺。經過大規模保育之後,幾十年後,2015年,加州神鷲仍然“極危”,而加州神鷲蝨卻再沒出現過。
2014年11月刊封面,瓢蟲繭蜂(Dinocampus coccinellae)將卵產在瓢蟲體內,瓢蟲繭蜂幼蟲在瓢蟲體內發育,發育成熟後,會從仍然活著的瓢蟲體內爬出,並且會不管不顧地在自身周圍結繭。
攝影:ANAND VARMA
去保護看起來噁心的寄生蟲,需要非常大的勇氣,華盛頓大學寄生蟲生態學家Chelsea Wood就是這樣一個有勇氣的人,他也是新保護運動的領導者,這項運動旨在拯救地球上那些“缺乏魅力”的小型動物。
一隻捻翅目雌性寄生蟲鑽進蟋蟀體內。它將在這裡交配、生育和死亡
攝影:JEYARANEY KATHIRITHAMBY
在Wood的研究下,我們明白了這些:氣候變化、宿主消失、刻意消殺,致使寄生蟲在未來50年——其總數的1/10註定滅絕。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有超3.7萬個極危物種,但裡面幾乎沒有寄生蟲的位置,登記在冊的數萬極危物種中,只有一種蝨子和一些淡水蚌是寄生蟲,可想而知寄生群體有多不受人待見。
這不是一隻普通的大斜吻蟹,而是一隻被寄生藤壺入侵的殭屍甲殼類動物。寄生藤,會利用自己的能力擴大螃蟹的腹部,使“雄性變雌性”——在雄性大斜吻蟹體內創造一個子宮,以此來填滿自己的卵。
攝影:ANAND VARMA
梅奧診所(Mayo clinic)醫學中心人體寄生蟲實驗室的醫學主任Bobbi Pritt,她致力於研究各種寄生蟲、防止各種寄生蟲疾病;身為“抗蟲大師”的她說了句公道話:“作為一名醫生,我支援在寄生蟲引發疾病和痛苦的地方,消滅它們!但如果作為一名生物學家,我不贊同有意識滅絕寄生蟲的想法。”
“生命之樹”被稱為“門”的54個主要分支上,有多達31個“門”中大多為寄生蟲;那麼當寄生蟲全部被消滅,等於將這棵巨樹攔腰斬斷。
一種癭蜂將卵產在橡樹葉裡,併產生一種化學物質,誘導植物長出粉紅色的“蟲癭(yǐng)”,也就是寄生生物的房子。
攝影:ANAND VARMA
點選下圖或文末“閱讀原文”
購買2022國家地理中文日曆
首發限時優惠
10月31日內購買限價118元
※新疆西藏以及疫情影響地區暫不發貨
如果你看了這篇文章